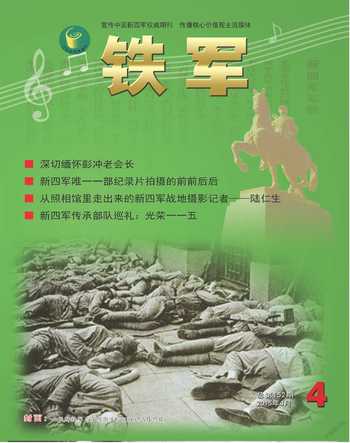浙东女地下交通员万忆琴
赵林
在上海市长宁区一处普通居民楼里,住着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名叫万忆琴。经友人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乐观豁达、笑容可掬的老人。她1927年生,浙江上虞人,如今年近九旬,但身体依然硬朗。每当有人来拜访,她总是笑逐颜开,就像迎接自家儿女一样,亲切热情。
参加革命 经受考验
万忆琴1944年3月参加浙东抗日游击纵队,初时在浙江余(姚)上(虞)两县办事处做通信工作,同年12月调到通信参谋部林一新同志领导的谍报组工作,任谍报组组长。抗战时期浙东环境异常复杂,日、伪、顽、匪各种势力盘踞。万忆琴当时还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其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回忆说,“交通员在敌后活动。刚开始送情报,我走的是山路,脚上常常会起血泡。晚上把血泡挑破后,第二天继续赶路。时间一长,脚底长出了老茧,再也不怕起血泡了。有次下大雪,白雪覆盖了整个村庄,我穿着草鞋,穿梭在冰天雪地里。走着走着,我看见前方有个大凹坑,习惯地纵身一跃,当一只脚落地时,不想恰巧落在一块被白雪覆盖的有朝天铁钉的木板上。坚硬锋利的铁钉扎进了脚底,我顿时钻心刺痛,泪水如注。然而方圆几里没有人家,且身上有任务,呼救等于暴露自己。于是我忍着剧痛,奋力拔出钉子,鲜血立刻涌出,我将头上的毛巾取下包扎好伤口,继续去完成任务。”
地下交通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传递上级下达的命令。万老说,“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如何避开险情将情报安全送达,是工作的难点。首先要在出发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冬天,我将小纸条塞进拆开的棉衣内,再缝好不留破绽;夏天,我把纸条夹在竹篮子的草绳里。其次是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遇敌要镇定自若,利用预先想好的话对答,才能化险为夷。”
1944年5月,经交通分站站长魏克明同志介绍,万忆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说:“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自己暗暗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革命一辈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万忆琴只读过两年书,老师教过的字长久不用也生疏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她觉得搞革命工作,没有文化怎么行?于是,她每天坚持自学,一段时间后,她就能阅读简单书报和写信了。
斗智斗勇 两次脱险
在为革命奋战的日子里,万忆琴时常会遇到各种险情,有两次令她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余姚附近一个叫‘竹园蓬’的地方。那天我刚执行完任务准备回家,途中遇到一个排的顽军迎面向自己走来,队伍前面还有一个被捆绑着的男子。见此情形,我考虑如果就此转身回避,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尽量克制内心的紧张,镇定自若地朝他们走去。可就在与他们擦身而过不远时,突然听到队伍中有人大声喊我过去。我想,如果过去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于是我索性豁出去向前飞跑,还利用平时自己掌握的闪避经验,采取跳跃的方式躲避子弹。我使尽全身力气飞快地跑进了‘竹园蓬’,得以安全脱离险境。”
“还有一次发生在1945年四五月间,傍晚时分我在上虞五夫敌伪据点收集情报归来途中,遇上一排伪军。他们见我一个人,就开始盘问。我急中生智,按平时准备的情况回答:我叫某某某,住在某某地方,现在回娘家某某村。本想蒙混过关,不料,他们也要到这个村子去。我想,这下麻烦了,如果他们同我一起进村,那不就暴露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说的那户人家在哪里,而且也互不认识。顿时我又生一计,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告诉他们让我先走一步,一个女人跟一大群男人一同进村‘不像样子’,在当地不成体统,必然会引起众人的闲话。伪军听后,感觉也在理儿。当他们让开人群一条口子的一刹那,我一个箭步就往村里跑,伪军可能认为我是往自己家里跑,也不急于追赶,只是在后面大声哄笑。我跑了好久才停下来。事后得知,伪军确实到那户人家去找了,但显而易见,他们扑了个空。”
转战上海 继续革命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浙东游击纵队接上级指示要北撤。万忆琴因执行任务特殊,一个人单独住在老百姓家,组织也不知道她的住处,所以她并不知晓部队去了哪里。
为寻找组织,万忆琴历经艰辛来到上海。为了生存,她四处寻找工作。1947年秋,她在上海新丰第一织布厂外读夜校时,终于找到了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1949年2月,上海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成立了沪西分区委,万忆琴被任命为区委委员,负责沪西地区染织业各布厂的交接任务。为此,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上海长宁区妇联宣教科长、上海县供销合作社总社工会副主席等职。
晚年的万忆琴老人爱好唱歌,每每有文艺活动,她总要满怀深情地高唱新四军军歌,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苦并快乐的战斗岁月。
(责任编辑 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