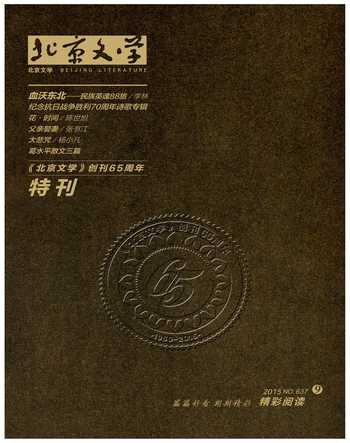南方的诱惑
1996年,我终于下决心去南方闯荡了,这一年我满40岁。我的前半生都是在波澜不惊的平静的死水中度过的。我在苏北小城生活了30多年,在工厂就蹲了20多年,我的青春都留在了美丽的故乡。在故乡的工厂里,我干过锻工、钳工和车工,也做过厂办的打字员和秘书,还做过统计员和保管。天生的不安分,我没能做一行爱一行。几十年当中,我爱好文学,还想靠文学创作当作家改变自己的命运。几十年中,我创作发表过许多诗歌和散文,在市里和县城也有一定的名气,但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我给省里、市里、县上的组织部、宣传部、报社、电台写过许多自荐信,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文化工作。也托过人、请过客送过礼,但都毫无回信和作用,因为我是一家大集体厂的职工,不能调到国营全民的国家部门工作。人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人生和命运,就像一个钉子把人钉死在一个地方,风吹雨打,在那里生锈腐烂,直到老死,了却一生。有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县城,也有人有吃有喝,像一只井底之蛙并且生活得很安逸,但我就是不死心,我要凭我自己的能力改变我的一生。
我也想在工厂谋个一官半职,但都没能实现,最后还下岗了,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下岗后又离异了,我成了一个多余无用的人,失落到了极点,对过去的一切都充满了不满和愤恨,对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也不再留恋。我横下一条心,坚决要走出去,寻找一条新路,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常从报刊电台获知外面世界的变化,心开始浮动了,我渴望金钱和爱情,但我更渴望广阔的蓝天和自由畅快的呼吸。远方像神奇的恋人把我召唤!
带着离异的伤痛,带着一个好奇而美好的梦,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我挥泪告别了生活了30多年的故乡——江苏海安,怀揣着仅有的500多元钱闯广州来了。一到广州火车站,看到路上铺天盖地的黑甲虫一样奔驰的豪华轿车,群星般闪烁的霓虹灯,简直像做梦一样,我已进入花城广州了,我真的到了广州了吗?我真的站到这一块灼热的土地上了吗?但我的兴奋很快就冷却了,因为我仅有500元钱,除去车费和路上的开销,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身上只剩下51元4角8分钱。我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如一时找不到工作,拿不到薪水,我吃什么,用什么?是否也要像作家艾芜那样流浪或沿街乞讨?我有些害怕了,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城市从少女柔和的面纱中刚刚醒来,我就上路了。我买了《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广东交通图,沿着大路走进每一条大街小巷,开始了我艰难的跋涉。我寻找每一家用人的单位,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冷面孔。但广州毕竟是开放城市,还是比家乡好,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有真本领和能力,又能务实和吃苦,就一定会有所发展,我坚信这一点。
身上的钱花光了,我忍着难熬的饥饿,拼命地找工作,如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流浪街头了。真的流落街头,我才体会到了白天真饿、晚上真冷的感觉。白天饿昏了,顾不得面子和尊严,我去饭店、快餐店喝过面汤,吃过客人留下的剩饭。晚上睡过公园和桥洞,风从河面上吹过,布满星星的天空真美丽啊。哪一颗星星属于我呢?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在广州生存下来吗?所有的梦都是美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有原始资金的积累,都充满了血腥。只有脚踏实地,先生存后发展。先解决吃饭睡觉的问题。
为了能在广州生存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打算放下文化人的架子,先干小买卖。我卖过甘蔗,卖过水果,卖过书刊,甚至卖过妇女用的纸巾、胸罩和内裤,但都没能赚到钱。最后我决定在天河购书中心的地下通道口卖装饰画。听熟人说,卖得好一天能赚100多元钱。我用身边仅有的40元批发了10张装饰画,然后以每张15元卖出。净赚了100元,第二天我将所赚的100元钱全部投入,加上本钱,一共150元,批发了40张装饰画。第三天几乎全部卖出,净赚了300多元,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我傍晚拿钱买东西,店主说是假币,我一下蒙了,打开3张百元大钞一看,也发现了异样,手中全是假钞!我真是傻帽,我上当受骗了,一下惊呆了,出了一身冷汗。偏偏这时,保安城管又以影响交通市容为由没收了我全部的装饰画,连一张垫在地上的塑料布也被他们拿走了,除了身上3张100元的假钞外,我成了真正的穷光蛋,搜遍全身所有的口袋,只剩下1块多钱,连吃一个盒饭的钱也没有。我垂头丧气地走到借住朋友的出租屋,所见的情景又给我当头一棒。挂在窗口的1000多元的皮夹克不见了,旅行包和身份证也不翼而飞。这时我真想哭,但怎么也哭不出,我的命运和遭遇怎么这样惨啊!生活,你什么时候才会对我微笑啊!在这痛苦万分的时候,我想起一位名人说过的话:“苦难是你的财富,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擦干眼泪,勇敢地抬起头,面对现实,努力拼搏。我坚信,明天会好起来的,工作会有的,牛奶和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当新的一天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仍然饿着肚皮找工作。
连续找了三四天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光明的希望也没有。正当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广州市《足球报》社主编严俊君和副主编马锦炽老师同情我,他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让我到《足球报》社上班,试用期月薪1800元。每天上夜班,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苦和累我是不怕的,但我根本不懂足球,不懂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再说,人也不能单为钱而活着。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条件优厚的《足球报》社,又重新开始我的寻找。有人赞成我做得对。有人说我是个大傻瓜,有钱不会挣。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我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已的路。
从此我又开始了不知疲惫的寻找,像数门牌号码一样,不放弃每一个可以争取的机会。
广州市文德路170号《广州文艺》杂志社,我见了,眼前不由得一亮,就像干渴者见到沙漠中的绿洲,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日夜向往的文学殿堂吗?
平心静息鼓起勇气,我终于敲开了这神圣的大门。
接待我的是高社长和梁主编,他们热情而又诚恳。他们说,文学现在很不景气,有时连工资也开不出,新来的人,除了编辑组稿工作,主要负责广告经营,每月工资只有底薪800元,另外广告收入提成15%……就是这样的条件,还有10几位应聘的硕士生和研究生跟我竞争。好在我热爱文学,喜欢文学编辑工作,又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过,发表过100多万字的作品,在家乡就担任过广告公司副经理。最后高社长、梁主编决定录用我,选了我这个什么条件也不讲,为干一番事业的穷作家,并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一种千里马遇到伯乐,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有一种为文学奉献和献身的崇高感觉。在《广州文艺》虽然每月工资只有800元,却比《足球报》忙多了。我白天组稿、看稿、拜访作家、拉广告、调研市场、掌握信息,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写自己的东西,一写就写到深夜。我到广州后,每天从来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一次也没有吃过夜宵,饿了都是喝几口茶后睡觉。一个月工资800元,除去房租330元,还有470元。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每天我只吃两顿饭,每顿只吃价钱最低的4元钱一盒的盒饭,饿了忍一忍,渴了喝几口自来水。感冒了,发低烧,口干得裂开了许多小口子,我很想吃街上摊贩卖的两元钱一片的西瓜,但还是忍住了。我来广州是创业的,不是来享受的。我把多余的钱都买了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我每天除了工作,一回到住处就发疯般地投入创作,没有桌子,就伏在床上写,手写酸了也不歇一歇。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已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诗刊》《十月》《钟山》《清明》《天涯》《椰城》《北京文学》《特区文学》以及美国《诗象》、台湾《心脏》《薪火》等1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800多篇,并出版了《怀念家园》《风中的小鸟》《徐泽诗选》《心灵笔记》等诗文集,我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十分想念故乡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每当想起他们,就满含热泪,但一刻也不能松懈,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只要生命尚存,我就要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生活虽然十分清贫艰苦,但我感到很充实。记得一位大诗人说过:“贫穷听着风声也是美丽的!”只要我手里还有一支笔,就不停地写,不停地创造,在创造中完善自己。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