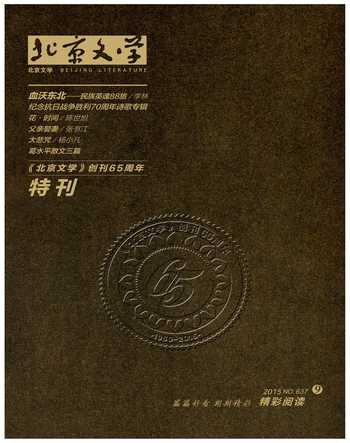涉江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
这首诗描写的是爱情,你看,采了荷花之后打算送人,这不明明就是说要给女孩子送花嘛。她说。
不对,是写思乡之情的,“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这句多明显。他摇摇头说。
她咬着嘴唇,回头看了一眼,不满地哼了一声,把课本扯过来塞进了书包,站起来就把书包一甩,拉灭灯绳,小跑着出了教室。他坐在一团突如其来的黑暗里,耳边尽是自己乱糟糟的呼吸。愣了几秒钟,他赶紧把书本哗啦拨进书包,跟着她出来了。
这座乡中学,是建在半山坡上的,这个县所有乡里的中学都是这样。中学没有围墙,他们一前一后从教室出来,再下一个土坡,就到了黑黢黢的山路上。她在前面沿着那条窄细的溪边小路走着,手电筒的光没有照向小路,而是在初春稀稀拉拉的草里胡乱晃动着。有虫子不停地从光里跳出去。有的跳进了溪水里,在他们看不见的暗处荡起了波纹。
他在她后面,攥着手电筒,远远地照着她面前的路。她就要走到两座山之间的那个岔路口了,从那里往左是他的村;往右,则是大山更深处的她的村。她猛地站定,回头说,谁要你装好心!说着,又转过身去,脸朝着山黑暗的轮廓。她就这么站着,并没有朝着回去的方向迈出步去。他心里快活得有些不敢相信,舔着嘴唇一步步向前挨过去。终于到了她身后,他小心伸手去勾住了她的手指。她不作声,继续站着,留给他一个瘦瘦的脊背。
他索性把她整只手都攥住了。她嘴里低低哼了一声,转到他面前。他伸出胳膊,刚抱住她,就像想起什么似的,捧起她的脸来,慌乱地衔住了那两片软凉的唇。
她闭上眼睛,双手绕过去,把他的腰扣住了。
他们不是乡中学的学生,是县中去年的高考落榜生,正准备再参加这年的高考。他们交不起县中的复读费,就只在县中挂了名,平时白天在家帮着干些农活,只在晚上来乡中学温书。他们从前在不同的班,并不认识,直到成了“高四”的同学,这才熟悉起来。
只一眨眼,这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
车早过了自家从前那座村子,他把脑袋从椅背上抬起,瞅着窗外。他揉搓着酸直的后脖颈,觉得四周的山头都是模模糊糊的。他晕乎乎地想起昨晚的那顿酒席,神经质地把手捂住嘴,哈口气闻了闻,似乎真的闻到一股腐臭的酒气。他早知道自己在的那个部,随便是个官儿,甭管是哪一级,到了地方上都是一把手亲自陪同接待,吃山珍海味,住五星酒店,行警车开道。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一个普通科员,竟然也有这样的待遇。
他是前天下午进的家门。晚上,二舅来家里串门,才知道他回来了。二舅有串门的习惯,他娘,他所有的亲戚也都有。本来嘛,同一个村子的人,都被安置住在县城同一个小区里。进城不到一年,山民们还没习惯打电话。要和亲戚说啥事,还和在山里一样,都是迈迈腿,直接进了亲戚家的客厅。
二舅走后,只一个晚上,他回家这事儿整个县城就都知道了。昨天一早,家里电话响个不停,县里几大班子都宴请他。他知道自己应该“低调”,不该去,可架不住大伯二伯、大舅二舅那样求他。于是,中午是爹和大伯、二伯陪他进“富丽都”,晚上是爹和大舅、二舅陪他进了“金山城”。每顿饭的饭桌上,都是一张张圆胖的脸,笑眯眯地在自己面前转来转去。他记不住这些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脸。这些人都是爹他们素日见都见不着的官儿,看着爹在接受他们敬酒时受宠若惊的笑容,他也有些小小的得意。没轮上的,本来要在今天请,他说这次请年假回来,就是要进山再看看那个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子。否则等水库里蓄上水,村子就到了水库底了。
啥时候截流蓄水,还不是领导一句话?有张白脸在自己面前说着,还毕恭毕敬地把脸转向那张端坐于主位的更胖的脸。他朝那边看去,只看到领导那红亮油润的嘴唇开开合合,似乎是在说要把自己的车,连同司机,一起借给他。接着那张脸慢慢变得模糊了,这也是他醉倒前看到的最后的东西。
他不记得最后怎么回的家,只知道早上自己醒来后,就在客厅里看到了这个正斜坐在沙发上的司机。他胡乱吃了早饭,上了车,才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要去的地方。
她家的村子,是山里最偏的一个。这是个山区县,除了县城在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别的15个乡镇,都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至于那百十个行政村,就更偏僻难寻了。
哥,那个村就在前面,嘿嘿,除了打去年陪领导来打山货,我还没来过这个村。司机说着,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指着对面山崖,说,哥,你看到那根红油漆线了吗?那就是以后的水位线。
他仰脸看过去,只见路边灰白色的山崖上,高高地画着一根粗大的油漆线。他心里盘算着线的高度,估摸着在这根线画完后,有多少个村子从山里搬了出来。
哥,你多久没回村了?司机说。早上还没出家门时,司机叫他领导。他不让这么叫,就和司机论了年纪。一论,他大8岁,就当了哥。
多久了?他想,总有6年了吧。自从他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到了部里,评先进哪年都有他,这也是部里破天荒的事儿了。他要是年年春节回来过年,可就做不到这个了。要知道,每年春节放假前,部里安排假期值班表,他都是第一个报名。
这几天,其实非年非节,他回来是有特殊原因的。前一阵子,处长如愿以偿当上副局级巡视员,退了;两个副处长掐架,都拉他。他一个小科员,倘或站错队,一辈子就完了。科长他都惹不起,何况处长?索性请了年假。他盘算着,等5天的年假结束回到北京,一切也就见分晓了。
昨天,中午的酒劲儿还没过去,晚上就又上了桌。三钱一杯的酒,谁来敬他他都干。他从未这样喝过,直到现在,山风灌进车来,他才清醒过来。这样也好,路上颠得最厉害的那段,就在迷糊中过去了。省道10年前就只从县城修到乡里,现在也还是只修到乡里,到各个村还是没个正儿八经的路,这样也就是“乡乡通公路”了。那时县里的书记,就是靠着这个,后来到市里当了副市长。
这时,车绕过最后一道山崖,进了她家那村子。司机说,村里现在没人了,年前,还有人回来翻腾些东西拿进城里。现在,各家各户都空得只剩下墙了,
他没说话,这些,娘前天晚上都说过。当时娘说完了这些,他说,他还得来看看。你这娃儿啊。当时娘一甩门帘,走了。过了几分钟,娘进来把一只提篮塞给他。里面有一把香,一沓黄纸。娘说,你俩好歹同学过,想去就去吧,既然去,就有个去的样儿。
他佝偻着坐在床边,瞅着提篮不作声。
娘说着,在他对面坐下,拿起衣角来擦擦眼角,说,这女娃子命苦啊,打小爹娘挖药跌下山崖,连尸首都找不到,后来一直跟着那个姑过。再后来嫁到村支书家,别人都说,她可算是进了福窝了,可还是——唉,她也是,都读罢高中了,心还这么傻,让男人蒙得这个惨啊,钱没了,命也没了。
越野车进了村,七拐八拐一番后停下了。哥,到了。司机指着路边一处院子说。他下车,站在路边,打量着这院子。
这就是她家,她嫁给村支书的儿子时,这儿可是附近几个村唯一的三层楼房。他想起了大三时收到的那封信,她说自己有了一间带阳台的书房,上学时的书,打工这两年买下的书,都有地方放了。信里那张照片,就是她在阳台上拍的。
院门早卸走了,他进了院子。院子里到处是砖头。司机跟了进来,把提篮递给他,笑着说,农村都这么干,当时听说哪怕是拿破砖烂草席子搭间房,就能在县城里按比例换楼房,于是家家户户就赶紧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房。
这话,娘从前在电话里也给他说过。娘说,水位线以下要搬迁的几个村子,大半都假离婚了,为的是多分一份宅基地,等有了宅基地,只要突击多盖上房子,到时也就能多分房子。说到这里,娘的语气也含糊起来,试探着说,娃儿,咱家的院子空着也是空着,不如……
他马上冲着话筒说,娘,可别听这些馊主意,咱家不能干这种私搭乱建的违法事儿。娘听他说得坚决,只好怏怏答应着,万分遗憾地说,村里好多人家都这么干。反正山里石头多,树多,村里人一分钱不花,就能把自己家院子盖满。就在娘挂断电话前,他听见爹在朝娘幽幽地说,咱娃儿在惦着前程哩,咱可不能给娃儿拖后腿。他的脸,立时就通红了。
此时,他抬起头,看了看三楼那个有阳台的房间,回头对司机说,村里人的坟地是在哪儿?司机似乎看出了他的来意,脸上的笑又多堆了一层,说,这个村的坟地,就在咱刚路过的那道山崖底下,前一阵子搞截流蓄水试验时已经淹了。这家从前的那个年轻媳妇,本来她离了婚,按农村里老规矩,就不算这个村的人了,但墓地是按户口分的,所以还有她一份。我听说是她从前的男人出钱出力把她火化的,还在村里墓地给她起了坟,立了碑。人家是支书家的小子,要说为人处世,还真不是平头老百姓比得了的。
他站在院子当中,用脚尖拨拉着地上的砖头、木片,默默听着。
仁义,真是个仁义孩子,提起这事儿,村里人都这么说。司机还想继续说,他摇摇头表示不想再听了,就拎着提篮上了楼。
那时,他们白天各自在家温书,吃罢了晚饭,就到乡里中学上夜自习。当初是他先来的。入冬后,没了农活,加之电视信号不好,山里各家男人的娱乐就只剩下打麻将和打老婆。他受不了那声响,索性每晚走个把钟头山路,到乡里中学来,央求看门人给了教室钥匙,就进去温书了。
他来了没几天,她也来了。那天他进了惯常在的那间教室,她早稳笃笃地坐在里面。他愣了愣,也就寻处桌凳坐下,铺开了书本。
乡里中学条件差,晚上没炉子。他倒没什么,可她坐了没多久,就开始打喷嚏。第二天,他把自家的一个漏底搪瓷盆带了来,柴火也是他一路上捡拾来的。进了教室,他拿出火柴,拼命回忆着爹和娘生火的动作,小心擦着了火,好容易点着了最薄的木片。木片渐渐变得黑黄了,可火苗还没出来,烟已经灌满了教室。
他直起身子咳嗽起来,眼瞅着已经有几株小火苗在盆里微微露出头。这时她一路咳嗽着跑过来,啪啪啪几脚跺灭了火苗,接着抱起搪瓷盘,跑了出去。
你想把教室烧了啊?她拎着空了的搪瓷盆回来了,脸上是一道道的灰,脸旁边的几根头发被燎得卷了。
她说,你啊,是爹妈惯大的吧,在家啥活儿都没干过吧?
他点点头。哼,书呆子,明天看我的。她说着,从书包里抽出手帕,擦过头脸,又拿出小圆镜子,左右照了好一阵子,才又看起书来。
第二天,他到了教室,她已经在里面了。教室里热了很多,她在搪瓷盆里放了木炭,木炭发出的,是那种柔柔淡淡的暖,不像柴火,是让人心里发慌的燥。她把搪瓷盆放在过道中间,过道一侧是他惯常的位置,她则坐到过道另一侧。
后来,过完年,又出了正月,冬天最冷的那一阵子过去了,山里向阳的那一面山崖,渐渐有了毛茸茸的绿。一天,她一进教室,就摘了绒线帽子,露出了一头的披肩发。他记得县中的规矩,是不让女生留披肩发的。高一时,有次他在学校澡堂门口见过几个女生说笑着出来。他站在她们走过的空气里,洗发精的味道不由分说地钻进他的鼻孔。他看到她们的披肩发潮潮的,软软的,仿佛没有任何重量一样,在晚风里轻轻垂拂在各自的肩膀上。他记得就是在那晚,他迎来了生平的第一次梦遗。这天,她骄傲地甩了甩头发后才坐下,那发梢险些蹭着他的额头。一整个晚上,他都觉得炭烧得格外热,烤得他半边身子热乎乎的。
过了一阵子,真正暖和起来了,她就不再带炭了,他也把搪瓷盆拿回了家,但两人还是隔着过道坐着。温书累了,就说上一小阵子话。又过了没多久,发生了两人在河边亲嘴的事儿。那天,他回了家,一晚上没睡,始终瞪着眼睛望着泥屋顶。黑暗当中,泥屋顶上放起了电影——爹背着装满板栗的口袋,为了省下两块钱车钱,弓着脊背走在通往县城收购站的路上;天刚蒙蒙亮,娘在河边砍猪草,一个趔趄,装猪草的筐子倒了,她在水里扑腾着去够越漂越远的筐子,全身湿得净透;高考分数公布后,自己落了榜,捂着头蹲在县中门口痛哭……
第二天,他没去乡中学温书。
第三天,他还没去。
一直到了第七天,他才去。进了教室,就看见她正在老位置坐着。她扬脸朝他笑着,他不敢看她,慌里慌张地到了最后一排坐下,背靠着冰凉的土墙。
她忽地一下转过身子,瞪着他。他脸色惨白,把书一本本掏出来。
你什么意思?她喊他的名字。
他几乎哭出来,把头抵在桌板上,喊——俺得上大学,俺爹俺娘让我上大学!他嗡嗡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着。她慢慢转过身,坐了下来。
他记不清多久后,两人才重新说起话来。这道题怎么解,她拿着一册习题集,腾腾几步过来,把书按在他面前。
他看完了题目,放心了。这题,他会。
你打算报哪儿?解完了题,她问。他说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你呢?他问。
能到省城上个师大,我就满意了。她说。他估摸着她的学习成绩,觉得她就属于老师嘴里“有希望,没把握”的那种情况。
3个月后,两人再次参加高考。后来,成绩公布,他考取了第一志愿,她则又一次落榜。就在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被姑姑带着进了县城,当上了服务员。
大一大二那两年,因为不舍得把钱花在路费上,暑假他都留在北京打工,寒假才回来。回到村里,他虽然没有去刻意打听,但总会有零零碎碎的消息传进他的耳朵。他知道,她先是和姑姑当了两年服务员,后来有人在青海给姑姑介绍了一个男人。姑姑正犯愁要不要把她带去时,她们那个村的支书,遣了人给自家小子做媒,她答应了,就回了山里。
大三时,他能挣稿费了,也寻了一个女朋友。这时,他意外地收到她的信,信里说她要参加自学考试,央他寄书。信里还有一张照片,是她站在阳台上,摆出一个《泰坦尼克》里女主角的姿势。
他真的给她寄过不少书, 可没多久,她来信说,她公公去南方考察时染了病回来,婆婆就住了她这间书房。再后来,她就不让他再寄书了。可他还是又寄了几本。这几本却都被退了回来,他就不再寄了。进了大四后,他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成绩很好。于是在毕业后进了部里,当上了公务员。
参加工作三年后,他分得一套二手的一居室。消息传回山里,点燃了亲戚们来北京旅游观光的热情。亲戚们来了之后,因为影影绰绰知道他和她的事儿,也都会影影绰绰地说起她。那时,说的都是好消息。
——她命好哩,早上村里卖豆腐脑的,卖炸油条的,都给她家送。山里兴“农家乐”了,老有县城里的人,开车来山里,哪个村子偏,离着城里远,这些人就爱往哪个村子去。她那个支书公公,把那个村村委会后面那一排平房改成客房了,每间房里都有彩电席梦思啥的,可客人还不满意,说得上网。支书么,啥事干不成,马上说村里要搞信息化办公,给村支部通上了网线,顺便也给那些农家乐通上了。
后来,他又听说,支书嫌“农家乐”来钱慢,就带了人去南方考察。那个刨花板厂,就是支书从南方考察回来后盖的。后来,刨花板厂把山里的溪水弄污染了。这溪水流出了山,流到县城就成了河水,溪水有污染就是河水有污染,这下县城里的人不答应了,县里环保局派人来查,查完说厂里污染排放超标,强行把厂子关了。这时支书就说厂子其实不是他家的,是村办企业,办厂子赔的钱就都成了村里的欠账了。
因为水被污染了,城里也没人来“农家乐”了。她本来当着“农家乐”和刨花板厂两处的会计,如今也闲了下来,就开始专心致志准备生孩子。她一连在家待了三年,都没怀上。两口子去县里检查,啥毛病都没查出来。后来又去市里大医院查,一连查了好多天,最后说是她的问题。医生说,因为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她已经不能生育了。
就像得到提醒似的,那几年,村里的人才明白过来,自打建了刨花板厂,村里的确没有哪个年轻媳妇怀上过孩子。
水库的事儿,也是这个时候传开的。
开始,亲戚们都很不安,一到北京,进了他家门就开始谈搬迁的事儿,语气里满是惊慌。去年,大伯两口子送刚考上大学的堂弟来北京,他在小区里的饭店订了位置,还要了烤鸭。大伯说,山下的几个村子已经开始征地了,有人要现钱,说自己是农民,就会种地,要拿了钱到山里别的村子去赁地种,大部分人要的是县里的房子。
凡是要房的,都假离婚了哩。大伯说。
假离婚?
离婚了,就是两家人了,就能多要宅基地,多要房了。
他问,你家是怎么打算的?要钱,还是要房子?
大伯看了看他,刚想说些什么,却又赶紧低下头。他看到了大伯眼里的羞怯。
还用说啊,当然是要县里的房子。堂弟从手机上抬起头,不满地横了他爹一眼,从他娘手里接过了刚卷好的鸭饼。
就是,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也种了大半辈子地,可不想再种了,得到城里住楼房享福了。大婶说。
能住在县里,好是好,可一家人吃啥?大伯说。
干点啥买卖不比种地强?再说城里有低保,饿不死你。堂弟说。
第二天,他找同事借了车,带着大伯一家三口人去看长城。大婶忙着给堂弟照相,他和大伯走在前面。到了一处城楼,他拐弯问起她的事儿,大伯说,她和老公也学旁人离婚了。那一阵子,她家的门还整天关着。别人想去给她公公送礼,打听些搬迁政策的事儿,都是她或者她婆婆从门口出来,和来人聊上几句,再把装着炖山鸡的提篮接过去,不让来人进门。村里人慢慢就起了疑,直到有天村里有人到对面山上采蕈子,看到她家院子里满满当当盖满了房,这才恍然大悟。只一夜间,村里家家户户都这么干了。
大伯说,测量组进了村子后,她公公又把“农家乐”那排房子打开了,让测量组的人住了进去,他们每人都住单间,顿顿饭都是到她家吃。她男人带人在山里打来穿山甲、野山鸡,从县城买来好酒,不断顿地供着测量组吃喝。吃喝还不算,那些人还在她家的大客厅里唱卡拉OK。那组长唱歌唱戏都拿手,还好和她对唱,唱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再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段真感情”。她男人和她公公忙着给别人倒酒布菜,得空便在旁边拍掌叫好。
前天晚上,他进了家门,爹娘给他包饺子,爹擀皮,娘包馅。娘叹着气说,大伯大婶自打上次从北京回来后,就决定要房子了。他们本来也打算离婚,后来到了乡里,大婶忽然哭天抢地,死活不肯进乡政府的门。大伯怏怏骂着,两人买了些农药化肥,就回村了。
听完大伯大婶的家事,他就想打听打听那桩关于她的新闻。他才提了她的名儿,爹就把擀面杖往桌上一拍,说,天杀的那一家人,骗人家姑娘骗得真狠。当初她家一口气在县城里得了三套三居室、一套两居室,填的都是她公公和她男人的名。从山里搬进县城的十来个村,就她家得的房子多。
娘说,分房子的大红榜,在村头贴出时,她没事儿就在跟前站着,就等着别人给她说一句,你的命真好,马上就要进城住大房子哩。只要听到这话,她那眉眼神情,可美气呢。
他皱着眉说,她离了婚,分给自己的房,咋还填别人的名?
娘说,分房子时,她男人靠她的宅基地多分了房。可到了打房本时,那男人一家人都故意不提离婚的事儿,硬是在房本上填了男人的名儿。
这时,二舅和二舅妈来串门了。爹出门去买下酒菜,二舅妈进了厨房接了爹的活儿,二舅和他坐在客厅里,白嘴喝着酒等饺子上桌。只喝了两盅酒,二舅的耳根就全红了,说话时舌头也大了不少。他模模糊糊提到她,一听她的名字,二舅就直摇头,说,她那男人也不是人,自打住进了县城,天天晚上日弄她。她也得意,叫得整个小区都听得见。
后来,等四套房子的房本都到了手,她男人就开始不着调了,整天张罗着和一些县城里的女人见面。有人给她说了,她开始不信,可县城有多大,她到底还是看见了好几回。有一回她男人实在过分,就在她打工超市对面的“肯德基”和女人见面。晚上下班回了家,她问她男人。她男人说,咱俩早离婚了,你还想管我?
她说,离婚行,除了她那套房子,还得再给她10万块钱。她男人当场笑得没背过气,说,啥叫“除了她那套房子”,这四套房子是补给自己家的,和她一点儿关系没有。她说,房子是按照宅基地补的,她的宅基地就在那个村子里,凭啥没她的份?她男人说,这四套房子是离婚后才有的,是他独个儿的婚后财产,她想上哪儿告,随便!
她当时就开始在家里连摔带砸的,刚买的平板电视都被她砸了。那男人恼了就揍她,她被揍得跑出门,在楼底下又是哭,又是叫,哭得都晕过去了。幸亏住她家那个楼的,都是当初一个村的,有人看不过去了,就给她出主意,让她上县里拆迁办要个说法。她去了,可人家说,搬迁补偿方案早就公示过,要有意见的话,得在异议期提,这时候早过了。这闺女气性真大,出了拆迁办,她就找超市老板辞工,说这口气咽不下去,要和那一家人打官司,让超市把工钱给她结清了。
他问,她拿着钱了吗?
二舅嗞儿的一声,把盅里的酒喝完,这才说,那个超市老板告诉她,因为她总是算错账,所以要扣工资。就这么七扣八扣的,她干了三个多月,拿到手的才1000多块钱。这点钱当然没法打官司。后来,有那么几个月,谁也没见过她。有人说她去了青海找她姑。可她那个姑父,说是个农场主,其实是个刑满释放的。那人对她起了歪心,老想着占她的便宜,她姑也怪她,她在青海待不下去,就回了县城。还有人说她去了省城,想打工挣钱,好和那一家人打官司。可她找不到工作,手头的钱又花完了,就只好去当鸡。后来倒是挣了一两万块钱,刚想回县城打官司,就又赶上省城扫黄,她挣下的钱,全都交了罚款。
总之,在大概半年的时间里,她在县城消失了。她再次在县城出现时,是在她从前的男人结婚那天。那天中午,那个男人包了“富丽都”办婚宴,正和新老婆给县里的领导敬酒时,她不知道打哪儿冲了出来,抓起一盘子菜摔在那男人脸上,又扑上去在他脸上抓啊,挠啊。她从前的公公叫保安把她赶出去,她不等保安动手,就自己跑了。这一跑,人又不见了。又过了一个礼拜,人们才在县城边上的河里发现了她。有人说,她是直接从县城跳的河;有人说,她是从山里跳的,后来给冲到了县城。
二舅刚说到这里,爹拎着一塑料兜子猪耳脆进了家门,娘接了拿进厨房去切,二舅妈把刚出锅的饺子端上了桌。二舅也就住了嘴,慌忙吃起冒着热气的饺子来。
在阳台的角落,香和黄纸都烧得差不多了,他望着正徐徐熄灭的火堆,把那张照片也扔了进去。照片迅速卷了起来,从中间冒出了细细的火苗。他又看了一会儿,就抬起头,朝村子对面的一排排大山望去。那道水位线就画在对面的山崖上,比刚才在路上看到的又近多了,清楚多了。这道油漆血红血红的,霸道地横在大片石灰岩上,把一些长在石缝里的荒草都压住了,像一根肿胀的舌头。山崖后面,太阳正摇摇欲坠地挂在那里。他知道山里太阳落得快,天黑得早,也就把双手揣进裤兜,慢慢走下了楼梯。
司机见他出来,赶紧打开了车门。车开动起来,距离村子渐渐远了。山崖的阴影把车和路都罩住了,他坐在车里,也觉得有些凉了。他想,不能把年假都扔在这里,还是得早些回去,打听明白是谁当了处长。山里,自己终究是不会再回来了。
邱振刚,男,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学硕士,现任职于中国艺术报社。业余从事小说、散文、影视剧本创作。在《创作与评论》《中国作家》《作品》《广州文艺》《西部》《上海文学》等发表多篇作品,作品曾转载于《小说选刊》。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多次获得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铜奖。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