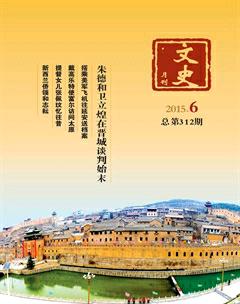任鸿隽与四川大学(连载)
智效民
三、任鸿隽的改革措施及其成效
四川大学成立后,校务由省政府整理大学委员会代行。1932年2月,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任命王兆荣为首任校长。王上任后,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不懈努力,但因经费等问题不易解决,使他心力交瘁,最终于1935年8月辞职。随后,国民政府任命任鸿隽为四川大学校长,并要求他尽快到校处理校务。9月初,任鸿隽飞抵成都正式上任。同年12月,他把家搬到成都,只把上中学的大女儿任以都留在北平。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任命任鸿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他没有就任。1931年,他回四川考察成都大学,希望四川的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这次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难当头,“乃不得不奉命驰驱”(《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7页)。当时的四川在蒋介石的策划和刘湘的经营下,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或北上,取消了原来的防区制,并决定军费由中央直接划拨,从而使学校经费有了保证。因此,任鸿隽在1935年5月向记者说:“‘国立四川大学在西南方面极为重要,彻底整顿,数年来即有此计划,亦实有此必要。唯以往四川政局不定,整顿计划殊难实现。’现在,防区制被打破,整顿川大计划乃趋于实现。”对于任鸿隽的到来,当地舆论也好评如潮,认为任鸿隽是我国学术界少有的人才,他入主川大,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也会给四川文化带来转机。
上任后,他明确提出四川大学的两大目标和三大使命。两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三大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与此同时,他还把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以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当地报纸认为新校长“是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四川大学史稿》第178-180页)
与梅贻琦等人一样,任鸿隽也认为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请著名学者当作头等大事。他认为原来的教师队伍有两个问题: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亲繁殖的危害;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陈旧,方法不当。因此他宣布重新发放聘书,没有得到聘书的可以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他四处聘请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1936年9月,任鸿隽在开学典礼上说,经过一年努力,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
一是学生人数大大增加,由原来的4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新生中外省籍学生比例很大,这种做法与国外大学招收外籍学生一样,有利于大家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增进友谊,也与“国立化”目标完全一致。
二是新聘一批教授,其中有担任过厦门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颐,有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的闻宥,有分别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戴家祥和萧涤非,有刚从英国归来的外文系教授钟作猷,史学教授范祖淹、教育学家张敷荣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刘绍禹,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过化学研究所所长的王季梁,有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光学专家张宗蠡,有在比利时研究法学的刘雅声,有在浙江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程复新,还有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从美国归来的体育系教授黄中孚……前后来川大的还有曾经担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桂质柏,曾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大杰,著名生物学家钱崇澍等数十人,这些人均为一时之选。据当年曾在这里就读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回忆:“那时的四川大学很注意教师阵容,尽力网罗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学者来校执教,学校办得很有生气,一时蔚为蜀学中心。”(同上,第183页)
三是校舍和教学方面有所变化。在校舍方面,任鸿隽经过调查,草拟了一个三年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30万元,先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再将原校址皇城改建成一个大学城。在这个开学典礼上,任校长说虽然经费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校舍改建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马上就可以动工。1937年4月,任鸿隽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校址定在望江楼附近。不久,新校舍破土动工,后人称这一决策很有远见(《四川大学史稿》第199页)。在教学方面,任鸿隽认为课程标准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要注意打好基础,“即在第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二要注重培养学生自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出“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学生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科学救国之梦》第545页)
任鸿隽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政法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叫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叫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期,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187页)。在他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在这方面进步很大。以农学院为例,该院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在开展双季稻栽培试验、引进优良品种、调查柑橘生产和其他农业资源、改进植棉技术和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他们主动成立各种研究会探讨学问,从而大大增强了学术氛围,丰富了校园生活。据说“从1935年到1936年下(半)年,除王兆荣时期已成立的研究会外,新成立的研究会有英文研究会、史学研究会、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演说辩论会(分国语和英语)、奖励论文会、法律学会、体育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经济地理研究会、政治学会、数学研究会、物理学会、化学研究会、生物学会、农学研究会、园艺学会、植物病虫害学会、蚕桑学会、农业经济学会、农业教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青年问题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青年写作协会川大分会、新闻学会、歌咏戏剧社、绘画研究会等。许多学会的学术活动搞得十分出色,成绩卓著。”(同上,第191页)这就是任鸿隽“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内容。可见他不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当作一个为我所用的口号,更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整人手段。
四、任鸿隽的辞职与晚年遭遇
任鸿隽锐意革新,有目共睹,成就很大,因此,获得了教育部传令嘉奖。正当四川大学步入正轨,并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时,突然传来正在南京的任鸿隽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的消息。川大师生闻讯后,文学院院长张颐与76名教授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任鸿隽,进行挽留。全体学生也召开大会,并致电任校长,要求他继续主持校务。电报说:“本校自先生长校以来,校务蒸蒸日上,全校师生额手称庆。近闻先生忽将引退,群情惑然,现值本校正谋发展之际,尚非贤者高蹈之时,万恳早日回校主持校务,不独本校,亦国家民族之幸也。”(《国立四川大学一览》,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209页)但由于任鸿隽去意已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于1937年6月签署了同意他辞职的训令。
任鸿隽的辞职原因很多,细说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他要广纳名师,并反对把四川大学办成一个闭关自守、近亲繁殖的地方性学校,就必然辞退一些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的四川籍教师,这就引来不少人的反对。据说他上任时,曾宣布前任校长聘定的教授不算数,要另送聘书,无聘书者可以自谋出路。这一措施在教授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教授公开表示反对。这次反对虽然无效,但也为后来埋下隐患。
二是其夫人陈衡哲的有关文章引来恶意攻击,也是导致他们愤然离去的一个重要原因。陈衡哲是江南大家闺秀,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庚款女留学生,第一位北大女教授,第一位成功地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第一位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女学者。1936年2月,入川不久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一封给朋友信的公信》,披露她一路上的经历和到达四川后的见闻感想。这是一组分四次写成散文,分别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90号、195号、207号和216号。陈衡哲是文章高手,这组散文至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第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这次远行极不适应。比如在重庆吃饭,就辣得难以下咽;从重庆到成都,因为天气不好,被折腾得够呛;到了成都以后,正值冬天,因为行李未到,房子走风漏气,又买不到火炉,让她大病一场。这一切,都让她对四川产生不良印象。几个月后,她发现这里大多是阴天,太阳难得一见,因此不仅对“蜀犬吠日”有了深切体会,而且还对云南有了真正的理解。她说,由于四川总是阴云密布,因此所谓“云南”,就是“云天云地之南”了。她还幽默地说:“‘四川’的名字不很恰当,因为一省之中,川流何止千万,哪能以‘四’为限?倒不如把它改为‘二云省’更恰当。”(《独立评论》第195号第16页)为什么要改为二云省呢?她解释说,因为除了天气多云以外,当地人还喜欢吞云吐雾(指吸食鸦片)。
如果说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还是个适应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落后和政治腐败则让她更不能接受。在《川行琐记(二)》中,陈衡哲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四川的落后。一是小孩子到处拉屎、砸汽车玻璃,没有教养;二是女学生“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三是许多人吞云吐雾,不把吸食鸦片当作可耻的事。她认为四川的落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二是鸦片。只有彻底销毁鸦片,人民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才能对军阀统治来个釜底抽薪。《独立评论》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这一期里有两篇文字都是写四川的现状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云’写的是四川在那双层密云笼罩之下的黑暗。‘寿生’先生的‘二十三年代’里面写的那个黑暗惨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名虽然是捏造的,读者当然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同上,第21页)
陈衡哲的文章发表后,社会上反响很大。赞成者说:“您太客气了,若由我来写,哼,我不能仅仅说那么一点。”有人甚至说:“这位陈女士真不知道黑暗哩。她那(哪)知道比她所说还要丑恶,还要壁垒森严的四川内地的情形,她说得真太少了。”还有的说:“您是外省人,您可以说真话,我们可不敢说。我们一开口,人家就骂,‘为什么你不投胎到外省父母的肚子里去呀!’”但是陈衡哲在《川行琐记(三)》中说:“这位朋友不知道,外省人说真话,也一样要挨骂的。”(《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8页)当地的几家报纸甚至把这件事当作重要问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并假造学生来信,说陈文是颠倒黑白,污蔑四川人的人格。对于这种状况,任鸿隽不得不在《独立评论》第215号发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说明言者无罪的道理以及陈衡哲的幽默和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陈衡哲以她敏锐的感觉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有人以为她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发牢骚,她辩解说:“我们这一群人在此的最大困难却也并不尽在物质和环境上,虽然我们对于有些情形,有时也感到难受,但一想到现在正在被人吃,或吃他人之肉的四川灾民,想到四川内地人民的流离困苦,我们也就怀著一颗惭愧的心,自动的去和环境妥协了。”她还说,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员中,有一群非常努力的人。她觉得:“在一个受过军阀蹂躏的社会环境中,竟能找到这样一群手持火把接前导后的朋友们,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钦敬”。(《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9-20页)
大约在1937年年初,陈衡哲离开四川,先行回到北平。她的离开,可以用她自己在《川行琐记(四)》中的话来形容:“一个受过教育者的最重要的品性,第一是自尊。他不能让一个在泥里打滚的人,把他也拉到泥里去。”(《独立评论》第216号第8页)在这篇文章里,她还讲了两个爱管闲事的故事,大意是管闲事本意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却受到对方的责难。这明显地表达了她在四川的处境。不过,她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撒手不管。因为好人不管闲事,会让罪恶增加。因此她的大女儿任以都说:“我想家父离开四川多少是有点遗憾,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但我设身处地来假想,倘若我抱著一腔热切的期望,想要建设一番事情,结果却不欢而散,自然也会感到很失望。但他始终不谈这件事,只是淡淡地说,事情既然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能做的就这么多,以后就让他们接著办罢!”
任以都还说:“那时的四川,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来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加上家母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没想到后来抗战期间,又到四川住了好些年。”(《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89-9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另外,从陈衡哲去四川没有退掉北平的房子来看,她本来就没有做长期打算,因此他们的离去,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任鸿隽夫妇去香港将子女送往美国并交代了中基会的财产后,又返回大陆。随后他们定居上海,担任过一些名誉职务。任鸿隽回来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维持中国科学社及其事业,但是从1950年至1960年,中国科学社及其所属《科学》杂志、图书馆、研究所和所有房产资金,一个也没有保住。到了1961年11月9日,75岁的任鸿隽与世长辞,可以想象他走的时候心情多么沉痛!
1962年,长期被眼病折磨的陈衡哲应子女要求,写了《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其中谈到多年前任鸿隽曾经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上,第194页)这一细节也许有助于解读他们夫妇离开四川的原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