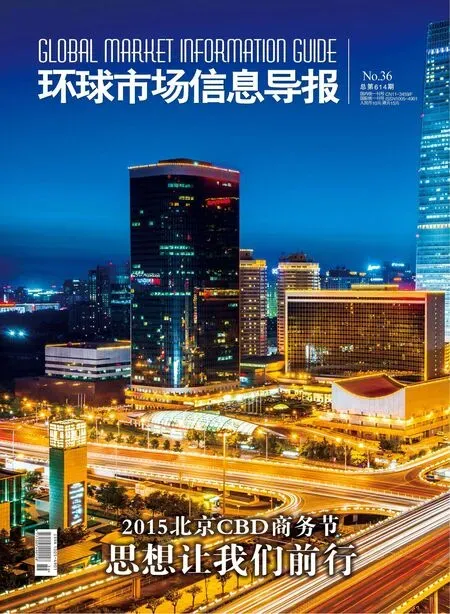张爱玲的后半生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三个月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经广州搭火车抵深圳,从罗湖桥出境到香港。这年她32岁。
话题和价值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三个月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经广州搭火车抵深圳,从罗湖桥出境到香港。这年她32岁。她22岁时,因为香港沦陷于太平洋战争而自港大辍学返沪,10年后以申请重读完成学业的理由获准赴港。等到移居美国后的1963年,张爱玲把这段经历用英文写进过一篇散文《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美国《记者》杂志发表,1982年以中文又重写一次,里头的回忆场面就像是老电影镜头自带着年代的张皇: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张爱玲和其他等着过境的人都站在太阳地里等着,不肯听警察的话到旁边小块阴凉地去。“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就这样,自1952年再回香港至1995年逝于洛杉矶,张爱玲在海外的写作生涯绵延了43年,至少在长度上已超过她的上海时期。2010年张爱玲诞辰90周年的时候,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举办了规模较大的纪念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张迷”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晚期写作:她是一个夭折于历史大转身之后的华语传奇,还是隐居海外却仍旧保持杰出水准的写作家?或者,还有另外的答案。
2015年9月,在张爱玲去世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记者分头去踏访她在香港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生活过的地方,访问她的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哈佛学者王德威、大陆研究者止庵等人,目的是要通过谈论张爱玲和她的后半生,使我们有兴趣重新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忠于天才和孤独的一种写作者,“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张爱玲:《写什么》)。
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华语文坛“张爱玲热”大体经历三波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早期,她不过20多岁,即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横空出世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坛。1943年的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星期后,周瘦鹃告诉读后感: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她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传奇》出版四天即告售罄而再版重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曾提到,写过长篇《风萧萧》、中篇《鬼恋》而风头甚健的作家徐訏194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有人介绍他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可见张爱玲当时名气之盛。徐訏批评张爱玲“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但同时期还是有不少文人视其为天才。1944年,专门研究女作家的学者谭正璧发表《苏青与张爱玲》,评价张爱玲,《金瓶梅》和《红楼梦》“给了她无限的词汇,不尽的技巧。所以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替,也成为作者特殊的风格”(符立中:《张爱玲大事记》)。

抗战胜利后,因与“附逆文人”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缠,加之自己作品中从无亡国之痛,张爱玲在文化界声讨汉奸的声浪中备受压力,有几年几乎停止发表作品,只和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合作写些剧本,然而1947年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大卖,又让她回到文艺界的中心。1950~1952年,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先后在上海《亦报》连载小说《十八春》和《小艾》,是她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之前的最后作品。《十八春》仍旧成功,1967年由她在美国改写为《惘然记》重新连载于台湾《皇冠》杂志,后来出版为单行本时又更名为《半生缘》。
第二波“张爱玲热”大概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1961年发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给了张爱玲42页篇幅,并将她排到鲁迅之前,甚至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华语文坛一时耸动。1965年,经香港朋友宋淇介绍,张爱玲开始将旧作和新作陆续交平鑫涛的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时皇冠因为刚刚出版了琼瑶言情小说《窗外》等书而拥有大量读者。前后这两件事情,令在美国几近隐居状态的张爱玲再次走红台湾和香港文坛,报刊请人追访张爱玲,女记者“翻垃圾”事件即发生在这段时期。直到90年代,两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获奖又走红,一部是关锦鹏的《红玫瑰和白玫瑰》(1994),另一部是许鞍华的《半生缘》(1997)。在第二波热中,80年代中期,北京《读书》和上海《收获》先后发表柯灵的怀念文章《遥寄张爱玲》——40年代张爱玲曾在他主编的《万象》上发表小说《连环套》。同时《收获》还刊登了《倾城之恋》,是内地在张爱玲赴海外后第一次正式发表其作品,自此她在内地也重新进入大众阅读,并不断升温。2005年之后的第三波热至今未退。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都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新的文学遗产执行人,陆续授权出版了她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围绕遗稿究竟是否该出版莫衷一是,尤其是2009年出版的1976年即完成的《小团圆》更是争议纷纭,书中有大量情节让人无法不联想原型胡兰成,但出版行为本身带来的作品热销及话题效应毋庸置疑。2007年,李安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色·戒》上映,电影本身挑战尺度,也令张爱玲话题热度难消。据宋以朗2010年述:“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影响横跨两个世纪几个时代的“张风”,对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除了话题还留下了什么遗产?这种争论在她40年代少年成名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头。在现代中国作家里,张爱玲是唯一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张迷”对她的出身十分熟悉:父亲张志沂这边家族,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则是李鸿章长女。母亲黄素琼的家族也不普通,张爱玲的曾外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张爱玲自小到大都在写她的高门巨宅。6岁写了第一个故事,情节是年轻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设计了一个曲折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7岁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这样的人被世人视为天才并不奇怪。《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时期,她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后,到了美国晚期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她开始写自己。“写来写去都是同样的事”,但于张爱玲却是文字下的万般风情。她的写作其实就像她书中的人物,如作家格非评论《小团圆》里的九莉:“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过度敏感遇上了时世的纷乱,实际上它就是生活的赠与,就像止庵先生说到的人生的底子。”她在文中写尽一切关系: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无不彻骨清醒而到残酷的地步。关系背后并非感情,是世相,张爱玲一贯平静地低笑着,在一个个精心编织的华丽结之下抽出隐藏的线头,给人看那瞬间的一败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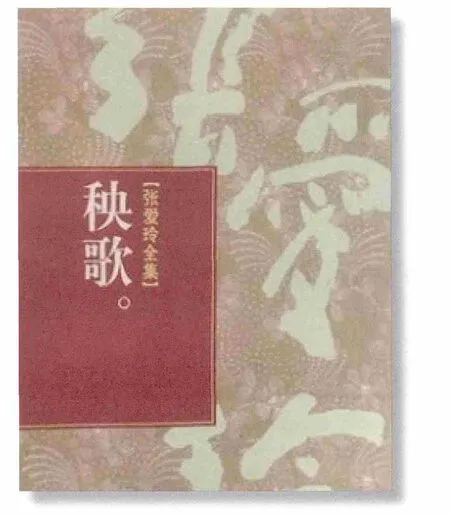
18岁那年,她被父亲毒打禁闭,逃到母亲和姑姑处生活,却发现母亲因她的累赘而脾气变坏。她不怕写出后来母女之间那种互憎和绝望:“越是痛苦,越是可耻。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狄奥尼索斯(Dionysius)说,有一种叙事风格,不以壮丽,而以优雅与精致取胜。张爱玲显然属于后者。但她的优雅也是张爱玲式的优雅,一切冻在冰层之下。以此而言,将叙述始终保持在零度的张爱玲是同时期其他女作家难以相比的。她曾列举自己喜欢的时代女作家,有苏青,有早期丁玲。但苏青的把握生活情趣难免流入俗套。丁玲在写《莎菲女士日记》时期大约是合于张爱玲偏好的文字性情,“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张爱玲语)。不过张爱玲到美国后,曾应允为一个研究中心撰写关于共产党女作家丁玲的论文,证明心里还是有她分量,后来因为研究资金没有申请下来才作罢。
海外写作的境遇
《秧歌》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后用英文写的第一部小说。1953年出版后,她主动寄了给胡适。1955年胡适回信,对《秧歌》评价甚高:“写得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今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对于《秧歌》以及一年后发表的同为长篇的《赤地之恋》,张爱玲写的序和跋里都隐约看得到写作者期待被外界了解和接纳的那一点急切,这和上海时期的张爱玲似已有了差别。1944年她在上海参加一个女作家聚谈会时,曾回答取材范围的问题,自信“女人在活动范围上较受限制,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但在香港写这两本小说时,张爱玲显得不像从前那样“无所谓应当”。
此时张爱玲已放弃在港大复学的打算,因为想到日本找工作,又错辞了尚在争取中的奖学金。她得到为美国新闻处翻译《老人与海》等文学作品的差事,并因此认识了对她后半生影响颇大的美新处的宋淇和麦卡锡。但翻译只是临时生计,张爱玲想用英文写作来进入美国文坛。《秧歌》中文单行本先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了,一年后英文版才经麦卡锡促成在美出版。《秧歌》的后跋里,张爱玲开头即写道:“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读者们我这篇故事的来源。这也许是不智的,认为一件作品自身有它的生命。解剖它,就等于把一个活人拆成一堆脏腑、筋肉、骨骼,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也并不能变成一个活人。”但接下来,她仍旧还是为小说里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一一说明来处。1954年10月,用中文写的《赤地之恋》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张爱玲写了篇三五百字的《自序》,仍在强调作品和真实之间的关系。“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倍。其实一个故事的真假当然与它的好坏毫无关系。不过我确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大约她也是想要说明此书并非如外界传言,是美新处给她下单的定制作品。
1955年11月,张爱玲由麦卡锡作保,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在谈到为什么张爱玲没有去伦敦投奔此时还在世的母亲时,宋以朗说:去英国的签证很难拿到,况且她也没有生存来源。而《秧歌》出版后,麦卡锡为她在美国找好了出版经纪人,《纽约时报》等报刊也发过对她的书评。在这个时候,张爱玲对于英文写作仍是有自信和期待的。
1956年3月,张爱玲获得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文艺营写作补助,在那里写成《粉泪》英文版。更大的人生变化是她在这里认识了和布莱希特关系密切的德裔左翼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不到半年两人即在纽约结婚。
到美国后的40年,尤其在丈夫赖雅去世之后,张爱玲基本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比上海时期更甚——那时候她还去参加女作家座谈会之类的活动。庄信正说,张爱玲怕与人来往,怕接电话,也怕收到信,因收了便要回,对于“一封信要写好几天”的张爱玲是一大心理负担。日常与她保持通信的,其实也只有几个较为亲近的友人:宋淇、邝文美夫妇、夏志清、庄信正。即便如此,她仍有几年才拆看一次信件的“荒唐行径”(张爱玲语),甚而在去世后,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还发现有些信件一直没有拆封,或者写好的回信并没有寄出。
前面提到的这几个名字,几乎是张爱玲晚年的全部私人交往——并非见两面的访问关系或工作、出版事务上的通信关系,而是真正和她生活保持长期交集的人。但这几个朋友如果来访,也会被张爱玲一再叮嘱先写短信寄来,说好大约哪天到,那几天她才接听电话,否则也是一概不听的。
宋淇夫妇和张爱玲识于1952年的香港,其时宋淇任职美国新闻处(USIS)项目翻译组长,因张爱玲去应聘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而开始交往。夏志清教授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据他记忆,1961年3月将著作寄给张爱玲,从那以后两人即该开始了通信,虽然都在美国,但不在同一城市,主要是通过信件往来,直到1994年5月。
庄信正和张爱玲认识得比较晚一点。196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筹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请曾是自己学生的庄信正代为邀请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在夏志清的推荐下,庄信正请了张爱玲,并且因为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格外郑重,特别请老师福伦兹出面亲邀,而张也接受了,她在那次会上谈论的是中国电影的话题。庄信正在1966年8月后曾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中国研究中心,三年后又推荐张爱玲接任他的工作遗缺,两人因此联系较多。1969那一年,张爱玲总共写给庄信正9封信,于她平日行事风格是不多见的。虽然对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提供诸多帮助,包括找工作、租房、采购生活用品这类琐事,但庄信正始终以后进身份自处,视张爱玲为导师。
另外一位和晚年张爱玲接触比较多的华人,是后来被张爱玲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他是庄信正在美国大学时期的同学,因为住洛杉矶,庄信正就托付他照顾同城的张爱玲,比如帮她寻找新的住处之类。
1995年9月8日12点半,张爱玲在洛杉矶家中被发现死亡,死因为心血管疾病——宋以朗指出,这个时间是洛杉矶警署出具的死亡证书上所写,并不是她死亡当天的日期,而是她遗体被人发现的日期。“其实去世了多少天,由法医来判断,但那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所以那些说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张爱玲在去世前三年的1992年2月14日就依照当地法律立好了遗嘱:将她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委托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她去世后,警察的通知电话就是打给林式同的。1995年11月,林发表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除了房东、警察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他是唯一到现场并看到张爱玲遗容的人。“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后来一些传记作者描写张爱玲死后“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穿一件赭红色旗袍”“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各种臆想性的文字至今还在网上流传,正是他们以“张迷”的名义,将一个本性孤独的作家附会到了猎奇和俗流之中。
夏正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以及林式同写的《有缘得识张爱玲》,都成为后来张爱玲研究者最倚赖的信史资料。
张爱玲在美国的写作,大多数仍是旧文翻写或加写。与美国40年生活有所对应的作品,大概就只有生前被她搁置而一直未交出版的2万字手稿《同学少年都不贱》。女主人公赵珏有她自己的影子,折射了她多年在美国的现实生活和感受。比如,庄信正忆张爱玲晚年的阅读大多是“时下流行的书,包括名人传记和侦探小说”,信中向他推荐过两本写肯尼迪家族的书,一本《A Bridge at Chappaquiddick》,讲总统之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醉酒车祸而致女助手淹死在Chappaquiddick的一座桥下,她评价“像好侦探小说,又可靠”,专门买了一本寄给庄。另一本《泰迪熊》,庄信正听她提到后去买了一本,却“看不下去,丢掉了”。张爱玲对肯尼迪家族的这种兴趣,在《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情节里就有了相应的情节,比如小说里写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时,女主赵珏正在洗碗,“午后一时左右在无线电上听到总统中弹,两三点钟才又报道总统已死。她正在水槽上洗碗盘,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乃迪(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这样对照现实的小说情节,在张爱玲后几十年里是比较少见的,多数时候,她都在改写或扩写旧作,或者如《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国语、英文版,是在对自己一生最心爱的读本做些研究和再译。

可惜这本《同学少年都不贱》连张爱玲自己也认为“毛病很大”,生前只寄给宋淇看过。从1978年写给宋淇的那封信看,她曾试着修改过几页,但没有寄出,后来也没再提起过,直到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举办“张爱玲遗作手稿特展”,《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才被公开披露。宋以朗在2004年授权皇冠出版了这部中篇。但论及对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的写作之文学价值的再评价,这部小说也价值有限。张爱玲在1978年8月写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自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于是在小说出版后,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都集中于“外界的阻力”到底指向什么?有分析说它是指张爱玲担心因这篇小说跟胡兰成间接产生纠葛——当时外界还不了解有《小团圆》手稿存在,这部小说2009年才出版。而大陆学者陈子善认为,“外界的阻力”无非是广义的泛指,即外界对张爱玲期待甚高。联想到张爱玲在和宋淇、夏志清和庄信正等友人的通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写作的压力感,陈子善这一解读应较为合理,即外界的期待令张爱玲感受到很大压力,也就成为写作的阻力。
1955年张爱玲到达美国。也成为她后期写作的一个时间界点:前期主要是三本英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和《怨女》。《秧歌》是英文版《The Rice-Sprout Song》先出,然后她自己翻译成中文出版;《赤地之恋》则相反,英文《The naked Earth》在后。《怨女》是她改写自己作品的一个开始。张爱玲把中篇《金锁记》扩展成英文长篇《粉泪》(Pink Tears),交给为她出版过《秧歌》英文版的纽约出版者Charles Scribner's Sons,却遭了拒绝。据庄信正回忆,此事对张爱玲“打击很大”。张爱玲后来将《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同样未能被美国书商接受,直到1967年这本小说才由伦敦Cassell出版社刊行,“此后直到她去世近三十年当中没有再以英文出书”。
但从她去世后被转交到宋淇夫妇手中的遗稿来看,张爱玲在《北地胭脂》之后也没有放弃用英文写书。综合宋以朗所述,他母亲邝文美作为遗产继承人,在1997年将张爱玲遗物中的一批手稿捐给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余留下一些在家里,其中就有几部重要的英文打字稿,包括:《海上花》译本,后来由孔慧怡完成,2005年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少帅》,2014年中英对照版由台湾皇冠出版;《雷峰塔》和《易经》,2010年出版了经赵丕慧翻译的中文版本。这说明晚年张爱玲还是没有完全打消让自己的写作进入英文世界的努力。
《雷峰塔》和《易经》都在60年代完成,没出版也是因为被美国出版社拒绝了。那么,这两部小说在她自己的写作上是否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呢?2010年授权将它们出版的宋以朗对此叙述得比较客观:“《雷峰塔》写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节背景类似《私语》《童言无忌》《小团圆》童年部分和《对照记》,但内容更丰富;《易经》主要写港战时的大学生涯,可视为《余烬录》与《小团圆》港战部分的加长版。”“出这两部小说,不仅为其文学价值,我也考虑到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
对《北地胭脂》张爱玲自己没有表示过什么,她在1969年写给庄信正的信中说:“这本小说倒是一个标点也没经人改过,除了印错,不像《秧歌》,英文本我始终看着不顺眼。”但以中文重新扩写《金锁记》的《怨女》,1966年在香港《星岛晚报》和台湾《皇冠》连载时,张爱玲本人很不满意。她在1967年1月1日给庄信正的短信中说:“连载《怨女》是没改过的,脱落字句又多,自己也看不下去。”关于这篇小说,她和宋淇在信中也谈论几次。
《半生缘》同样也是改写增补而成的作品。1950年,张爱玲还未离开上海时,在《亦报》副刊连载了新作《十八春》,第二年又出单行本。到美国后,她根据《十八春》改写了《半生缘》,1967年也是交给台湾《皇冠》月刊连载,两年后出版单行本。改动的主要是结尾部分,在《十八春》里,几个男女主角在1949年后都转变思想,报名去了东北投身建设。变成《半生缘》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
张爱玲在香港那三年,英国女作家韩素音以半自传体写的东方主义味道的小说正在走红。到美国后,她也不是不了解赛珍珠用中国为母题创作的那些小说如何受到出版商和读者欢迎。但是,张爱玲没有表达过想要效仿的愿望。在韩素音最风光的时候,张爱玲说:她不如我。在比较符合美国出版商口味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后,因为《粉泪》遭到拒绝,张爱玲没有再循这条看起来通顺的写作之路走下去,她重新回到自己在中国大宅里的传奇,直至她自己的那些传奇。然而美国出版商想要的浪漫东方故事,并非这样复杂而绝望的真正的旧式中国。张爱玲晚期用英文写的作品一再被拒,即便对她评价之高如夏志清,也认为张爱玲进入英文文坛的努力是失败了。
张爱玲知道以她的履历在美国找事很难,几次写信托请夏志清和庄信正帮忙,希望寻一个事少的工作,宁可工资也很少,这样可以有时间写作。她后来在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工作就不是全天,算是四分之三,她通常可以等到下午其他同事都下班了才去办公室。但这份工作也只做到两年就被解除了合同,至于原因,主要是她和研究中心主任、华人学者陈世襄相处不太好,递交的研究报告也令对方不满意。夏志清、庄信正都和陈世襄熟识,他们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两人的个性差异太大:陈世襄夫妇喜欢招朋友聚谈,而张爱玲素不喜社交,应付几次后便视上门拜访为畏途,导致生出误会。
张爱玲自己说过,她七八十年代后不再找事情做,唯一固定收入是来自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版税,每半年约2000美元,有时加倍,所以不会太宽裕,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有人传言的要捡纸皮过活。庄信正提起一个细节:张爱玲将美国每年4月报所得税视为大事,亲自填写,而且精打细算。她有次在信中告诉庄,付税时将头一年里买戚本《红楼梦》的钱算了进去并过了联邦税捐稽征处的审核,这令久居美国的庄也颇意外。那两年张爱玲在研究《红楼梦》,即后来结集为《红楼梦魇》的那些文章,所以托庄信正帮她从台湾、香港买书买资料,包括比较少见的影印本,从信中语气来看,这笔购书开销在她眼里是个大数目。
1995年9月26日,张爱玲被人发现去世18天后,在香港的宋淇夫妇收到林式同从洛杉矶寄来的一张遗物清单。林在信首告知:“受张女士之托,丧事将依其遗愿于九月卅日办理完毕。”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依她“遗体立时焚化”的心愿,林式同恰好在这一天将其肉身的全部痕迹从这个世界干净抹去。张爱玲不可能预测到自己会在9月离世,生与死这番巧合,让人感喟。她在文字里铺叙过的人生苍凉况味,都在此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