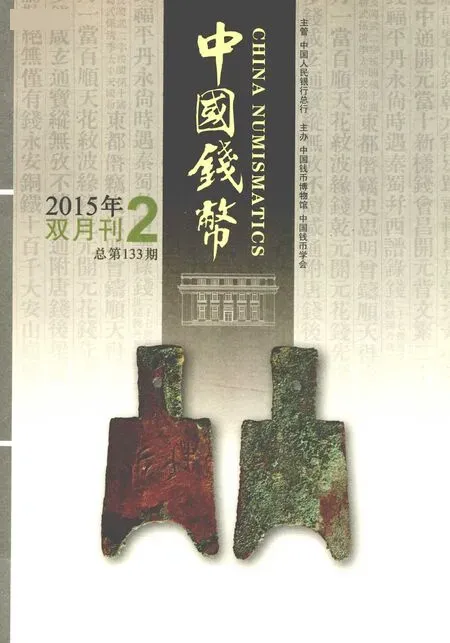谈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及云南护国公债票
徐渊
谈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及云南护国公债票
徐渊
一 一场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引发的护国战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2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当即辞职,推袁为总统。2月12日,袁世凯借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力逼迫清帝退位。次日,袁即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①。孙中山履行诺言辞职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继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并不满足临时大总统之称号,他要把民国变成帝国,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申令,并于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随即定明年为 “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②。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曾多次发表讨袁宣言,并筹组中华革命党,坚持进行讨袁斗争。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9月11日、10月7日、11月3日连开三次秘密军事干部会议,加快了武装反袁之准备③。12月17日,曾打响反袁 “二次革命”第一枪的原江西都督李烈钧携筹饷款数十万元自海外来滇④。而原云南都督蔡锷受梁启超策动从北京出逃后,亦于12月19日辗转抵达昆明。云南成了护国讨袁的策源地。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云南护国军政府,武装讨袁。反袁护国战争遂正式爆发。
袁世凯听到云南独立后,即派兵前往镇压。1916年1-3月,护国军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五省广大战场上与袁军激战,取得节节胜利,继云南独立后,又有黔、桂等多省宣布独立。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但却又把住总统宝座不放。护国军在要求袁下台的同时,起义各省还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联合组成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弃声中忧愤而死。之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于6月底宣布恢复 《临时约法》和民国二年的旧国会。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二 一张云南军政府发给刘登的护国公债收款证
讨袁护国期间,孙中山曾在日本印制中华革命党债券,以筹集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经费。此类债券,丁张弓良的 《中国军用钞票史略》有载⑤,安跃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孙中山在美洲发售的债券考述》一文中亦有介绍⑥。而云南护国军政府则以李烈钧为筹饷总局总办,黄德润、解秉仁为会办⑦。在 《中华民国护国军筹饷总局简章》中,将 “捐输、公债、股票”三种作为 “筹饷办法”⑧。唯其所发公债票实物则从未见披露。
不久前,香港钱币收藏家冯乃川先生向笔者展示了一批从海外华侨中征集到的早期军需债券,其中居然有一张民国五年云南军政府所发的护国公债收款证,引起了笔者极大兴趣,并索要了该收款证的彩色照片。
该收款证的花框、图案为红色,文字为黑色,额首为地球双狮及两面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图案,而此类图案,亦曾出现在民国三年富滇银行壹元纸币正、背之上⑨。在花框内上首,横列 “护国公债收款证”名称,下面自右至左,纵列文字为 “云南军政府为发给收款证事今收到刘登君应募护国公债西贡币银拾元正折合国币□元正合即先行发给收款证收执以便持此换领本公债券可也”其中 “刘登”、“西贡”、“银拾元正”为手书。后面为 “经募人”的签名盖章,所具日期为 “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四日”。收款证的右边有骑缝字号,其编号可识读为 “第壹佰贰拾贰号”。还有骑缝大红印章,因字迹不清,无法识读 (图1)。

图1
云南护国军筹饷总局把海外华侨作为重要的筹饷对象。据1916年3月20日越南张南生致唐继尧函,即提到 “滇省现行之股票、公债二种,欲于东京 (今河内)属内劝销,则以股票为宜。”他还提到云南派吕天民来越南西贡、堤岸 “察看情形”,“选择其能办事及地方上有势力者”发给筹饷 “委任状”⑩。在后来张南生所列 “越南东京、南圻等处筹饷人员表”中,“西贡、堤岸”即有吕天民推荐的 “马培生、赵桃之、邱应篆、李瑞芝”四人。信中提到的吕天民本名吕志伊,云南思茅人。1905年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辛亥云南光复后任都督府参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司法部次长。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员。参加 “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初在孙中山支持下返滇策动军事讨袁。被唐继尧聘为高级政治顾问,并派其于海外募款。再细审该 “护国公债收款证”上 “经募人”的两个签字,下面一字为 “手”字,上面一字则很可能为 “赵桃之”三字的组合字,意为由赵桃之所经手。
至于应募护国公债西贡币银拾元的刘登君,应该并不陌生,因为笔者曾在 《中国钱币》2011年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增刊上所发 《1911年同盟会之兴仁社发给刘登的筹饷捐款收单》中介绍过他:这位与兴中会老会员、檀香山商人刘登同名之人,乃是一位一直在越南经商的爱国华侨,曾于1910年加入南圻中华商务总会,其商号 “刘登记号”为五等小商号。1911年10月,他曾向越南同盟会分会为支援国内反清辛亥革命而设立的筹饷机构兴仁社捐款,并领到了捐款 “收单”。到1916年5月,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积极应募云南护国军政府的护国公债,并拿到了该公债的 “收款证”。
三 一批废物利用的云南护国公债票
既然云南军政府已先期印发了 “护国公债收款证”,并言明将来可 “持此换领本公债券”,那么,是否还有云南护国公债票之实物存世呢?云南钱币收藏家范昌明先生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范先生特地给我寄来了有关债券的彩色复印件,并在其来信中称:“遵嘱将所需资料图寄上。其中除云南护国公债伍拾元为完整券外,其余均为废物利用券,故难以确定其完整规格,仅供参考。”查所寄来的云南护国公债票,其中完整的伍拾元票,注明大小为233× 297mm,而拾元票及伍佰元票均为残票。上述三种公债票之背面,均有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为废物利用而印的各式表格。另外,范先生还附寄了一张云南靖国公债壹元票的残票。
现以伍拾元公债票为例,对云南护国公债票作些介绍。该公债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为息票,共十五份。上半部为额首有 “云南护国公债”字样的花框,花框四角有 “伍拾元”或 “50”的票值数;花框居中,为 “伍拾元公债票”票值;票值上方,有 “总额$20,000,000”字样;票值左右,有预留编号的长方小框;票值下方,自右至左,印有公债条例,全文如下:
“民国六年云南护国公债条例。前经督军、省长公布施行,兹将条例摘要如左:利率,周年六厘。息期,以每年六月付给一次。偿还期间,自发行之日起,居置十年。以民国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息,至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止,此五年以内,只付利息。又自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一日起,每年摊还本金十分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六月止全数偿清,但每年以六月内在省城执行抽签。保息,每年由财政厅预行筹措的款,发交富滇银行存储付给。担保品,本公债应付本息,由云南政府完全担任,并指定云南全省厘金、牲屠税、烟酒税及公卖费全数收入为担保品。还本付息机关,富滇银行总行暨各分行汇兑处及委托之殷实商号。用途,债票可抵交公务上之保证金。其到期息票,得以之完纳田赋、厘税及其他现款交售之用。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云南财政厅长。”下方为红色 “吴琨之印”。在公债条例中央,则盖有红色 “云南财政厅印”。
依据上述资料,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是该护国公债票乃由云南财政厅所印,计划募款二千万元。而债票之运作,则与云南富滇银行密切相关。
二是该护国公债年息六厘,完全清偿时间要至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六月,须整整二十五年。
三是从各张护国公债票的票面来看,其编号处均为空白,应是一批未完成票。
四是从该批护国公债票上所署之时间来看,已是中华民国六年 (1917年)七月一日,此时离袁世凯气绝身亡及护国战争结束已满一年。
五是由于1917年开始进入护法运动时期,再发行护国公债似已落后形势,所以云南财政厅又有了云南靖国公债票之印制,从所见壹元靖国公债票残件来看,其年息升至八厘,完全清偿时间只须八年。但其编号处仍为空白,应同样是未完成票。
六是这些公债票印成之后,因故而未曾发行,遂积存于富滇银行库房之中。1949年后,民国之旧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这批已作废的公债票便被印上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的各种表格,加以废物利用了 (图2、3)。
四 一个护国战争中云南并未举债的说法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二十三辑,载有缪云台先生的 《我与富滇新银行》一文。他在谈到 “云南财政经济恶化”时称:“民元以后,曾举全省之力,负担护国、护法两大兵役,省府既无外援,亦未能举债 (外债内债都没有),饷需来源全靠富滇银行发行钞票,连年超额发行,银行储备早已不足。另外,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也要靠富滇银行发行钞票。所以银行愈来愈空虚,币值贬落,更日甚一日。”缪先生于1924年受唐继尧之邀任富滇银行会办,唐去世后,龙云又请他接任富滇银行总办。文章主要讲作者在云南省整理金融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主持整顿金融、成立富滇新银行等情况,但文章中关于云南在护国战争中“既无外援,亦未能举债 (外债内债都没有)”的说法,显然过于绝对。
且看温益群在 《毁家纾难,再造共和——论云南人民对护国战争的贡献》一文中的统计,“从护国军兴至凯旋而止,云南都督府筹集的款项有:一、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移其费作军用者,共十八万余元;二、筹饷局劝导各县各界捐济者综计三十五万一千余元;三、向海外华侨募捐,先后共得一十二万八千余元;四、截留盐款共计一百六十七万余元;五、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六、向铁路局、水利局、垦殖局等机关提借款额计八十一万三千四百二十元;七、挪用宝华公司、东川铜矿公司等处股本,截留中央解款,共六十一万六千元;八、向银行借用之款共二百三十三万元 (其中:发行中国银行纸币一百三十五万元,向富滇银行借款八十万元,向香港富记解还总行借款十八万元);九、向各县摊借之款共一百一十四万元。以上各项综计为九百零七万八千四百多元。”该文还注明统计资料来源为 《续云南通志长编·大事》。从这些所筹款项来看,诸如向铁路局、水利局、垦殖局等机关的 “提借款额”,向中国银行、富滇银行等的 “借用之款”等等,算不算 “举债”?实事上,就在缪先生的文章中,即是这样说的:“老富滇银行的崩溃,始于护国战争时向省府举债,省府无力偿还,银行便不能不作无准备的发行了。”

图2
或许缪先生想要说的举债乃是指政府明令发行的公债。因为曾在富滇银行任职的缪先生很清楚:云南财政厅曾有发行护国公债、靖国公债之计划,但先后印制的护国公债票及靖国公债票,均因故而未能发行,并被封存于富滇银行之库房,从而还免却了该行为发行这些债票带来的还本付息之劳作。

图3
不过,虽然云南护国公债票最终未能发行,但并不等于筹办云南护国公债的活动没有开展。就在温益群的文章中,即提到 “发行护国公债”之情况:“为征讨独夫,补充战费,省都督府还发行了护国公债,公债发行时,向民众讲明公债发行的目的,声明了给息还本的具体规定。云南人民皆懂得 ‘国之不存,于家何有’的道理,即使政府不发行公债,也会解囊输财,共襄义举,何况公债是以给息还本的方式向人民集资,所以大家都踊跃争先认购。”该文注明其资料来源为1916年3月29日的 《滇声报》。
鉴于正式的护国公债票直至1917年7月1日才印制,因此当年 《滇声报》所说认购的公债,只能和越南华侨刘登一样,拿到的是 “护国公债收款证”。因此,云南军政府发给刘登的 “应募护国公债西贡币银拾元”的收款证,乃是一件发行护国公债的具体实物证据,凭此即可否定护国战争中云南并未举债之说了。
刘登拿到由赵桃之经募的该本云南护国公债收款证已是第122号,而仅在越南受云南护国军政府委托的经募人还有不少。至于云南省内,就如 《滇声报》所说 “大家都踊跃争先认购”。因此当年已认购公债之款项不应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那么,为什么温先生文中 “从护国军兴到凯旋而止云南都督府所筹集的款项”中,居然没有筹募公债款这一项呢?这也是温先生未能答复的问题。而其原因乃是,后来,由于所印制的云南护国公债票因故未能发行,包括刘登先生应募的护国公债收款证在内,均未能改换成正式的护国公债票,而是成了变相的 “捐款收据”。从而,上述该收款证实物便与刘登先生其它捐款收据一起,有幸一直留存至今,成了这位爱国华侨积极支援国内革命活动具体的见证。如果温先生文中提到的云南都督府的筹款统计并无疏漏,或许,已收取的护国公债收款证之款项,已分别被统计为 “各县各界捐济”及 “海外华桥募捐”之中了吧?
温益群的文章认为:云南都督府 “以政府的名义,通过各种途径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力量,保证了护国战争的军需费用。虽然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加紧收税,克扣人民而来的,但是,在护国战争这个特定的时期,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是一致的。诸如裁减教育经费、发行护国公债这些决定,得到了当时云南各族人民的谅解。正是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同舟共济,才使政府的各种措施得以实施。所以说,人民是共和的真正再造者。”笔者赞同温先生的说法。当然,温先生如果知道了当年发行护国公债的后续变故,一定还会在文章中再添加一笔的。
五 结束语
2015年,是以云南为策源地的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一百周年。护国战争粉碎了 “洪宪”帝制复辟,把被袁世凯废掉的民主共和制度重新建立起来,捍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今天纪念它,不仅要记住那些再造共和的护国将士们永垂史册之丰功伟绩,同时还要记住在护国战争这场历史壮举中,以云南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包括刘登先生在内大批海外爱国华侨们为此作出的积极贡献!
注释:
①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第59页。
② 张海鹏:《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长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5页。
③ 赵椿主编:《唐继尧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④ 周寒僧:《记李烈钧先生》,载文明国编 《李烈钧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
⑤ 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1982年台北忠孝彩色印刷厂承印,第107-112页。
⑨ 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