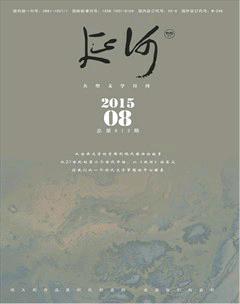月光曲

丁小村,本名丁德文。著有中短篇小说二百万字,作品曾转载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并有多篇被收入年度选本。另著有诗集《简单的诗》、长篇非虚构作品《大秦岭:清洁的家园》等。中国作协会员、汉中市作协常务副主席。现任职汉中市文联。
四个人约好在西关外柳林村口汇合,他们从那里步行五里路到城西下马渡口,那里有一条小渡船渡他们过河。过了河他们还得走五十里山路,才能到坐长途汽车的地方。坐上汽车就可以到西安;到了西安,会有人带他们去延安。
舒贞脑子里牢记了这个行程,这些熟悉的不熟悉的站点,对她来说都十分重要,离开——到达,告别——迎接,过去——未来……这样一组组的词汇在脑子里发出声响,就像沙漠中的旅人头脑中响起的驼铃声,声音清脆,节奏鲜明。
柳林村是离城最近的一座村庄,村庄外有一大片绿云般的柳树林,树林像是绣在一个漂亮的河湾上,野马河在柳树林那里划出一道弧形,形成了个漂亮的河湾——这个河湾像一汪明亮的眼眸,那片柳树林就像一道浓密的秀眉。春天里舒贞还和同学一块去踏青,对于这伙年轻女孩来说,这柳树林、这河湾,都像是春天写下的诗,充满了生机和希望,也洋溢着青春的热情。
下马渡是野马河边的一个有名的渡口,也是她们常去的地方,教美术的老师带她们去写生。美术老师学习过西画,有些新式教育思想,春秋季节,喜欢带她们去乡野,在下马渡口观察放牛的老人、往来过渡的人、撑船的艄公,为那些在菜地里摘豆角的村妇画素描画。
至于更远的长途汽车,就只能在舒贞的想象中了……更远更新奇的想象是西安,是延安。有几个年轻教师私下里跟她们说起延安,经常是眉飞色舞,带着几丝神秘,让她们心中充满憧憬,就像童话中的小女孩憧憬那些长满奇花异草的原野。
舒贞是比较勤快守时的,早晨五点钟她准时起床,收拾好东西,打了个小包裹,就悄悄出了门。包裹里有一套简单的换洗衣服,两套小内衣——其中一个小肚兜里边裹着二十几个银元,是悄悄从母亲的小箱子里偷出来的。带着这个小包裹,她溜出门,到不远处会馆巷的街口等着杨莲。三个女孩中她和杨莲住得最近,就相约一起赶往柳林村那里。她站在街角的糕点铺的屋檐下,等杨莲过来。糕点铺的铺板门面紧紧关着,门缝中漏出几丝光,里边有响声,大概买糕点的早早在忙碌着了。
躲在人屋檐下,舒贞大气也不敢出,就这样等了杨莲好久。杨莲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冲动型的,几个女孩中她对去延安的态度最坚决。正是她的热情感染着舒贞和另外一个叫肖立筠的女孩子,三个人下定了决心跟着那个叫秦艮的年轻教师,一起去投奔延安,去到那明亮的天空下,迎接新的生活。
杨莲几乎啥也没拿,直接把一个小包袱裹在腰上,她告诉舒贞,自己就带了一件衬衣和一双袜子。她把包袱这么缠在腰间,像个走江湖的人。舒贞在昏暗的光线中,看着杨莲的样子,感觉好玩,扑哧一声笑出来。
“笑啥哩,咱赶紧走,去迟了他们会着急的。”杨莲推了一把舒贞,舒贞没注意,身子碰在糕点铺的门上,里边有人喊了一声:哪个?
她俩赶紧跑开了,一边跑一边还在笑。到了西门口,俩人跑得有些急,站在那里大喘气。这个时候,舒贞才突然想起,忘了带一件东西。她赶忙对杨莲说:“你先往柳林村那儿走吧,我要回去取个东西。”
“回家去取吗?”杨莲问,“啥东西啊,不重要就算了。”
“我要回去取,一定要,你先去吧,我跑回去,赶得上你们的。”舒贞没等杨莲反应过来,就沿着黑乎乎的城墙边,往城北跑。听得杨莲在身后边喊叫:“舒贞,你慢点啊,我陪你一起去取东西啊……”
舒贞跑得很快,杨莲大概也没赶上来,转眼间就没有了杨莲的声音。城墙根下一簇簇的草,还有些杂树,都影影绰绰地从舒贞眼前划过去。
她必须回去取那样东西,手里提着小包袱跑起来很不方便,她干脆把小包袱挂在肩上,大步往城北跑。她要取的东西不在家里,在学校,在宿舍里的床铺下压着:只是一个小本子。
学校在城北,名叫烟寺。自然了,烟寺是一座寺庙。
在十年前,抗战开始时,从西安迁来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临时占用了这座寺庙做了校园,从此这座寺庙里边少了钟磬之声,多了琅琅书声。女师在这里只办了一年半,就迁到别处去了,本地就有人商议,还在这里办一所师范学校,有些女师的教师和毕业的学生自愿留在这里当了教师。舒贞就是在前一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在这样一个小县里,女孩子上学,还是比较少的。
舒贞偷偷摸回宿舍,正是放假期间,学校里空无一人,两排高大浓密的柏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默然矗立。走过青石板路、青石小桥,舒贞放轻脚步,围墙边的草丛里虫儿唧唧鸣叫,一些早醒的鸟儿在大柏树枝丫间活动,发出扑啦啦的声音。
宿舍是过去为僧人修建的住所,几个人一小间。舒贞悄悄扒拉开窗子,跳进宿舍,摸到自己的床边,从棕垫子下边摸出那个本子,塞进包袱里,这才喘出了一口大气。这时候她看到月光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洒在铺地的大砖上,亮花花的,仿佛能看清楚砖上雕刻的花纹。
宿舍外边的空场上,有一棵老迈粗大的柏树,舒贞她们三四个女孩子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住这棵大柏树的树干。柏树下边是一个小亭子,里边有一口大钟。自打进到这个学校,舒贞也没听过这口钟被敲响过。本地人都知道“烟寺晨钟”,是本县有名的“八景”中的一景。
舒贞踏着月光走到大柏树下,那口钟在亭子里寂寂无声,仿佛时间没到黎明,还停留在午夜。连晨钟也这么安静,这让舒贞在一瞬间忘记了时间。
有只鸟突然在柏树黑乎乎的枝叶间叫了一声,这叫声在异常安静的清晨,十分响亮,甚至有些刺耳,让舒贞从片刻的愣怔间回过神来。她好像突然想起了要去柳林村追赶杨莲他们的事儿。她拔腿就跑,往学校外边跑。
快到校门口,她脚下绊住一个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包袱里边也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她顾不得屁股摔疼,赶忙把包袱里掉出的东西捡起来,原来是那个沉甸甸的小肚兜,里边裹着几十个银元。她把东西塞进包袱,这才发现,自己撞在一只水桶上。水桶倒在一边,水流了一地,反射着丝丝的月光。
水桶放在青石桥边,一个人从桥边过来,他看到还没从地上爬起来的舒贞,赶忙过来扶。
舒贞坐在地上,这才感觉小腿被那只水桶碰疼了。
那人扶起舒贞,瞅着舒贞狼狈的样子,半天才认出来:“这么早到学校来了啊,是李舒贞呀,摔着没啊?”
舒贞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把包袱往背后藏。她想着打个招呼,赶紧出学校,去赶杨莲他们。可是不争气的脚,这时候突然发出一阵钻心的疼。不是小腿,是脚踝。
“没摔着,没摔着,您这么早打水啊,高师傅?”舒贞疼得悄悄咬着牙吸着气,和他打着招呼,一边开步,准备继续出校门,“我来宿舍取个本子呢。”
那人把倒在地上的桶提起来,放在青石桥边。他盯着舒贞,像是在观察一个才在学步的小女孩:果然,舒贞一瘸一拐走了没几步,脚上的疼使她止住了步,她试着单腿站立,把那只受伤的脚提起来,抖了抖,疼痛并没有减轻,反而让她悄悄地咬了咬牙。
那人过来扶舒贞:“脚伤了吧,慢点啊,慢点。”说着他扶着舒贞走回来几步,他们坐在青石小桥的桥墩上。
“先不动啊,先不动。”那人让舒贞坐在桥墩上,“很疼吧,歇会儿看看,还疼不疼——你不着急回去吧?”
舒贞心里急得很,她耳边仿佛有一根钟表的秒针在跳:咯嗒,咯嗒,咯嗒……越来越急,这让她脚踝的疼痛仿佛更加重了些,如果不是当着一个男人的面,她都快叫出声了。
有一条水渠从烟寺横穿过去,这条水渠四季不断流,干脆有人就在水里养了些荷花、睡莲、荸荠之类的水生植物。现在俩人都没说话,那人站在桥边,陪着舒贞歇着,看桥下的水渠。
舒贞稍微缓了缓,感觉脚踝的痛感减轻了些,想要和那人说两句话,好赶紧出学校去赶杨莲他们。但那人好像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只是看着桥下的水渠。舒贞不由自主地也随着他去看水渠。
她看到了一轮清明的月亮在水里,这轮明月不像是漂浮在水里的,而像是一只被水包裹着的晶莹的玉盘。四周有些小小的睡莲,像是雕刻的花纹。这时候似乎水底有鱼儿游动,把这幅宁静的画面搅碎了,月光像是融化在水中,变成了丝丝缕缕,幻化成了一团团泛光的晕。
俩人仿佛都被这水中的月光迷住了,谁也没说话,连呼吸也听不到。舒贞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地看过水中的月亮,旁边这个男人,也像是沉入了这谜一般的水中光影。
不知过了多久,那边的柏树上边一阵扑腾,一些早起的鸟儿开始活动起来,舒贞这才像是从梦中惊醒,她下意识地看看天,天上已经有些许亮色,一些发光的云彩掩住了月亮的眩光,天上的月亮仿佛慢慢在融入黎明中。
“高师傅,”舒贞叫了一声,“我回去了。”
她起身的时候,才发现,脚踝上的疼痛并没有消失,一旦她起步,那疼痛仿佛也被唤醒。
那人转过身来看舒贞,他搀着舒贞站起来,往前走一步,舒贞站立不稳,几乎倒在他身上。
“不行,肯定是脚颈瘀伤了。”他一手搀着舒贞,一手提着桶,把舒贞扶到不远处他的房子里。让舒贞坐在椅子上,他倒来热水,让舒贞脱了袜子,把脚放进盆里。舒贞有些不好意思,那人站在窗前,背过身去。舒贞这才脱下袜子,把光脚放进热水里。温热的水一浸,脚踝一阵疼,但是接着,舒贞感觉到舒服,受伤的脚被温暖柔软的水包裹着,疼痛的节奏仿佛缓慢了些。
“你先用热水泡泡脚,好好揉揉,我再去打水。”想着刚刚被自己莽撞地碰翻的水桶,舒贞悄悄笑了。那人提着那只水桶,出了门。舒贞这才把自己那只娇气的脚提出水看:脚踝瘀伤了,肿了一个包。
杨莲他们是没法去追赶了。舒贞坐在这间小屋子里,对着自己肿了一个包的脚,一阵失落感涌上心头,让她忍不住想要流泪。
这会儿他们可能已经走在山路上了,一边看着清晨的山色,一边朝着火车站飞奔。后天这个时候,他们兴许已经到了西安,再过上五六天,他们大概就到了延安。“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舒贞心里响起了那些悄悄听来的歌声。没有了同路人,舒贞是不能想象到延安去的,也许这辈子自己再也到不了延安了。舒贞的心里飞出一只鸟,飞过柳林村,飞到下马渡,飞过野马河,飞过茫茫山峦,飞上了汽车火车……但是,哐当一声,鸟儿跌了下来,落到地上,疼痛地扭动着受伤的翅膀……
为了打发胸膛里锥心的失落和惆怅,舒贞一边在温水里揉着自己受伤的脚踝,一边看这间屋子。屋子里边很简单,就一张床,床上铺着干净的床单,整齐地放着被枕。小小的木格窗,窗边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有茶杯,有笔砚。像个读书人的书房,又像小旅馆的客房。桌边放着一个竹编小书厨,书架上放着一些书,舒贞不能站起来去翻看那些书,只能心里猜想,那可能是些什么书。
一块木板棋盘放在舒贞身边,舒贞无聊地数着棋盘上的格子。棋盘很大,像一张小饭桌。棋格棋路画得清晰,楚河汉界写得分明。舒贞小时候跟父亲下过几天棋,象棋围棋都会几手,看到棋盘就想这位高师傅大概十分喜欢下棋。
棋子装在一只木箱子里,就放在棋盘下边。舒贞好奇,就打开了这只小木箱,棋子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真漂亮,舒贞不由自主伸手拿起一个棋子来看,是个“相”。棋子打磨得光滑圆润,抓在手里,仿佛触及温润的木头。
那位高师傅提着满满一桶水进门的时候,舒贞正在观赏这只棋子。棋子是什么树木做的,舒贞不知道,但好像能嗅到一丝丝的木香,是那种新鲜的木头气息。上边的字儿是用魏碑书写的,刻成了阴文,虽然没有涂抹颜料,但能看清。
舒贞好奇,没有涂颜色的棋子,如何分红方黑方呢?
他放下水桶,问舒贞:“你脚好些了吗?”
舒贞觉得未经主人许可翻人家的东西,很不礼貌,有些不好意思,要把棋子往箱子里放。
“会吗?”他注意到舒贞在赏玩木头棋子。
舒贞点头:“会点儿。”
“脚还疼吗?”他一边问舒贞,一边给舒贞拿来一条干净的白洋布帕子,让舒贞擦脚。舒贞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把光脚拿出盆子。他好像明白舒贞的心意,把白洋布帕子递给舒贞,就走出门,给小灶上的锅里加水。
舒贞飞快地擦干净脚,穿好鞋袜,然后站起来,端起木盆,要去倒洗脚水。脚踝上的疼痛经过热水浸泡,减弱了许多,他刚好走进来,接过舒贞手里的盆子:“你坐着,你坐着哈,我去倒。”
舒贞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把板凳放好,把那只擦脚的布帕子搭上门后的绳子,门后有个拖把,她赶忙拿过来拖干净地上的水渍。地面是大方砖铺的,跟舒贞宿舍里一样,看来这也是从前僧人的住房。
那人倒了水把盆子放在门外,这才进来:“你坐啊,我给你泡茶。”从竹编书橱的底层拿出一只茶叶罐,又拿出一只青瓷小盖碗。他给舒贞泡茶,舒贞半倚着墙站着,想去看他书橱里边的书。
“你随便看。”他在小方桌上放好茶碗,放在舒贞这边,也给自己泡了一碗,然后自己坐在靠门的椅子上。
他这么说,舒贞反倒不好意思看了。于是坐下来,端起了茶碗。茶碗有小孩拳头大,秀气好看,青花瓷面,端在手上,带给舒贞一种稳重滑润的手感。他端起自己那碗,放在嘴边,嗅了嗅,喝了一口,然后抬头招呼舒贞:“请喝茶。”
舒贞也轻轻嗅了一下,喝了一小口——茶很好,虽然已是秋天,却带给人一种春天的草木清香。
喝第二口茶的时候,舒贞心里一直压着的那个感觉冒了出来:对这个男人的一种神秘感。
依舒贞对他的了解,仅仅限于他是学校的一个校工,也就是做些杂役,打理打理花草,修一修课桌椅,有时候帮着采买东西。总之,像所有的杂工一样,哪儿有需要他就在哪儿。他姓高,舒贞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都把他叫高师傅。
他们这么慢慢地喝着茶,也没多说话,好像把时间留给了这些茶水和茶叶,让它们在一起互相融化,然后散发出缕缕清香。
带着一丝丝好奇和猜测,享受着漂亮的茶碗和新鲜的茶香,舒贞忘却了脚踝的疼痛,也把时间给忘了。舒贞心里有些紧张,但他并没有追问舒贞挎着小包袱到底来学校取什么东西,还是准备干啥。
快到中午的时候,舒贞从这个房子里走出来,依然挎着小包袱,脚踝有点儿疼,但勉强可以开步走路。高师傅要送她回去,被她拒绝了,他站在烟寺的大门口,看着舒贞走过校门口的那座石桥,穿过那片长满杂草和小树的田地,往城里走。
家里有些乱。舒贞的父亲正坐在天井边的摇椅上发火,虽然发火,他还是没舍得扔掉他那个接骨木打磨的拐杖,只是把拐杖头在青砖地面上戳得哒哒响。舒贞的妈妈和一个奶妈去街上找舒贞,另外两个常年在家里干活儿的长工,也被派到几家亲戚家去找舒贞。事情是妈妈发现的,妈妈发现舒贞的两套衣服,还有内衣都不见了;同时也发现小箱子里少了的银元。舒贞不是那种很野的女孩,会去哪儿,难道跟人私奔了?这种事,妈妈想也不敢想的。
没想到舒贞自己回来了。父亲把拐杖扬在半空,没戳下去,外边去找舒贞的人都还没回来。
舒贞隐瞒了出走的事儿。只是说去学校取东西,准备和几个同学去乡下一个镇子赶集。舒贞算是个乖女孩,对于这个漏洞百出的谎言,父母都似乎相信了。小县城里的年轻人心野,想往外边跑,但那是男孩子的事儿,女孩子不兴这么干的。他们绝对不能想象舒贞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往延安去。
家里有两个儿子,舒贞的两个哥哥,早跑出去了。很让老父亲不可理喻的是,两个儿子,一个跑到了黄埔军校,成了国军军官;一个则跟人跑到了延安,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舒贞对两个哥哥都很敬佩。她之所以答应和杨莲他们一起去延安,也多半跟那个传说到了延安的二哥有点关系。
但是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了,舒贞坐在自己的房子里,抚着隐隐作痛的脚踝,不由的流下了眼泪:失落,失望,夹杂着浓厚的伤感,一起涌上心头。她真想放声大哭,但怕惊动了父母。
舒贞的父亲算是城里有名的绅士,他们家被称为李家大院,在城里也算数得上的家门。两个哥哥的事儿,在城里尽人皆知,毕竟有一个当国军军官的大哥撑着门面,谁也不能小瞧的。舒贞不想在这么个小县城里待下去,多半跟那两个野天野地的哥哥有关系……但是她现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
到了秋天,舒贞坐在烟寺的教室里,学校里都传说有个年轻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出走了,据说是到延安去了。有人追查这件事,舒贞装作一无所知。这年她十七岁,再过一年,她就毕业了,她毕业后还会在这所学校当老师吗?那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舒贞抚摸着毛边纸印刷的课本,望着窗外那棵开得正热闹的紫薇树,不由神思漫漶,一时间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功课了。
好多年以后,我听说舒贞的故事,很好奇那个小本子,想着当时舒贞为了回去取一个小本子,耽误了去延安的事儿。就不由想追问:那是个怎样的小本子呢,竟然改变了舒贞的命运?
这时候舒贞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太太了,她笑了笑,然后告诉我一件事,顿时让我目瞪口呆。她说,那其实是她收集抄写的一本花谱,她给这个小本子起了个名字,叫《群芳谱》。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接她的话,我看到她脸上的笑容,那是一位老太太的笑容,就好像回到了童年:流露出一丝天真,一丝稚拙,有人说老小老小,这个时候我真是觉得老人就像孩子。
两个老人经常互相搀扶着,在城南的野马河河堤上散步,他们跟人打着招呼,但多半的人都不记得认识他们。别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像是他们生活在传说中,突然降临身边,反倒让人觉得有些漠然。事实上,他们的确是这小城里一度的传奇人物。多年以后,随着城市的拆迁新建,街道的变化,那些老院子老街道都不复存在,这样的老人,也好像被人们忽略了。不再有人去打听他们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住在烟寺,那时候烟寺已经被改造为一家工厂。学校在多年前早已搬迁,搬迁之后,烟寺被改建为一座罐头厂,我的朋友刚好在那座工厂工作。烟寺里边的那些石碑和菩萨被搬走,那口古老的大钟被搬进了博物馆存放起来,再没有被敲响过。
烟寺里住着一家人,男的在工厂当工人,女的则担任工厂的看门人兼收发。我的朋友告诉我,这家人有点儿来历。有什么来历,朋友告诉我:那家男的姓高,他的父亲,曾经是本县最早的留日学生;他的母亲,姓李,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女儿,上过师范学校。
这家男主人的母亲,就是舒贞。父亲呢,当然就是那位校工高师傅了。
因为朋友的介绍,我对这对老人充满了好奇。
在舒贞老奶奶七十一岁的时候,我见到了两位老人。当时他们正在城南老街的一座小房子的楼顶晒太阳。城南老街二层的小房子,两位老人住在楼上,两间小屋子,一间做了厨房,一间当了卧室。房子很低矮,我走上楼,看到门前的楼顶平台上,放了许多花草,那是个夏天的清晨,花草刚被浇过,闪着湿漉漉的光泽。两位老人坐在花草边,两个藤椅,他们面前放着个小茶桌,还是两套青瓷小盖碗。他们见我上来,招呼我坐在第三只椅子上——不是藤椅,是一只塑料凳。
跟我讲讲你们的事儿吧,老奶奶。介绍我去见他们的人,刚好和他们有点儿亲戚关系,无论年龄还是辈分,我都该叫他们一声爷爷奶奶——因为这个关系,我对他们说话,就显得亲近些,近乎撒娇。
老奶奶健谈,老爷爷则不置可否,听我们说。
舒贞老奶奶讲了些片段,我只能想象那些过去的故事。实际上,她讲的可能比我写下的少得多。他们并不喜欢讲自己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几十年,他们经历了无数的时代风雨,对于世事,他们甚至有些漠然。所以要求两位老人讲自己的过去,多少有些让他们觉得违心。我心有同感,所以并不想追问。我设想当我七八十岁的时候,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我留恋清晨的阳光,傍晚的霞色,但我并不想回想过去的人生,或者说,我不会对着人去讲那些。一如当年,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藤椅上喝茶,并不理会楼下喧嚷的街市。
开学不几天,舒贞在烟寺校门里边的青石校路上遇到了高师傅,他提着那只被舒贞踢过的木桶,装着满满的一桶水。在青石小桥那里,他放下桶,走到桥边,去看水渠。舒贞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也想道一声谢,为了那天清晨他对她的照护,还有他的茶。
舒贞走到他身边,也去看渠水,她在水中看到了小小的睡莲,翠绿的叶片漂浮在水上,像是在温柔的梦乡;一朵朵小小的嫣红花朵,探出叶间,正像是梦中的星星在闪烁。舒贞看着这些小花小叶,出了神,最后却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男人身边,被双双映在水中。
他转过头来:“你啊,好了吗,你的脚?”
舒贞有些羞涩:“嗯,好了,没啥了——谢谢你,那天……”
“后悔吗?”他看着舒贞的脸,问。
“什么?”舒贞一时没回过神来。
“没和杨莲他们一起走。”他又垂下头去看水里的睡莲。
舒贞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人什么都知道。
舒贞不好直接回他的话。就也沉默下来,又跟他一起去看水中的那些美丽的小花小叶。
过后舒贞打听这个男人的事儿,才隐约知道那么一些。原来他竟然是城西柳林村的人,柳林村有个大户人家,高家。高家有三个儿子,都被官费送到日本留学。两个大儿子在北平南京,做了官,做了教授。只有最小的这个儿子,不知为什么没上完学就回了老家。
他出了家,在烟寺。
烟寺是本县有名的寺庙。他出家那年,刚好三十岁。后来烟寺被西安搬来的女子师范学校占据了,他就脱了僧衣,当了学校的校工。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是本县大户人家子弟,而且到日本留过学。
舒贞花了一年多时间去打问这些事,等她弄清楚这个人的事情之后,她跟他已经熟的像家里一样了。
她喜欢去他那里喝茶,还和他下棋。对于品茶,舒贞倒是不陌生,家里有个绅士爸爸,当然懂得品茶。他偶尔几次跟舒贞讲起日本的茶道,说这些都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他的小房子,在舒贞看来,是让她觉得安静又舒心的地方。她喜欢那个给她泡茶的青瓷小盖碗,甚至超过喜欢茶本身。她对于手中触摸着暖暖的瓷器的感觉很特别,那是一种温润的触感,一点儿都不亚于触摸一块玉。经常的情景是,舒贞和他,各占一只椅子,坐在那只小方桌两边,各自对着一只青瓷小盖碗,也不多说话,仿佛怕多话冲淡扰乱了茶的清香。
和他下棋舒贞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一旦面对棋盘,舒贞就显得和他一样的心平气和,并没有在棋盘上杀伐征战的感觉。有时候,舒贞甚至跑了题,顾着欣赏这棋子,触摸着这圆润的檀木,嗅着棋子上散发的木香,忘了下棋本身。
这时候舒贞才发现这幅棋子的奥妙。原来,黑方使用的棋子是青檀,木纹自带黑色;红方使用的是紫檀,木纹自带红色。虽然不是那么鲜明,在棋盘上却自然能够分清。舒贞就好奇地向他打问:“这副象棋是从哪儿来的?”
他告诉舒贞,是一位高僧送的。后来舒贞会猜测,是不是因为这么一位高僧,他才会想着回到烟寺来出家?
舒贞是不喜欢多事的人,她没问他很多问题,就像下棋,两人甚至忘记了输赢。经常下着下着,他把棋盘上的残局变成了一个迷局,然后告诉她:这是一个古谱上的残局,叫什么什么。舒贞觉得自己很傻,不知不觉地就随着他转换了主题,研究一个残局当然有趣,这时候没了输赢,仿佛信马由缰,跑到了野天野地,忘记了归路。
舒贞家的灾难是在一个早晨降临的,当时舒贞毕业待在家里,正在考虑是不是到小学去当个老师。这一年是多事之秋,不断地有军队过往,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战事。然后就这么平平静静地在某一天突然就改天换地了,舒贞熟悉的小城,一下子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明亮的天。但现实对于舒贞是不明亮的,因为家里有个国军军官,又因为二哥不知所在,家里有着商铺田产,父亲自然被当成了地主豪绅,在一个早晨被抓走,第二天,死在外边。家里的长工和佣人跑光,一伙人涌进院子来把她和母亲撵了出去。这是最冷的一个冬天,舒贞看着母亲在一个临时借用的小房子里,躺在凑合的床铺上,奄奄一息。最后没到过年,妈妈闭了眼,临走时,要舒贞去找二哥。他们家唯一的希望是二哥,但是那个传说中跑去了延安的二哥,却根本不知道如今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乱糟糟的这个冬天,外边锣鼓喧天,吵吵嚷嚷,舒贞连大声哭也不敢。面对着死去的妈妈,舒贞淌着泪,却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候她想到了他。
她一路跌跌撞撞跑到烟寺,到处找那个男人。这时候,有个男人就像是有了力量,舒贞已经没有了任何力量可以依靠,让她能够撑着站在寒冷的风中。
她在他的小房子门口等了几个小时,才看到他匆匆回来。舒贞毕业后,这所学校也解散了,有人提议把烟寺恢复成寺庙,但是在人心惶惶的战乱年代,哪有什么僧人仍然来这座寺庙修行呢。
他又把脑袋剃光,穿上了一套青布衫,勉强像个和尚的样子。
她从来没看过他当和尚的样子,这会儿看着他光着脑袋从外边回来,不由得有些诧异。
他看她一脸泪水的样子,吓了一跳:“是舒贞啊,出什么事了啊?”
她把他领回家,看着躺在床上的妈妈。
他跑出去找到邻居,烧了一锅水,然后关上门,让舒贞给妈妈洗身子。等舒贞给妈妈洗干净,穿上衣服,他已经叫了好几个邻居来。他们忙了一天,把母亲安葬在城北的山坡上。到了晚上,她不敢回到那间临时借用的小房子,就跟着他到了烟寺,回到他那间小房子里。
他给她烧了水,让她洗脸泡脚。然后他泡了茶,他们坐在小方桌边喝茶,茶是热的,到这个时候,舒贞基本上闻不到茶香了,她只觉得暖和。小方桌上倒扣着一只小碗,半截洋蜡点着,发出一星明亮温暖的光,照着桌上的青瓷小盖碗,茶正冒着丝丝热气。
喝了半会儿茶,舒贞缓过神来。这一天太累了,舒贞都忘记了伤心,她默默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茶碗冒着热气。热气一丝丝地弥漫着,把蜡烛光变得朦胧起来。
最后,他起身从床上抱起一床被子,跟舒贞说:“你关好门,好好睡一觉,我去找地方睡。”
舒贞愣里愣怔地站起来,跟着他往门边走:“那……你去哪儿找地方呢?”
“这么大个地方,肯定有地方啦,你不用担心的哦……”他一边说,一边要出门。
这时候,舒贞突然站不稳了,就像人就一下子垮了下来,她倒在他身上。
被他抱在怀里,舒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只是觉得自己很累,身体很软,想要睡着。到了半夜,窗外寂寂无声,舒贞醒来,发现自己睡着在他怀里,他端坐在椅子上,给她身上搭上了那床准备抱出去用的被子。
小房子里寂静而黑暗,蜡烛早已熄灭。舒贞感觉到自己在一个男人怀里,很安宁,很暖和。她动了动,听到他说:“你太累了,去床上睡吧……”
舒贞突然抱紧他,好像怕他跑掉。
这一年,舒贞十八岁,他四十二岁。他们成了夫妻,结婚证是过了两年才办的,按照新时代的新政策,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照片上,她的腹部已经挺起,怀着他们的大儿子。
几年以后,舒贞在小学里当教师,他依然在烟寺,不过烟寺改成了工厂,他在工厂里打杂。他们依然住在烟寺。上边有人给她送来哥哥的相片,还有一块铭刻着“烈士家属”的小金属匾——二哥在朝鲜战场上变成了烈士。因为这块匾,他们获得了一直住在烟寺的权利。她在小房子前边用捡来的断砖烂瓦砌起了几个花坛,种上了一些花草,有大丽花、月季,还有四季海棠,虽然都是些普通的闲花野草,却也四季开花,长得旺盛鲜活。当然,她还专门种了一畦蔬菜,有黄瓜、西红柿、辣椒和丝瓜。他找来细竹子、麻绳和铁丝,编成了小篱笆,到了夏天的清晨,小黄瓜和小丝瓜,都把细嫩的枝条伸展在篱笆上,丝瓜开出金黄的花朵,引来了一些蜜蜂,它们钉在花蕊上,舍不得离开。
又过了三十多年,有人从台湾来,找到他们,说是她大哥的后人。大哥到了台湾,好几年前已经去世,养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在台湾,两个女儿去海外结婚成家了。大哥的儿子找到老家来,寻找到姑姑,也替父亲打听家人的情况。他们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迎接大哥的儿子,他和她忙碌了大半天,做了一桌家宴,来招呼远来的亲人。烟寺的房子大部分已经拆除,只有他们住的这两间还保留着,不过外边已经经过修缮,打上了水泥。这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在烟寺这个罐头厂当了十几年工人了,二儿子去铁路当了工人,女儿在本城结了婚。一大家人聚集在烟寺,房子太小,他们只好把家宴摆在门外边。
大哥的儿子很大方,给每个人都送了礼物,来表达父亲几十年没回家的歉意。过后小城里都传说,这家台湾亲戚给他们送了金戒指、金耳环,还有美元。只有舒贞知道,他们悄悄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换成了现金,捐给了即将开工的学校。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出过家当过和尚,一向对这些金的银的纸的都没什么热情,她顺从了他。
对于用什么来回礼,他们商量了半天。本来舒贞家是出名的大户,家里有很多东西,但是当年全都被没收,事后几乎没什么存留。那幢大房子,被分给很多户人家住。舒贞感到很羞愧,因为没有一件家里的东西可以送给大哥的后人。后来,还是他出的主意,把那副檀木象棋送给大哥的儿子,留作纪念。
舒贞第一次反对他。她实在舍不得这幅象棋。并不是它有多么值钱,而因为它保留了太多她的记忆。再说,这也是他最心爱的东西。
舒贞说什么也不同意把这幅象棋送给大哥的儿子。后来,舒贞总算想起了一件东西,是一只玉镯,那还是很小的时候,妈妈给舒贞的。舒贞觉得这件祖母的东西传给大哥的后代,算是对家族有了个交代。对于母亲给女儿的东西,他也不同意舒贞送给侄儿。两人争持不下,最后还是舒贞说服了他,理由很简单:这镯子很小,好带啊;你把那么一副大象棋送给他,他不方便带回去呢。
他笑了。舒贞也笑。
有人知道他曾经是本县最早留学日本的人之一,也有人打听出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老头子八十多岁的时候,他们来请他当政协委员。他谢绝了,说年龄大了,什么事都记不清了,又不能写,又不善说,还是不给你们添麻烦了。他们还是坚持让他当了个政协委员,算是挂名的。
舒贞蛮喜欢老头儿这一点。她好像和他过着安安静静的日子,过惯了,也不喜欢热闹,除了自己的孙子孙女,他们也很少招呼客人。他们喜欢坐在一起喝茶,或者搀扶着去散步,有时候他看她侍弄那些花花草草,不加评价。他比她老得多,有时候他甚至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2002年,本县才女,二十三岁的高雯雯,赴日本公费留学,在外籍大学生演讲赛获得第一名,上了《读卖新闻》,成为本县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高雯雯,就是舒贞的大孙女。
2007年,本县著名的百岁老人高老先生去世,多年来,他一直在县办食品加工厂当门卫兼收发;高老先生的老伴名叫李舒贞,当过多年小学教师。退休后,老夫妻俩住在城南老街的一个小院里。鲜为人知的是,高老先生曾经是本县20世纪二十年代留日学生之一。高老先生去世不到半年,舒贞老太太也随之病逝,他们好像命中相伴,生死不离。
我有幸和这两位老人聊过一次,虽然他们都不多话,我还是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安宁和温润。我从舒贞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回味他们的故事。有一次,我特意跑到烟寺,去寻找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但是很遗憾的是,烟寺那里什么也没有了。那些古老的大柏树,早已经被连根铲除,那条水渠也被水泥板遮盖住了,那座青石小桥连一点痕迹都不存在了。
我想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去看看那条水渠,看看像淡墨一样点画在水上的睡莲叶子。或许我会在水中看到一轮明亮清润的月亮,或者看到我自己的眼睛?
我记得舒贞老人曾经告诉我:就在那个清晨,天快亮的时候,她和他一起看水渠,看到那么安静的月光,那么清明的渠水,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一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让她忘却了脚踝的疼痛,也忘记了去追赶同伴——他们原本相约要一起去延安。
多年以后,有人从北京来探望舒贞,是当年跑到延安去的女同学肖立筠。到延安后,她和一位军人结了婚,退休前她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她们说起了当年一起相约的四个人——她们崇拜的年轻老师,秦艮,1970年,饿死在劳改农场。她们说起当年,不由感慨万分,那位老师曾经是她们这帮青春少女都暗恋过的人。然后肖立筠跟舒贞讲起了杨莲,舒贞想起那位大大咧咧的女同学,就像现在站在她眼前——当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本子,舒贞会和杨莲一路飞奔到柳林村,一起飞过野马河,飞上火车,飞到延安去。肖立筠告诉舒贞,杨莲在30年前已经不在人世,她当了一所学校的校长,在一天早晨被自己的学生揪出来批斗,当天晚上她上了吊。舒贞听着听着,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她天真地想,要是当年杨莲陪着自己回到学校取东西,要是杨莲也和他们一起站在青石小桥边看水渠,要是她也看到水中的那轮月亮,看到融化在水中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