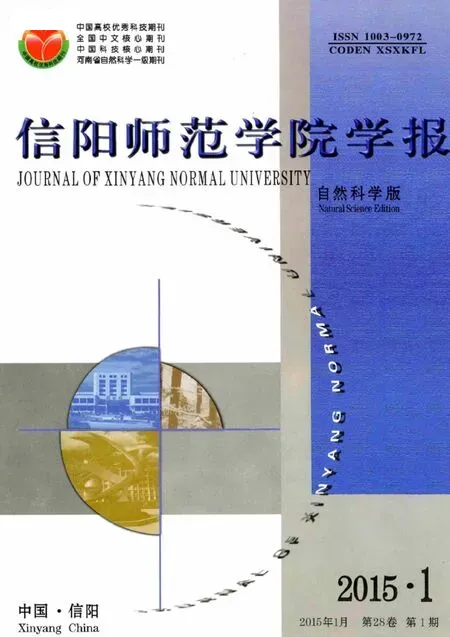大河三角洲营养盐研究进展与启示
——以阿斯旺建坝前后的尼罗河为例
顾家伟
(河南教育学院 地理系,河南 郑州 450046)
0 引言
世界大河是陆源物质与能量输移至海洋系统的重要传送带[1].据估计全球河流每年由此进入海洋的陆源物质约200亿吨[2].其中,N/P/Si营养盐、陆源无机碎屑和有机质等成为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物质基础[3].然而,这种自然的“陆-海”物质传送带很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特别是大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干扰[4].其中,流域建坝导致的入海输沙量和营养物质的相应减少,已经对下游河口地区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产生显著负面影响[5].
尼罗河流域以独特的干旱气候背景和阿斯旺大坝(建于1964年)闻名于世,紧邻地中海的三角洲地区,哺育了主要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的埃及人民(>8 000万).20世纪中叶建坝后,埃及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激增,三角洲生态环境随之恶化,特别是N、P等营养盐肆意排放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响应.近20年来,相关研究积累了众多文献资料,范围涉及三角洲多个泻湖水体和临近海域[6].基于此,本文详细梳理了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三角洲泻湖和近海营养盐研究成果,并对我国三峡建坝与长江河口生态环境响应研究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
1 尼罗河三角洲自然与社会条件
尼罗河发源于降水丰裕(1 000~2 000 mm·a-1)的赤道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蜿蜒于干旱的沙漠,最终由Rosetta 和 Damietta两条支流注入地中海.埃及是尼罗河最后流经地区,其稀少的降水(50~100 mm·a-1)使埃及极度依赖尼罗河河水,每年从阿斯旺大坝下泄55×109m3淡水,大多通过纵横交错的水渠被引入三角洲农田和沿海泻湖[6],最终注入地中海寥寥无几[7].1960年之前尼罗河入海泥沙约1.6亿吨,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几乎被截留(~98%)[7],其后沿海地区遭受海洋侵蚀,埃及政府实施了多个护岸工程[8].埃及农业主要集中在三角洲平原上,这里水渠纵横交错,组成严密灌溉网络,同时大量农业废水也通过水渠排入Manzala、Burullus、Edku和Mariut 4大泻湖[9].这些泻湖自东向西分布于沿海地区,水深较浅(~1 m),是埃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其鱼产量占到埃及的一半[6].1964年阿斯旺大坝修建后,进入下游地区泥沙骤减[7],强烈改变了三角洲沉积环境.笔者前期利用同位素测量获得泻湖沉积速率从建坝前的0.5 cm·a-1降至建坝后0.27 cm·a-1[10],进一步印证了三角洲地区泥沙输入减少,海岸保护工程实施后,泻湖地区逐渐演变为稳定而缓慢的沉积环境.
2 尼罗河三角洲营养盐研究
2.1 尼罗河与泻湖营养盐
19世纪的尼罗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洪水,伴随巨量泥沙而下的N、P等营养盐成为三角洲一年一度的天然肥源,埃及人也基于这种“恩泽”繁衍生息[6].然而,1964年阿斯旺大坝建成后,这种景象不复存在,大量泥沙蓄积上游水库(图1A),每年沉积于三角洲泥沙由2 400万吨锐减到210万吨[7],导致吸附于泥沙上的营养盐无法到达下游地区[11],三角洲土壤开始贫瘠化,这促使了化学肥料等的大规模使用.建坝后的近40年来,埃及化肥施用量激增,其中磷肥在1964—1970年使用量较为稳定,其后每年增加约20万吨,1990年后开始下降,而氮肥总体上呈线性增加趋势(图1B).

图1 尼罗河三角洲营养盐和产鱼量综合图(垂直虚线表征阿斯旺建坝年代)Fig.1 Nutrients and fishing load in the Nile Delta (the timing of AHD is denoted by the vertical dashed line)A.建坝后尼罗河水量与输沙量曲线(据文献[11]修改);B.埃及化肥施用量变化(据文献[12]修改);C.埃及泻湖产鱼量变化(据文献[12]修改);D.泻湖中N含量与产鱼量变化(据文献[13]修改);E.四大泻湖溶解有机氮(DIN)含量与产鱼量的关系,其中菱形—Burullus、倒三角形—Edku、正方形—Manzala、圆圈—Mariut(据文献[13]修改);F.Mariut湖化肥输入量与产鱼量变化,实心圆—产鱼量、空心圆—化肥输入量(据文献[13]修改);G.泻湖溶解氧含量变化(据文献[14]修改);H.泻湖藻类生产力变化(据文献[6]修改)
化肥大规模无节制使用增加了营养盐的输入量(N和P),也大大超过了因阿斯旺建坝而“损失”的部分[12],改变了三角洲水体的盐度,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虽然埃及农业生产区域较为广泛且分散,是典型的非点源污染,但是在三角洲地区农业废水被沟渠“收集”后,会以“点源污染”的方式注入泻湖.据估计,埃及每年有4亿m3的农业废水排入尼罗河及四大泻湖[9].这些废水含有较多的盐类,导致了水体盐度增加.有研究表明[9],从阿斯旺大坝下泄的尼罗河水盐度约为150 mg/L,到达开罗附近增加到250 mg/L,最终到达三角洲北端和河口时会高达2 000~3 000 mg/L.进入三角洲后,由于径流分叉减少,城市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和农业污水的加入,水质恶化的情况尤为突出.
2.2 泻湖营养盐与产鱼量关系
1964年阿斯旺建坝后,三角洲泻湖的产鱼量大幅减少[13],然而自1980年产鱼量开始逐渐恢复,且大大超过了建坝前的数值(图1C).起初,人们对此现象无法理解,后来研究发现建坝后泻湖产鱼量增加与水体N、P等营养盐含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图1D).然而,两者关系并非人们猜想的那么简单[13-14].图1E显示了四大泻湖单位面积产鱼量与DIN(溶解有机氮)的关系,图中显示Manzala、Burullus、Edku湖泊单位产鱼量与DIN呈大致正相关,这表明泻湖N、P营养盐输入增加起初极大地促进了湖泊产鱼量;Mariut湖DIN远比前三个湖泊高,而产鱼量随着DIN含量增加而迅速下降,表明N、P含量达到一定阈值后可能对湖泊鱼类繁殖产生反作用力,图中显示这个DIN阀值为~100 μmol/L(图1E).实际上,建坝前Mariut湖产鱼量一直较为稳定,建坝后随着化肥施用量增加产鱼量也随之增加,但至20世纪80年代产鱼量到达峰值后迅速降低(图1F),这应该与营养盐输入(包括附近亚历山大市的废水排放)超过阈值而产生的抑制效应有关[13].与此同时,有研究发现泻湖水体溶解氧含量在1950—1995年间呈逐渐降低趋势(图1G),这可能是由泻湖N、P输入过量水体富营养化,藻类大量繁殖所致[6](图1H).
3 埃及近海区域营养盐研究
地中海是一个较封闭的萎缩性海域,由于周边淡水输入量少,地中海呈现出“高盐度、低营养”特征[15],因此也被称作“大洋沙漠”.尼罗河是注入地中海的最大河流.阿斯旺建坝前,随洪水而下的营养盐对埃及近海生物群落的生长繁殖极其重要[6].1964年建坝后,N、P和Si入海输入量骤降(图2A, B),导致近海PPR(初级生产力: Primary Productivity Rate)降低(图2B),产鱼量也随之锐减(图2C).后来,埃及大规模施用化肥(图2C).虽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磷肥施用量明显下降,而氮肥施用量依然在上升(图2B),这导致了输入地中海的营养盐比例失衡(图2D),N∶P比值升高(N∶P=19[15]),超过了正常藻类生长的所需条件(N∶P=16[17])(图3H),埃及地中海海域出现了“P限制”(图2E).建坝后,PPR随着N、P输入增加而迅速升高(图2B),且PPR与P施用量呈现出极好的线性正相关,这也侧面证明了埃及近海水体出现了P限制现象(图2E).Tyrrell研究表明[18],世界80%的水体都受到P限制影响,这是由于当水体中的N被消耗而减少时,上层水中的藻类可以利用空气中的N,藻类死亡或被鱼类食用排泄分解后,这部分N便可以转化成水体中DIN,以弥补损失,然而空气中没有P储备,水中的DIP被消耗掉后也就无法补充了.另外,图2B显示建坝后Si的输入量虽骤降,但其后长期没有明显变化,原因是Si主要来源于陆源碎屑,而建坝后泥沙剧减,后期虽然化肥施用量增加,但是入海泥沙没有增加.
4 尼罗河三角洲营养盐研究对我国长江的启示
流域建坝已成为现今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电力的主要途径,例如截至2000年,我国长江流域修建了超过50 000座水坝,总库容约为200×109m3,相当于长江年径流量的22%[19].特别是2003年长江三峡建坝后,来水来沙条件发生改变,对下游三角洲及东海的水文地貌、生态效应影响深远[20-21].目前,对长江干流、三峡水库和长江口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相关营养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长江口的生态环境演化,现在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尼罗河三角洲要丰富得多.然而,国外科学家在尼罗河的相关研究,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因此,为深入认识我国三峡建坝与下游环境响应过程,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应予以进一步关注.

图2 埃及近海营养盐和环境响应综合图(垂直虚线表征阿斯旺建坝年代)Fig.2 Nutrients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es in the adjacent sea of Egypt (the timing of AHD is denoted by the vertical dashed line)A.尼罗河入海营养盐N、P通量变化(数据来源文献[16]);B.尼罗河入海Si通量与近海初级生产力(数据来源文献[16]);C.埃及近海化肥输入量与产鱼量变化(据文献[15]修改);D.埃及近海营养盐比值变化(数据来源文献[16]);E.埃及近海的P限制(数据来源文献[15]);F.世界大河与湖泊水体的N:P比值散点图(据文献[17]修改)
4.1 水库蓄积效应研究
三峡大坝与阿斯旺大坝不同,它“拦沙不拦水”[22],三峡水库淤积率一般在60%~70%[23],而建坝后入海流量没有明显减少.营养盐要素N、P和Si在固—液两相中的赋存形态和含量差异较大[24],因此水库对营养盐的滞留效应不同.因此,从入库、出库和水库(内)沉积、水库内部物质迁移转化过程等角度来分析建坝对河流物质通量和组成的影响尤其重要,但目前这方面研究较为薄弱.另外,宜昌以下长江干流并无大坝,而两湖地区可能向长江输送大量营养盐,如何剥离这部分而科学评估大坝效应,也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4.2 河口营养盐研究
建坝改变了入海物质通量与组成,导致河口水体性质(温度、浊度、盐度、pH值等)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营养盐的分布规律与扩散方式发生改变,今后应继续这方面研究,特别是对与初级生产力关系密切的溶解无机态营养盐的含量监测.
4.3 河口近海生态健康研究
近些年,由于流域建坝对营养盐的“选择性”拦截,以及中下游的过量“补充”(类似埃及阿斯旺大坝),长江入海营养盐比例失衡,河口与近海也出现了“P限制”和“Si限制”[5, 20],这对藻类繁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例如,Li等[21]研究发现由于入海溶解硅通量减少,导致了长江口硅藻优势种向有毒鞭毛藻转变.Zhou等[25]也发现近些年长江口和近海海域有毒藻类的赤潮爆发频率与范围强度都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今后应加强长江口的藻类和鱼类等生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检测,这对维持河口—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保障鱼类(舟山渔场等)生产安全更具现实意义.
致谢:作者感谢埃及Kafrelsheikh大学的Mena Mohamed Essam博士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在Burullus湖考察期间的帮助;同时感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Brian Finlayson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