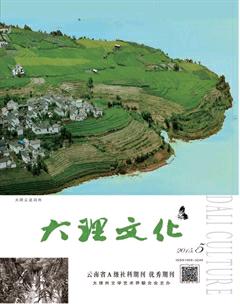悠然热水城
徐汝义
一个城,与荷结梦。
一个城,与水结缘。
一个城,像一首古词,平平仄仄,唱出烟火的多情,也吟哦山水的纯净。
一个城,像一坛陈酿,含蓄幽香,醉了游子的诗眼,也厚了归客的行囊。
洱源的早晨从热水开始,洱源的生活在热水里演绎,洱源的四季在热水里更迭。
太阳能渐渐代替了温泉水的今天,老城热水沟头再没有排着长龙的壮观队伍,也没有了松毛火烧猪的熊熊火焰,只有沟边那院老宅灰褐色的木门依旧迎着四季的风沐着水汽,透出楸木淡淡的旧香。但是,热水始终是老城人生活的一部分。理发店的师傅们早早地拉上一车水备用,鹅墩、北门、大埂、玉河几个村里的人仍会拉上几桶水烫牛水烫猪食,几条老街的街坊邻居也还是习惯拎一桶挑一担洗碗洗衣。那不断的热水仿佛就在白家庭院,何时要用取来便是。
盛水的铁皮桶长年累月在热水浸泡里结上了厚厚一层泛着黄的“水垢”,像时光雕琢的一幅老画,谁说光阴无痕?挑水的扁担磨出的光亮,走进土官充的杨家老太从小家碧玉走成九旬老人,澡堂子墙壁上结起的钟乳石般的“热水石”,洱源的光阴牢牢地烙刻着热水的痕迹。濯足浣面,洗去一日又一日的烟尘,洗白双鬓,洗尽前世今生的恩怨,从第一声啼哭到最后的“洗礼”,热水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悲欢,也陪伴过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哀乐。
闲来无事也好,心情低沉也罢,我都喜欢在老城游走,走那些不知走过多少遍的小巷,看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的老墙。北门老牌坊上的剥蚀的壁画,马家大院雕花的格子窗,土官充热水熏染的基石,文昌阁飞檐上的蛛网,它们像一册册尘封的史册,每一个章节都曾惊心动魄又洗尽铅华,还原成生命最初的底色。
正午,坐在文庙的古柏下听蝉鸣,童年在庙后的老树藤上荡秋千的欢笑依稀可辨,洋槐叶也历半百的风霜枝干更加浑厚,昔日的木楼虽然无一幸存,但物是人非的老院落,却因着这些生生不息的草木而更加葱茏,几百级的石阶掩映在草木间,苍凉了百年的风云,沉淀了历史烟尘。斑驳的青石阶上留下过多少洱源学子的足迹,也留下过多少浪穹英豪的梦?去年的大雪把门口那两棵百年青树的枝叶冻死大半,好在,根深,经过一夏,主干上绿意不减,明年,该会恢复到荫荫如盖。
黄昏,驻足冷清清的热水沟头,细细的水流再没有往昔奔腾的气势,再没有女人们拥挤不堪的浆洗,有的,只是上上下下到后山背水健身的休闲一族。往日时光像隔世的轶事,遥远到无法触及,又在热气缭绕里牵扯出难舍的记忆……
一大早,天还未亮,便在睡梦里听到屠夫们杀猪时猪最后的哀嚎,之后,上学的孩子常常都会围聚在烧猪的现场,边啃手里的饭团或是饵快,边看屠夫们娴熟的表演,那焦黄的皮香和松毛燃起的火星子混杂出别样的意味。早晚,排在长长的接水队伍后等待的急切总能被大家家长里短的谈论冲淡,熙来攘往中的彼此谦让,一路上说说笑笑像地上桶里晃出的水洒满一路,那时,老城的路似乎永远有这免费的“洒水队”。而贪嘴的小孩从园子里摘来一包小木瓜,或是小梅子,裹在小手帕里,系到一根木棍上,伸到热水里烫,青绿变成青黄,涩味少了些,便是很好的零食。遇到谁家办喜事,帮忙的人常常要背上笋片、海带、木耳之类的干货,来到热水沟边拣洗,记得那时的海带都要用刷子刷才觉得干净呢。那段时光该是热水城最热闹的季节,清苦的生活因为热水而多了温暖。
当下,外地的游客神往于地热国的舒适,本地人热衷于游泳骑车登山健体,我还是留恋老城的一股热水,这水早已在我未诞生之时就流淌在我的血脉里,如果说,民族是送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河流,那么,热水城的热水则是滋养我全部人生的源泉。我这一生,注定与它密不可分。
人们打趣洱源人“死脚不怕开水烫”,我不仅连脚,就是洗澡也一流的耐烫,似乎不烫不足以去尘污,不烫不足以称为浴。文庙旁的老澡堂洗澡,一洗快四十年,不见生分,倒是越发离不开了。站在简陋没有喷头的水管下,水柱直击,“飞流直下三两尺,热气蒸腾如仙家。”任凭热水冲泻全身,想那些高档的会所,即使再好的桑拿也比不过这地底喷涌而出的新新鲜鲜的热水。沐着这散发着地底深处矿物馨香的热水,我深深沉醉,心怀感恩。重要的是热水本身,通过形形色色的桶流进千家万户,温暖的不仅是手足,更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化解多少矛盾纠纷。夜深,汲一担热水,为夜归的家人洗去一天的劳累,泡得发红的脚明天的步子依旧会坚定不移。生命之初,只为热水而来,只需热水滋养,但是,光艳的世相迷惑了尘心,遗忘自己所求的不过是“一箪食一瓢饮”,把太多的目光积聚在那盛水的器具上,洗浴的外墙上。
热水,还在流淌,虽然早已减却了昔日的气势。我沐浴而出,人虽在江湖,但心已远在山林,白不与世相争则无物与我相争,白放下凡俗种种又何来牵绊不舍?“心远地白偏”,万物流转,随顺白然,累了,就痛痛快快地在洱源的热水里浸泡吧。
荷花处处都有,热水也并不是罕见。但是,在洱源,最奇特的是热水荷花。初出泉眼的热水温度白然很高,但在沟渠里流连驻足之后,温度减却不少,流过小河,淌进水泽,年复一年,洱源的荷花白然也就有了别样的气质。
昔日的热水城有很多蒲草荷塘,远的不必说,单是记忆里,最深刻的要算九台村龙潭周围的那些荷塘菜地。玄武阁下最老的泉眼里溢出的水四下流出,绕过村落,进了田野,老澡堂子里的水家家户户浆洗过的水,冒着热气氤氲了整个村子。龙潭里的水温很高,但在这高温的水边却垂柳依依,荷花苒苒,仿佛仙宫。儿时的我对龙潭就像对热水沟一样,充满着敬畏。老人们总是教育说,千万不能在这些地方撒野,要不得罪了神灵就要生怪病了。神灵的有无且不论,但对大自然由衷的敬畏我以为却是始终不可缺的,天地之间,人力何其渺小,如何参悟得了天道轮回?九台可以饮用的热水不仅给了九台人标志性的“热水牙”,也给九台莲藕独特的甜糯。不过,九台成为了城中村的今天,热水莲藕一去不复返。
九台的仙梦终于沉入地底,而热水城的水韵也像逝去的童年一样,浓缩进了玉湖公园的荷花里。洗心泉边,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早到的占个位,晚到的附近随坐,小小一潭热水,大家热热闹闹地挤着泡脚.热水在这头冒着泡,荷花在那边自在摇曳。公园几乎是洱源城最后的水泽痕迹,过去这里朝北就全是沼泽荷塘了。记不得有多少回,我总在梦里来到这空阔的荷塘边,怯怯地望着高高的荷叶,想象荷塘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而现在,去茈碧湖,也不过像到家的后院,洱源没有变小,只是城变大,大到覆盖了记忆里所有的原野。
好在,还有秋天,还有茈碧湖日益繁复的生态湿地。秋天的洱源清丽而疏朗,登高远望,绚烂的田野弥散着金黄、橙黄、嫩黄,而牵牛爬过院墙的狗尾草,在篱笆的一角,在包谷的胡须上,在曼陀罗的花枝间,在一架暗红的豆角上,在一丛密密的刺篱间,就这样红着,紫着,雪白着,体育场里蔓延开的草丛里也不乏它们的倩影。看着这绚丽的秋草,昔日的荷花淀再没有了,那些可以编草席喂小白兔的蒲草没有了,蒲草滩荷花塘边的热水罗非鱼也没有了……儿时的我不明白这一片冒着热气的水塘怎么会有鱼,它们怎不怕热,只是喜欢罗非鱼没有细刺的鲜美。在那方热水边,跟在母亲身后买刚捕到的罗非鱼。
往事依然清晰,但水泽早已成为小区,再不见半点水的痕迹。于是,所有关于荷塘的怀念只有到茈碧湖边去体验。
趁着明月夜,泛舟湖上,“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独对一湖秋水,独对自我,在清清水中照见心灵的尘垢,然后洗净。坐在湖中间那长长的石堤上,高原的夜风卷起波浪拍打着堤坝,深沉中留下久久的回响,深邃里弥漫着喟叹,“逝者如斯夫!”百年之后,我白归于尘土,千年之后,茈碧湖水还在否?眼前,湖水荡漾,星光之下,山影重重,秋荷几亩,方塘无数,水天相映,天高水远……
沧海桑田,岁月更迭,有些原本生动的名词最后都会成为历史名词,但依旧铭刻在鲜活生命的履痕上,丰盈一片土地。
热水城有很多地方几乎无人再提了,比如鼓楼街、城门充、文昌阁、大洗脸盆、凤凰台、白沙井。鼓楼街在南门,想必在古代该有个南城门及钟鼓楼,六诏之一的浪穹诏诏府,再小也还是会有诏府的形制。那么,那个遥远的古代,叶榆旧郡,浪穹古诏是怎样的呢?依山傍水,高原泽国,鸥鹭翔集,但水患亦频发,否则,就不会有观音老母背灵应山治水患一说了。而看到东边的小红山,真的像人们背箩筐用的背带,洱源人俗称“篼箩片儿”的。
追忆古迹,马曜老先生上世纪30年代夜游茈碧湖,天亮还能泛舟逆流回溯到洱源城东门小桥头,可见,未围海造田时,洱源的水域是十分广阔的。今天汉登村东曾有蛤蟆塘,鹅墩村周围的湿地荷塘还有残存,只是大庄村解缆上船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了。又忆起徐霞客游洱源时的情形,告别剑川,过了牛街,一路兼程,只为何公一句“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便急匆匆赶到浪穹拜访曾在四川郫县任过知县的何鸣凤。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水又是何等的深厚澄澈!过了赤硐鼻,南湖北海,湖称茈碧,海称洱源,一带如苏堤的石堤曲折向西,湖光山色,岛屿如珠。九台村是个形似老龟的小岛屿,百户人家居于其上,中有玄武阁,九股热水从阁下流出,那是怎样的人间仙境,真无从想象了,而洱源城里的护明寺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昌阁还有一点旧迹,作了青昌街的本主庙。
夜安静地来,洱源的夜来得早,即使是炎夏,即使是城里,晚上十点以后就静下来了。而到了冬夜,虽没有北国的冰天雪地,寒意还是驱赶人们日落而息。于是,太阳的余晖刚刚散尽,各家各户就在院子里升起栗炭火,伴着松球、玉米棒、碎木柴的火苗和缕缕青烟,黑黑的炭便在火中涅槃,那种红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不仅暖热整间屋子,更暖热人情,而且还有那浓浓的炭火香,这种暖香是任何的取暖器都无法替代的。
我又想到许多年前,很多人家还没有水泥地时,人们就地挖的火塘,上面支个三角架边烧水边烤火,有的则直接在梁上系根绳索,下面再拴个钩子,把茶壶钩起来烧水。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房梁上、瓦片上、椽子上就有了乌黑油亮的火烟痕。围着火塘、火盆也就衍生出各样的故事,红红的炭火映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纯美,映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挚情,当然,也映着谷贱伤农的感叹,空巢老人的孤寂,留守儿童的幻梦。但是,毕竟有这微光在,多少也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洱源人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随顺自然。当那些被强大的物欲冲昏了头脑、迷失在城市的霓虹深处的人来到洱源,寻找他们梦里的原乡,无需走得太远,更不必跋山涉水到那人迹罕至之地,只要在夜晚洱源的街道上走走,心就会宁静下来。
很多时候,我走在洱源的老街,路灯早已被顽童打坏又未到春节维修期。路上一片幽黑,有时从沿街的屋角会投来些许新月或残月的微光,有时是人家窗户透出的灯光,偶尔是晚归的人打着电筒的光,很容易让人想起80年代在洱源电影院看老电影时从放映孔投出的光,想起更早的广场电影,想起那些憨厚质朴的面庞,想起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想起曾经全民写诗的时代。
放慢脚步,悄悄走在幽幽老街里巷,夜的黑淹没了所有的华丽,听得见的只有轻轻的呼吸。生活原来如此简单,人要的其实很少,“一箪食,一瓢饮。”淡淡的月光映照着青瓦泛出幽幽的光,如流淌在瓦上的小夜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的浪漫不仅属于李白也属于洱源人。月影与白墙相映成趣,更显出照壁诗意的美,加上那青石路.多少有江南的情调了。
四面环山的洱源坝子,像一个庭院,与天地很近,与喧嚣很远。夜登凤凰山,独坐石台之上,新城的灯光映亮了天空,尘世的灯火与漫天的星斗交相辉映。隔着凤羽河,老城已然沉人梦乡,而散布在坝子的各个村落星星点点的微光,即使相隔甚远也会让人感到那份家园的温暖。
这样的时候,高楼淡去,山影淡去,我仿佛又能回到那个高原的泽国。九台村外的沟沟渠渠里热水蒸腾,热水滋养出的黑泥肥沃了千亩的藕塘,一到夏天,整个坝子,便在荷花的清香与芦苇的摇曳里生动起来,清凉起来。夏末,采菱的白族姑娘划着小船悠悠地在湖面上荡漾,像一朵娇媚的茈碧花。城里的老太则坐在大洗脸盆的石台上,浆洗衣物,水汽熏得脸红润润的,一如不远处塘里将谢的荷花。凤凰台外,白沙井边,汲水的阿哥正准备回家给老爹煮一块白扎五花肉,好下酒……
洱源,沿着亘古的青苔小巷,伴着满坝的新荷香,静静地沐着罗坪山风,走成茶马道上的古驿,走成蒹葭水泽的一首民歌,走出荷香温泉里的一段禅机,走出朴素自然的田园情趣,走出闲远悠长的诗情画意。
人在洱源,心如热水,宁静闲谈,随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