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地时光(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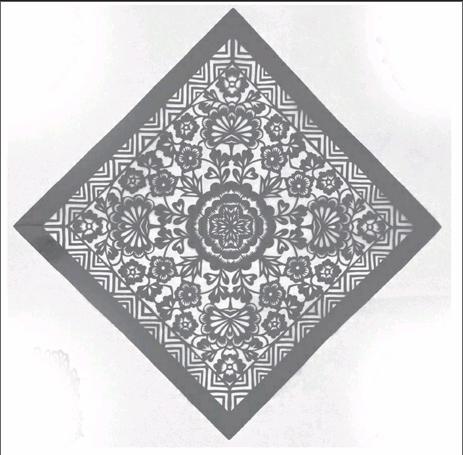
初秋盛宴
整个十月,天地一派澄明,枯草的反光都异常耀眼,天和地经过一番激烈的征伐,大地恢复了久违的平静和初始的面貌。所有的植物、动物都成了深沉而头脑清醒的思想家,就连一些石头中的晶亮颗粒都发出光芒,想高谈阔论一番。
在这秋冬和谈罢兵的日子是写作和沉思的最佳时机,这个时间,思想狂欢的鼓点才刚刚敲响,激烈的春夏和纷忙的秋日就是纷扰和喧嚣的世界。现在,秋刚离去,冬天尚未拉开大幕,这是些值得特别眷恋的日子。经过清醒、沉寂的短暂停留,仿佛是失败的士兵在收拾残破的旗子时宁静的内省时刻。初冬清晨的太阳格外清晰,像一把明亮的大扫帚,祛除了所有暗夜的印痕。穿梭在神木大地,沉浸在那些由真善美构建的荒野和村庄。我的视觉、听觉、嗅觉在享受了一番精美绝伦的盛宴之后,一条思想的溪流缓缓而至,树林的绿荫、鸟雀的欢鸣、腐草那狂野的气息纷沓而至,成了构筑我生命的全部材料,自然中的色彩、音律、味道无不向我们展示真理之于生命的最佳摹本。
荒野性格
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荒野地带,亿万年前,真正与贫瘠和黑暗斗争的是这些岩层高耸的石山,如今自然疯狂的举动被平息了,山峦安逸地沉睡在大地上,漫步于无垠的群山之间,峨然陈列的山所显示的从容之状,充满善意的面孔,让我觉得它们才是自然的主人。大山保持着不变的威仪,一些巨大的石头崩落了,被河流带走,被水冲刷,棱角磨掉了,变得光滑木讷,而山体永远以更古不变的姿态傲然于世。它们对季节的变迁不以为然,漠然视之,这些高傲的远古战神,一年的春花秋落在它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一场洪流也无从掳走什么,当春天远去,夏日来临,山头只增添了些许稀疏的淡绿,仿佛是在一年中仅做的一次简单梳洗。
山脊之上
山脊之上,这里有最出色的子民,无尽的高空和荒野之间仿佛只有像风雨雷电这些出类拔萃的成员才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圪针和蒿柴之类的野草密密麻麻地占领着这块高地,这些荒草承受着最强烈的风寒、干旱。山脊之下,都有一条忠实的河流趟过,硬岩层、砂质岩层被一路切开,裸露的岩层就是镌刻着真理的书页,这条河千万年都在书写和阅读着这部大书。大自然对只倾慕名山大川,江河湖海的人永远心存芥蒂,绝不会将自己真正的秘密倾吐半点儿。唯有对那些将足迹遍布在草丛中,将眼睛定格在它最微小的事物上的人才会敞开自己所有的门扉,展现它全部的美。
溪流
对于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的小溪流,大多无人问津。无论春夏,它都恪守着做为一条溪流所有的准则静静流淌,它没有明确的方向,山川造就了它们的路途,时节首先向它们发出诏令,它是自然界最忠实的顺民。它们没有“河润千里”的宏愿,只是滋养着沿途的草滩和饥渴的昆虫,一些杂草就可以将它们完全隐没。在平缓处,溪流便沉寂安逸地淌过,跌落处则倾泻而下,不做任何迟疑和停留,如遇高处,不急不躁,安然地等待蓄满,当汇入浑浊的大流时,它依然澄澈明净。所到之处全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些朴素的小村庄,牛羊小憩反刍的滩涂,鸡鸭嬉戏打闹的洼地,清澄的流水一路携带着农人恬静的歌谣蜿蜒而去。
沙漠
在神木北部的沙漠地带,豪爽魁梧的大汉,携带着鞑靼人和蒙古人驰骋草原的气息,他们的性格映照着如同天空一样空旷而坦诚的蓝,毫不掩饰什么。而沙漠这种流动的、不确定的砾石堆积成一个令人迷茫的区域,彰显着狂野的,慵懒的哲学家风范,经过季候风亿万年的筛选而被确认下来,就在这些近乎不毛之地,沙柳随处可见,宛若一个个清醒的沉思者,不做任何解释和揭示,风沙掠过,它只是在广袤沙漠上倾吐一些小秘密而已,一些善于伪装和弱小的生物在这里小心翼翼进行着他们微小的事业,那最深沉的思考全部孕育在沙漠的最深处,永不宣读。
消逝的归来之歌
五月一过,当遗鸥鸣唱着异国情调的归来之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凯旋而至,红碱淖顿时燃起了野性的火焰。欢爱的气息弥漫在辽阔的水波之上,让整个北方的夏天充满健康的活力。而这终将逝去,随着煤矿开采,水位下降,那些被遗鸥视为天堂的沼泽已经被干裂的沤泥取代,湖泊早已沦为出产钱币的苦力,汽艇咆哮的鸣笛和矿山轰隆的爆破已奏响遗鸥的挽歌,人类在建造美的领域无甚作为,现在连保护美都力不从心。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对我们灵魂的蹂躏和糟践,我们心灵的真善美都来自这些原初的、完整的环境。我应该欣慰,遗鸥毕竟有人为它敲响丧钟,而人类的丧钟将无人敲响。
河边丛林
这片小树丛长在河边的沙滩上,风将平静的河面吹起波纹时,这里即刻也会沙沙作响,努力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纵然它微不足道,朴素得再平常不过。足有十公分厚的落叶层,如果从它的一侧垂直切开断面,从下到上,这难道不是一部艰辛的家族史吗,最下面那一层成粉末状,和沙粒已经不分彼此,那是在它们从沙丘里长出来的头一年留下的,细心的梧桐树不会丢掉任何生长的记忆,太阳也不会将照在枯木上的光芒略去。这片小丛林有着和大森林一样的胸怀和虔诚,它从贫瘠的土地里汲取元素之后,无怨无悔地将落叶层层铺在足下,从不肆意纷飞,现在没有叶子落下,那些注定要在不远的秋季飘落的树叶,在盛夏激烈的光辉中尽情地生长着,没有一丝怯懦,无论是顶端的还是底部的都英姿飒爽,洁绿如初,纵然风沙肆虐,但不曾染上一粒微尘。长在各自信任的枝干上,哪怕是被昆虫叮咬,卷曲的树叶也毫不示弱,极力地试着撑开叶面,展示它的光华。那泛白、布满裂纹的树皮,面对它,我为之一振,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的变幻莫测,一棵树撑开树枝,长满绿叶的技能无与伦比,而他自身的躯干,却着实平淡无奇。他完全可以运用自己杰出的才华缔造一件华美的外衣,而它却心甘情愿附一身糙裂的装饰。可是,只要用指甲轻轻抠开一点,浓绿的色泽便凸显出来,那种绿放佛来自生命原初的萌动,犹如来自孩童年代的声声呼喊。这些梧桐树俨然是一群满腹经纶、超凡脱俗的圣贤,着一身粗布麻衣,在河畔一隅,随意席地而坐,姿态不一,没有高谈阔论,只是散淡闲适,任凭水逝远东、春去秋来。此刻,我就坐在它们中间,愿作一个温顺的孩子,听它们谆谆教导。
时至六月
北方的夏天还没有显现出应有的爽朗和热烈。西北风不时吹来,卷起尘土、柳絮、以及干枯的碎叶,整个高原狂躁不安,湿润凉爽的东南风吹来了,它们是夏天女神派来的先遣队,先行告知这里的每一个居民,打起精神迎接它的到来。当一场雨紧随其后,让所有轻浮的事物落归泥土,大地一片清朗。阵雨说来就来,时紧时慢,风忽南忽北,像打架的天地一般显得手忙脚乱,不过,很快便散去了,一时又静若处子。有时在半夜突然电闪雷鸣,闪光照亮夜空,像一架巨大照相机的闪光,定格这惊恐的一瞬。自然要彻底放纵自己,挥洒它的真性情。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些卑微和高尚事物初具雏形。
隆重的邀请
秋天,当农人奔赴在收获的田间地头,空下来的村庄,成了麻雀宣告接管的世界。远远地,那些鸣亮而凌乱的聒噪在一目了然的枝杆间混响成一片,落叶纷飞的场景被这些喧闹彻底击退。这是它们钟爱的、清晰的、明朗的时节,它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今日每一顿丰盛的午宴,那些谷米和稻黍的美味,但对渐渐步入食物匮乏的冬天置之不理,不做任何准备。它们在枝杈间熟练地跳跃,梳理羽毛,相互传达浓浓爱意,有时,成群结队在空中忽上忽下,任意东西,秋天是唤醒麻雀舞蹈天赋的绝佳时机,无论是大胆的雏雀还是经验丰富时常警惕的成鸟,都要一展绚丽的身姿。现在,树木和山体都变成了与它们相近的浅褐色,大自然向它们发出了隆重的邀请,它们要在这经过漫长等待的伟大的共鸣时刻喧宾夺主。
麻雀
相较于有着华丽羽毛的其他鸟类来说,麻雀着实寒碜了点。它就像贫苦的农人般勤勤恳恳营务着自己简单的生活。一身朴素的土褐色,成群集队穿梭于乡间宁静、晴朗的天地。麻雀是乡村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当一群接一群聒噪的麻雀,急促的嗓音齐奏出欢快的和鸣飞上飞下、掠过农家上空,寂静的生活顿时充满了原汁原味的活力,平静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诗情画意的美好时光。天性活波的麻雀,嘴短但有力,有时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活动筋骨,时而在院落中蹦蹦跳跳,跳动时胸脯直挺、头部昂起,宛若沉浸在芭蕾舞曲中的仙女。
是麻雀,率先拉开乡村清晨的帷幕,简略的早餐用罢,它们便站在农院旁的树枝上,高唱起黎明的赞歌,鸣声混响成一片,没有一丝间歇,直到晨曦洒满整个村野,农人拾起农具,推开房门,它们便四散而去,开始一天快乐的觅食之旅。它们没有在高空翱翔的宏愿,只是在离大地不远的空中驰骋,当它们吃饱之后,便开始呼朋引伴,一大片麻雀整整齐齐在乡村空旷的田野之上前呼后唤,掀起一股农耕事业永恒推进的空中浪潮。
原住民
听麻雀飞行时笨拙、吃力的凸儿凸儿声,就知道它吃得有多么胖了,每一顿丰盛的餐宴后,幸福地饮下青草返青时送给他的露水。一身灰溜溜的颜色是按陕北的颜色精心缝制而成,终生不改,它才是这里的主人。当我们举起弹弓瞄准它们的时候,它们该有多伤心,而且它并没有像我们一样锯掉它们栖息的树枝,我们应该付给它足够的租金,而不是扒光他的羽毛,我们才是这儿的过路人。你看他们并不由谁带领,有时单个从这枝跳到另一枝,有时成群结队飞往更高的天空。
葱茏之界
十月,自然仿佛大病初愈,从那些暑热难耐的日子里站了起来。像一位激情洋溢的油画家,上午还是万里碧空,一到下午云朵密布,而在傍晚,夕阳印染天际,一片通红,花草树木前几天还是中规中矩的绿色,现在一下子失去了耐心,它打翻调色板,红、黄、绿任意涂抹,这幅画宣布作废。到了十月,大自然再也按耐不住,仿佛接到了更高的、不可逾越的指令,决定用一场雨来推进速度,堵住所有植物返青的路途。自然开始举行最后的狂欢,树木一年一次盛大的作别开始上演,每一片树叶都是一篇精美的作品,作为阅读大地之书的读后感,趁着秋风刮来之际一并投递出去,它要用整个冬天沉思默想。
高大的杨树就是这场狂欢曲的指挥家,它熟知生命历经春夏的所有音符。柳树则是秋天的代言人,是它,最后守候着冬天的到来。它要在冬天彻底到来之际,站好最后一班岗,抖落一身金黄。如果不是树木装点和捍卫着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图景将是多么地了无生机,不堪忍受。
无论是在北极严寒的雪原上绵延数千公里的泰加针叶林,还是在亚马逊河域的热带雨林,抑或陕北高原上孤傲耸立的箭杆杨,它们所处地域迥异,种类繁多,形态多样,有的色彩都相差甚远,但它们那深入大地、促其直立的强大根系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地层深处的共同元素潜藏着强大的创造力,为世界呈现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绿色画卷。树木是土地和太阳精心养育的长子,是自然显示自信和力量的杰出代表,它们或集群、或孤立,都展示出其健康、年轻的活力。在风雨中适意地梳洗,在酷暑中强烈地陶醉,在冰封中久久静默。当我们惨遭不幸或心生苦楚,置身于密林深处,那由纯净、繁茂的叶子和分明的枝干所搭建的幽静处,正是心灵最理想的避难所。
客居
在农人的大地上,我仿佛看到了黄金时代的再现,那些被我们成为贫苦人的农人,他们恰恰是自然委派的使者,他们是山川的兄弟,河流的姐妹,他们性格鲜明、勇敢、坚韧,将节气和征候作为唯一的行动指南。暮秋,在熟透的玉米地,随着一阵清风吹来,那些干枯的长须叶像手臂一样相互摸娑,发出“嗖嗖”的欢快之声,相互告慰着结束这一段荣耀的旅程。广布在神木土地上的村庄,大都以地形地貌来命名,他们用最虔诚、简单的方式表明,他们仅仅客居于此。
第一排冰凌
在北方十一月的日子里,干燥寒冷的天气彻底来临,当农人将最后一袋粮食装仓入库后,偶尔还会去已收毕的田野中走上一圈,回想一下今年与它相依为伴的日子,这是思想丰收的时刻,他低垂的头颅,缓慢的脚步显然在土地中搜寻最有价值的精神颗粒。在这样的日子,应该敞开大衣,漫无目的大步行走在高山上,去初冬领略一下那完全拓展开的世界。此刻,冬天还没有放开胆子向前大踏步迈去,那湿地和屋瓦上的霜晶,仿佛是预先的试探和前奏,或者是一次必要的热身活动。在初冬的深谷中,那些小溪从萧索的枯草中幽幽而至,当经过一些斜缓的石槽时,细碎的水花在石阶上急骤而下,如撒落的银白色水晶,发出清悦而奔放的舒畅之音,抖落一身欢乐,仿佛是对秋天致以最后的、深情的答谢辞。就在河道的漫步中,遇到了入冬以来的第一排冰凌,它们还没有显露出棱角分明的锋芒,在依然温煦的阳光和激越的水流面前显得谨小慎微,犹如冬之大军派出的侦察连,以确证,秋已彻底离去。这些冰花着附在河床边沿,在草丛的幽深处,在潮湿的角落里,一些透亮的冰锥倒挂在岩石上,在阴暗的角落里逐渐拓展开来,冬天正以足够的耐心来彰显它的雄心壮志,抒写它铁骨铮铮的英雄史。
冬日面孔
冬天就是大自然枕戈待旦的日子,它躺在落叶铺就的绒床上,对来年的春天开始细算运筹。就在这枯草遍及的荒野之地,目击之处,一片肃穆威严之感从四周袭来,褐色的土地仿佛陷入更经久的沉思,它让所有的生命褪去昔日的繁华。树木只剩下遒劲的枝干直立在风中,河流冰封,开始收集整理它叮咚的乐谱,忙碌的松鼠终于要堵住洞口惬意地睡上一整个冬天了,这是理智的一次彻底胜利。冬天是自然用最精简的话语写就的一部真理之书。大地结束了浓妆艳抹的日子,披一身素装,天际中闪电和雷暴那些怒气冲冲的性情变成了安静、仁慈的善意面孔。深入冬天,就是走进了思想的源头。就连最不引人注目的小草,此刻也显示出了一副平和从容之态,先前那些柔情蜜意和妖娆风姿全然不见,颜色全部变成枯黄,叶子上的纹路清晰可见,枝节硬而分明。大斑啄木鸟敲击树木的声音干脆有力,仿佛可以将铁钉钉入树干。野兔在这个时节显得得心应手,强健的筋骨终于在那些让植被缠绕的岁月中脱身出来,释放它对自由狂奔的憧憬。
极简的法令
大自然永远在重新开始,对它的收获和失去从不估量。它要在风中一次次清扫自己的院落,让雪一场接一场来掩盖它在其他季节的迹象,仿佛那都是一时冲动而挥霍的情感印痕,要在冬日来一次最深彻的反省。在十一月,自然要作一次彻底的摈弃,将那些荒枝侧叶统统遗弃,河流禁止奔涌,让阳光从此一如既往,鸟儿无需隐藏,自然要立志实施它最高的理性和极简的法令了。
自由的猎人
黄土高原此刻成了动物露天游乐场,不会有一只落单,他们或三五结伴,或成群为伍,在枯干的草丛中,收割后的坡洼上,平坦潮湿的原野里,灰蓝的鸽子,五彩缤纷的雄野鸡,勤劳的野兔,在我们不经心的漫步中,时而窜出,让人心惊肉跳。强健的翎羽发出扑棱棱的震响,划破宁静的高原,似乎它在不停地向我们辩驳高原的贫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母山鸡,胖乎乎的身子,颜色几乎和土地接近,不仔细看,很难辨认,除非它扭起屁股走动起来,才可以将它从地上分辨出来,但它们似乎并不急着飞走。我试着逼近它,体验做一回猎人的感觉,它跑了起来,它那细短的小腿让我坚定地认为,不用多大力气就将它按倒。这一群有七八只,脖子伸得又高又直,完全对我的攻击持藐视态度,它的高傲和松弛激励我大步跑向它们。它们依然没有起飞的念头,不时回头向我瞥过来,好像在确认我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对象。它们有足够的信任来度量任何一方的伤害,但屡试屡败,终究还是飞走了,只消片刻便停在了不远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继续它们快乐的觅食旅途。其实,我只不过是想陪他们跑一段,锻炼锻炼筋骨而已,猎人,我只想做猎取快乐和自由的猎人。
坍塌的院落
土窑洞多年不住了,围墙风化、坍塌,门斜吊着,门檐上的土块大块大块塌下来,曾经忙碌的石磨早被泥土掩埋,在一片败落中院子里却生机勃勃,蒿草、榆树、槐树肆意生长,密密麻麻,鸟儿随意起落、飞进飞出、叽叽喳喳,爷爷当年和李贵茂打了一架争过来的木橼,还准备做羊圈门子,如今成了松鼠的窝窠,人很难再次进入,爷爷奶奶早已去逝,早把家当归还给土地,自然已经盖上了它的印章。
晨思
十二月,冬天彻底拉开它的大幕,正襟危坐。那些严寒中的生灵都已准备妥当,开始接受它冰冷的训令了。清晨,太阳升起时格外庄严,殷红布满整个东方的山脊,在冬日短暂的白昼中,这是最神圣的时刻,天空在腊月犹如一个安静的处子,它收起了电闪雷鸣,不再对土地大喊大叫,天地一时达成和解,再也不用对那些肆意招摇的植物指颐气使。暴躁的猪獾在艰难地吃完河边的最后一批根茎之后,沮丧地离开了,冬天把几乎所有的宴席全部解散。现在,是天和地畅谈的庄严时刻,那高悬的蓝空,以从未有过的平和表情俯瞰大地,阳光以更精更纯的色质倾向原野,草木、鸟雀不再接受它的温度,我的心仿佛也被带入到那浩渺的天空中,聆听晨曦的谆谆教导。
寒流与暖阳
寒流在十二月接撞而至,陕北高原完全进入沉睡期,没有一点生机,整个高原犹如矮下去一样。风开始肆虐,朝高地猛吹,登上任何一个制高点,远处沉闷的“唰唰”声一阵接一阵袭来,又向远处掠去。冬天的风如矫健的语言,行走在这儿,身体任何裸露的部分都会被无情地告知,让人瑟瑟发抖。不论什么树木,在这个时节,几乎都成了一色,不走近观察,无法辨别。凛冽的风和明亮的阳光是构成冬日的主要内容。前者是严厉的父亲,鞭策、激励我们接受考验、鄙歪弃邪,后者则像一位慈祥的母亲,自始至终用温情滋养着我们,延续着爱。
屋宇
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围在火炉旁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运气好,遇上寂静无风、天朗气清的好日子,就不应该蜷缩在屋里了。关好门窗,向旷野走去,让整个身体沉浸在被光瀑频频光顾的高原上,让炉火独自燃烧去吧。爬上那些山,任何一个山头都是一个制高点,极目望去,一个半径约有五十公里的圆形舞台以我为中心延伸出去。远处都被氤氲的气流围拢,我所站立的位置成了世界的中心,犹如第一次涉足这里,眼前的一切都崭新如初,仿佛是阳光、天空、山、枯草、零星的树木为我突击搭建的一个明朗的屋宇,我在此轻轻松松就独享了帝王的荣耀,此刻我极其富有,高悬的太阳成了我的火炉,那被谷茬铺满的坡地,就是我的餐桌。虽然眼前景物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但无疑,我们彼此都找到了理想的归属,它所呈现的精神画卷上镌刻上了我的名字。我坐在一片堆满玉米秸秆的地头旁开始分享这些圣餐,即刻,全身被晒得暖烘烘,先前的寒冷也变成了难得的凉爽。我将手伸进一丛密密麻麻的枯草当中,同样也是温暖的,整个高原徜徉在明晃晃的暖流当中,没有任何遮蔽,一些沟壑也在沐浴了清晨的红晕光线之后,此刻让都让位于另一侧的山坳。在这温暖的光影里,我被抚摸,被舔舐着伤口。坐在这里真的有疗伤的功效,心底那些阴郁的角落也一同被照得通明,我愈加惬意起来。此刻我就想做一个懒汉,每天,像蛇或者乌龟那样借助阳光来恢复活力。温暖,这隆冬的温暖尤其令人感动。当太阳在远离了子午线,冷气团控制了寒冬时,遍布每个角落的温暖就是它对大地许下的恒久的诺言。
沙棘
沙棘在冷冬的遴选中,无疑是骁勇的佼佼者,大自然绝不会让懦夫来做它的守门人。我无意中发现了路边长满的沙棘,橙色浆果缀满每一根枝条,这是在冬日难得一见的一种野果了,我试着摘了一颗,不料轻轻用力就将它挤破,手指上沾满黄色的汁液,我尝了尝,浓郁的酸裂感传遍全身,不禁打了个寒颤,随后一种陈年红酒的醇和圆润之感溢满舌尖,顿觉清爽、激奋。冷冽的寒冬没让它冻僵,反而让这一树野果更具野性的风味,冬天对一棵沙棘来说,成了它酿造醇洌性格美酒的酵母菌。对于这些深处冬日、生机不息的生命来说,冬天所需甚少,却是它们性格得以疯长的季节。
◎惟岗,本名刘维刚,1987年生于陕西神木,神木县诗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神木县作家协会秘书长,《诗界》主编、《神木》杂志编辑。著有散文集《自然札记》《野地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