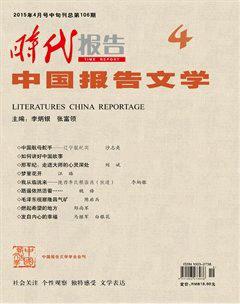花岩寺之殇
杨河
近几年忽然喜欢上了追踪寻古,特别是对家乡的一些名胜古迹,就象咀嚼腊肉骨头一样,越嚼越有味儿。这段时间追踪花岩寺古迹,钻古书堆,爬山涉水,实地踏勘,整日被花岩寺之殇所困。
花岩寺位于四川省中江县青市乡以西的法雨山鹿。历史上的花岩寺,以古迹与风景著称,曾经红极一时。由于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沉淀,如今,花岩寺已经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没有几个中江人知道了。就是土生土长的青市人,也只有一些古稀老人在茶余酒后,偶尔谈起花岩寺,还是那么津津乐道。
说花岩寺,必须要先从青市说起。青市乡场距中江县城约三十公里。民间相传始建于汉代,兴盛于三国至明朝末年。在青市的后山,曾经发现大量汉代崖摹,出土了陶制品。乡场因始建于一棵大树旁的大青石上而得名——青石,后演变为青市。因地处中江、罗江、德阳交界,又是古代川东北通往广汉、成都、绵竹、广元、三台的交通要塞,商贾繁华,远近闻名。据1930年版《中江县志》载:青市镇,距城五十五里,为金汉德罗盗匪出没之所,西北界德阳罗江,山峦重叠,藏奸实易,其要隘北有四方碑垭口,西有钻子口交罗江界。又,场西九里有花岩寺垭口,场北七里有聂家大梁子,泰广山下二里有猪儿石垭口,均当冲途。
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青市场上有东岳庙、满台寺、南华宫三座寺庙和两座钟鼓楼,每个庙宇占地都在2000平米以上,钟鼓楼有三层高,呈塔状。而从青市场镇到法雨山花岩寺仅仅九华里的途中还建有大小寺庙46座。这些建筑全都是石、木、瓦结构,屋顶为五脊四坡形,筒瓦、飞椽棱角,脊顶、挠角、均有石雕和用碎瓷片拼作的各种花纹图案相嵌于上面,殿内的挑梁、殿门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彩绘、描金、墨绘、雕刻等,庙宇内有大殿、相房和院落。后山上的东岳庙,是纪念西周名将黄飞虎的寺院,内有观音殿、东岳殿、大雄宝殿和戏台,可容纳千人以上在庙里看戏或参加庙会活动。东岳庙始建于明朝中叶,毁于明末清初。清乾隆年间重修,解放后文革破四旧,又毁于一旦。后由百姓集资在原址重建。东岳大帝又称东岳泰山之神,其身世众说纷纭,有金虹氏说、太昊说、盘古说、天孙说、黄飞虎说等。青市东岳庙供奉的是西周名将黄飞虎.而东岳泰山之神作为泰山的化身,是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是历代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
另一座寺庙满台寺也很有名。据1930年版《中江县志》载:满台寺碑在青市镇场外山顶,碑末有赞曰:乘教本一,法门不二,业基累明,功由积地;渺渺长津,遥遥遐辔,道有常尊,神无口器;说屣王家,来承宝位,慧日晨开,香雨宵坠;籍感必从,凭缘斯至,曰我圣储,仪天作贰,商想龙柯,瞻言思媚;镌石图徽,雕金写秘,望极齐工,举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备,敬勒玄踪,式传遐懿。
旧时,每年的农历三月廿八日前后三天,是青市最为热闹的日子。传说三月廿八是东岳大帝黄飞虎的生日,为了宣扬仁民爱物、忠君孝亲的传统伦理,每年农历三月廿七、八、九日,东岳庙都要举行庆典活动,庙宇前殿主祀泰山之神东岳大帝,旁配祀炳灵公,碧霞元君,还有文判官、武判官,后殿是地藏王菩萨及其他神像,所有神像都管人间赏善惩恶。当时香火很旺,庙会规模庞大,内容十分丰富。神像出会,仪仗孪驾,威灵显赫。游驾时,耍狮的、舞龙的在前面开路,信士们抬着东岳大帝、火德真君的木雕神像轿子出抬,鼓乐随后,然后是扮演化妆的列队,有牛头马面,活无尚,死无尚(头戴长帽,长舌鬼脸,手执铁链)有判官小鬼。还有八仙、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故事人物,这些角色全部由一般老百姓信徒自愿化妆扮演。还有送伞的、送帛的、送扁的紧随其后,说是接受菩萨惠顾保佑,日后能消灾避难。
东岳大帝神轿领先巡街一转,家家都会还福许愿,举香祈祷,一般青壮老少全部融入游巡活动,热闹非凡。庙会时间廿七、廿八、廿九三天,东岳庙香烟弥漫,火光烛天。大路两旁,搭满帐棚。队队乡会,接连不断。旗伞执事,争巧斗胜,锣鼓鞭炮,震耳欲聋。方圆百里村庄百姓也都赶来观看,小商小贩趁此机会来展销商品,还有木匠、篾匠、铁匠、女工都赶来展销手工产品。还有拈香的,江湖艺人,星相术士。商旅云集,买进卖出,购销两旺。
历史上名噪一时的花岩寺,就坐落在距青市乡场约九华里的法雨山顶,海拔680余米,属四川龙泉山脉尾端。据1930年版《中江县志》载:花岩寺,青市镇法雨山,宋敇建名广利寺,有万历十四年残碑。又载:广利寺碑,在治北青市镇花岩寺,有明直隶潼川州中江县广利寺修造碑记,未注龙集弘治四年岁在辛亥正月十五日邡江刘可茂撰书按宋大中祥符四年赦赐宁国寺碑,梓洲玄武县法雨山花崖院宜赐广利院为额,则花崖乃古名也。再载:广利寺源流碑,今碑存。有记曰历考广利禅寺,始于宋敇建修,殿阁峥嵘,山林蓊郁,国命专利,指挥黄公宣义同僧奠慰忠孝国家。宋世衰歇,元夷一混,兵锋燹起,殿宇燔灰。我朝基迹尚存,幸得灯焰不息,开山祖师胜中原,系湖广荆州石首人氏,云水遨来,以为始祖,接徒禧恕,称王正殿,并理斋堂,昌本重建,法堂.天王二殿,嗣续坤修,砌金刚台,施主罗乐山另碑,有罗乔山竖立金刚殿,七代法孙宗训修塑弥陀.接引,鼎新左右神堂,功绩增加,堪为福地,由是释宫落成,刻碑记曰:花岩孤峰,绝顶崆峒,天造地成,崑崙发踪,前朝赦赐,始建梵宫,大明洪武,基址尚宏,山川如故,风景亦同,外有四景,以光其中,东渊澄井,虹霓现空,南出龙泉,关将名雄,西生磐陀,尊者留踪,北有宕岩,云霞现彤,两山耸翠,八面玲珑,天缘胜祖,克苦修崇,经营台殿,香火朝供,光前启后,永壮宗风,万庵支派,灯焰无穷,皇图巩固,帝道昌隆,十方檀越,共享时雍,勒碑为记,以表厥功,亘古亘今,后代知宗。未注皇明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戊中秋月二日立碑,又有祖师修行铭并序述寺僧胜中功行,亦万历十四年丙戊季秋月初三日竖碑。又载:《通志》在治北六十里,异石巉岩,苍翠欲滴。《道光志》华严寺同,又另列花岩寺,康熙六年建。按花岩即华严,旧志歧为二,误。可见,花岩寺建于康熙六年,而早在花岩寺之前的宋代,这里就建有广利禅寺,广利禅寺又毁于宋末元初的兵火。花岩寺的得名,应该由广利禅寺古迹而来。
当地老人说,他们儿时听老人讲,花岩寺的规模宏伟,有大雄宝殿、观音殿好几重大殿,特别是花岩寺前殿的四大金刚,气势磅礴,栩栩如生,而观音殿的汉白玉坐式观音,更是远近闻名。寺庙僧侣达数十人,香火旺盛。一千多年来,法雨山的寺庙历经了多次毁与建,兴与衰,并多次易名,花岩寺已经由原来的寺名演变为了地名。而花岩寺闻名遐尔,除了历史古迹和香火以外,还与她独特的风景有关。法雨山海拔虽然不算高,山形也并不雄伟,但法雨山却是这一带的分水岭。法雨山西南是绵延起伏的深丘龙泉山余脉,东北则是一望无涯的川东北浅丘陵。立于山顶,一面是群山巍峨,无边无际:一面则一览众山小,极目千里。特别是秋末春初时节的日出日落时分,景色蔚为壮观。山顶是晴空万里,山下是云海茫茫。一座座低山从云海中隐隐约约露出头来,宛如海中小岛。太阳从云海中缓缓升起,彩云翻腾,霞光四射。人在云上,犹如置身仙境。所以,在当时法雨山又有小峨眉之称。
青市,这个偏僻的小乡镇,一方面地处交通要塞,古时是罗江——中江,德阳——三台,广元——成都小道(近道)的三道交汇处,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在此歇脚,吃饭喝茶,有时稍晚还会在这里住店。因为,再往西南步行几公里便是高山,上山之后便是长达几十里深丘地带的山路。山高路陡,人烟稀少,树大林密。这一带山路上没村没店,在强人出没的古代,一般都不敢夜行山路。另一方面,花岩寺、东岳庙等几座庙宇香火的兴旺,庙会的隆重热闹,吸引了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还有就是法雨山的美景,更是让八方商人和游客慕名而来。人越来越多,山顶的花岩寺已是无力接待,于是,人们在青市场镇到花岩寺九华里的沿途修建了46座小庙,加上起点的东岳庙和终点的花岩寺,又称四十八重庙。供过往的客商信徒和上山看日出的人们过夜之用。达官贵人富商就住在山顶花岩寺,有吃有喝,看日出又少动脚步。普通百姓就住途中小庙,既节省开支,又能挡风御寒,第二天凌晨赶往山顶观看日出。
兴旺的香火,奇特的景观,人脉的聚集,凸显了商机,各行商贩纷至沓来。这就是为什么古代青市这个小场镇会如此繁荣的主要原因。民间传说如此之繁荣,在明朝末年被张献中的一把战火葬送得干干净净。是青市乡场的繁荣,促进了花岩寺的兴旺,还是花岩寺的兴旺,带动了青市乡场的繁荣?我想,这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吧。但是,青市乡场后来的衰败,除了历年的战火,花岩寺的毁坏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战乱的平息,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道的兴建和交通的发达,古时小道逐渐被淘汰,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今日的青市乡已非历史上的青市场可以比拟的了。乡场扩大了数倍,街道整齐划一,小洋房鳞次栉比,人民步入小康,并被赋予“万亩粮田小川西”之美誉,成为中江县的粮仓,同时也是中江县的劳务输出大乡,水稻制种、蚕桑和玫瑰香柑生产基地乡。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花岩寺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土墙青瓦的简易小庙,供有几尊工艺粗糙的石菩萨,并沿用花岩寺庙名。在花岩寺背后的山崖上,有一个几平米的石窟,壁上刻有数十尊彩色小佛像。由于年代久远的原故,多数佛像已剥蚀不清,只隐约可见:清乾隆什么什么字样。站在花岩寺的遗址上,想象着它当年的繁华,心中充满惆怅。
在花岩寺背后山顶,有一口约一亩左右的水塘,水色清澈,飘满白云。当地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相传法雨山顶原本是无水的,三国时候,蜀将张飞率部途经此山,时置盛夏,又长途行军,将士们口渴难耐,人困马乏。而山顶除了树木就是石头。张飞情急之下,拔出弓箭,对着山头连射三箭,便命一个士兵前去查看落箭之处有无水源。士兵跑回来报告,只见一个大坑,不见一滴水。张飞大叫一声,拔剑将士兵斩首,又命一个士兵前往查看。士兵回来报告还是不见一滴水,又被张飞杀死。张飞再派第三个士兵去查看。这个士兵亲眼目睹了前面两个人被杀,心想说实话是死,不如撒谎还能暂保性命。回来便谎报,有大股泉水涌出。张飞果然大悦,给予重赏。马上带着人马冲上山顶,只见三支箭射出一个大坑,箭还插在岩石中。张飞跑过去用力拔出箭杆,立刻就有三股泉水喷涌而出,一会就有了满满一塘清水。张飞的人马喝了个饱,只剩下半塘水。从此,这个山塘一年四季不涸不溢,始终保持半塘水。人们为它取名天池。
这个故事只是当地老百姓世代的口头传说。其实,有书为证这个故事与张飞无关,而是另有其人。据1930年版《中江县志》载:李广泉,《图书集成》在治北六十里,相传李广提兵至此,乏水,广望岩发矢,水随箭出。又载:法雨山,治北五十里,在太广山上,石崖有李广泉,下有马蹄河,山鹿有花岩寺,以古迹风景著。查阅相关文献,李广乃西汉文帝、景帝(公元前170余年)时期的名将,而张飞则为三国蜀汉(公元220余年)时期的名将,李广比张飞早近400年,这个故事的出入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并不重要,只要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就行了。对于民间传说,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与法雨山相连的一座山峰叫太观山。1930年版《中江县志》载:泰广山,亦名泰国山,治北五十里,高五里,广倍之,旧筑寨堡。太观山海拔690余米,为这一带的最高峰。当地人传说太观山就是《绵州巴歌》中的豆子山,其山顶酷似豆子,还筑有古寨。《绵州巴歌》: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关,撒白雨。白雨下,取龙女。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这首出自中江的玄武民歌,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先后被收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代诗歌选》等书籍,是中江的骄傲。多少年来,很多文人雅士一直在寻找豆子山,但读遍所有志书、文献和资料,都查无踪迹,一无所获。前两年,我写《绵州巴歌考辨》一文时,曾采访过太观山当地百姓,也曾登上太观山实地考察,并采纳了这一说法。今天青市人也称太观山就是豆子山,又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这一点。然而,却为何历代中江县志和文史资料没有记载呢?而《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代诗歌选》关于豆子山的注解也是似是而非?这不能不说是个千古之谜。花岩寺的兴衰和豆子山的真伪,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但我相信,花岩寺庙宇虽然不复存在了,她美丽的风景依然如故,她神秘的故事依旧动听,加上一脉相连的古老的《绵州巴歌》的发源地——豆子山的知名度,对于人们就更具有神秘感和吸引力了。这应该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如果政府将其列为旅游开发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合理打造,着力宣传,花岩寺一定会复活,《绵州巴歌》一定会复活,花岩寺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责任编辑/孙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