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熊:艺术要追求正大气象
李怀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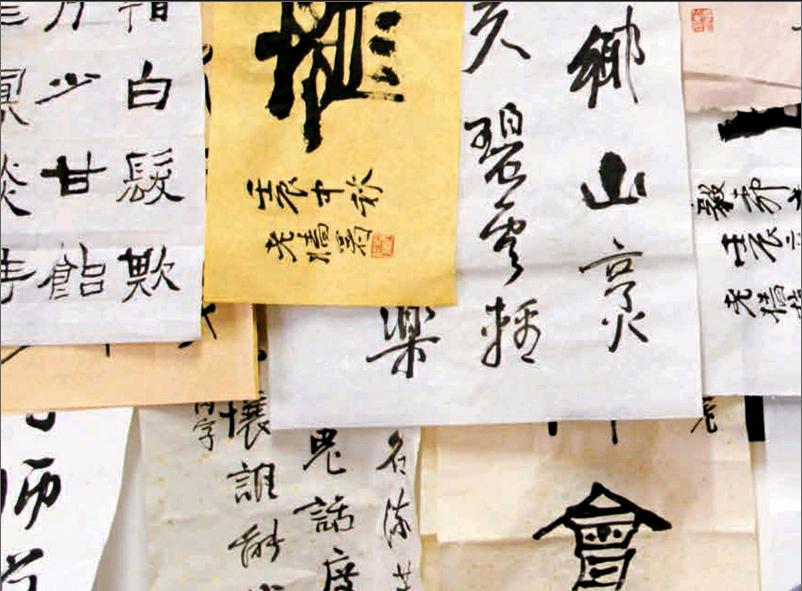

赵熊先生的书斋名为“风过耳堂”,每天刻印、写字、画画,偶尔写诗,与朋友唱和。他有和朋友诗云:“六十年来住旧京,红尘惯看变流行。短长浓淡真人秀,荣辱浮沉假道情。声色绵绵亡犬马,江河滚滚损雄英。云烟未绝群峰乱,但眺青山不问名。”
1949年2月1日,赵熊生于西安。祖籍绍兴,在道光年间,祖上考中进士到西安来当官,从此定居。赵熊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总是鼓励儿子多去读书。赵熊喜欢书画,后来大伯带他拜陈少默为师学习书法篆刻。
少时个性比较内向,赵熊常常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拿块石头刻刻印章,随便画一画,家里人都说这个小孩在做正经事,不去打扰他。赵熊说:“书法如果有童子功当然最好。按我的理解,对当代人要讲童子功,好像说天书一样。因为现代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用毛笔书写,而是一个硬笔时代甚至就是—个键盘时代,连硬笔都不愿意写。但是,学书法相对来讲越早越好,因为早一点的时候就相当于一张白纸,按照正式的法度,落的毛病比较少,上正路比较快。年纪越大,积习越深,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书写习惯,再要进入传统的技法层面上学习,两者经常要互相拧劲。从这一点讲,童子功恐怕有意义。”
赵熊读初中时,新来一位班主任,主张学生每个星期写上几张毛笔字,当作业一样。这正好和赵熊当时的心态切合在一起,他开始比较自觉地临习字帖,投入情感。1965年初中毕业,赵熊报考西安美院附中,专业课通过了,到最后综合审查却没有通过,上面没有任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赵熊应要求写大字报、画漫画。他回忆:“我们当时就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用篆刻的形式,刻点毛主席诗词,刻点豪言壮语,全都放到批判专栏上去。在陕西,“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倒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些艺术传统。”
赵熊在小节上比较随便,大节没考验过。从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初中,操行评语上经常是“不拘小节”。“文革”时兴“忠字画”,画家向毛主席献忠心,赵熊说:“对毛主席忠,要真正地忠在心里。”这种性格使他在一些事情上受过挫折,反倒刺激了他,使他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喜欢的书法篆刻上,远离政治。“文革”爆发不久,朋友送他一本《道德经》,他读了,感觉很能安抚自己的心灵。他曾在一把扇子上写了四个字:“居地心渊”,这是老子的话:“居善地,心善渊。”有一位原来的小学校长看了以后很吃惊,问他:“你敢写这个东西,你真能做到这样?”
赵熊学篆刻比书法稍晚,因为当年字帖比较好找,印谱比较难找。他从学习秦汉印开始,这可能也和性格有关系,他说:“秦汉印是正大气象。学术界认为秦汉印是中国印章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以前将古玺印排除在外,认为还不够成熟。实际上,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秦汉印以前的古玺印里也有很多好作品,是另一种气象,另一个高度。”
赵熊的印艺独具一格,他是西安印坛最有影响的终南印社社长,却与时风不太同流:“因为我不太和官场联系,和企业家联系也不太多。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缺点,所以这个印社的发展现在也有很多困惑。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文人雅事,好像也不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如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人文的精神和风骨可能要受点影响。但是不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客观上肯定影响这个社团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可能不够。”
赵熊曾写过《砚边有思》:“濡朱染墨此生残,换取霜丝意坦然。成败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贬是因缘。”他觉得在“风过耳堂”最好的状态是没人敲门,没有电话,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他笑道:“如果中央台来采访我,问我幸福不幸福,我肯定要说幸福。我比较容易满足,也没有什么大志,所以感觉还是很幸福。”
《收藏·拍卖》:你最初喜欢印章是什么样的因缘?
赵熊:和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因为家里有我祖父留的石头,他是想刻来着,还没来得及刻,有请别人刻的印章。他还买了一套刻刀,后来我们这些小弟兄都玩。刻得不好用砂纸沙沙沙磨了以后又可以从头来,这也和十多岁的心智有关系。刻刀再往深里刻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印章里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按照秦汉印就是寸印,基本上就是二到三公分。在一方很有限的尺寸里命题。因为刻的是人的名字,我不能给人家改名字,所以这个命题有限制,就像一个人在社会中一样,不是纯自由的,要受到人生、生活和社会的种种限制。在这个限制当中还要使自己相对自由,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彩,实际上这和印章一模一样。加上字与字之间要互相调配,讲究和谐,但是在和谐的前提下怎么样去生成很多的变化,这不是和人生完全是一回事嘛?现在来讲相对自由一点,像过去我们那个时代不自由,找个工作分配到啥地方就是啥地方。这就跟刻印章一样,就给你这么一块石头,软也好硬也好,你都得刻。如果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篆刻称不上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依靠的是汉字,而文字是工具。换句话说,这个艺术形式离不开工具性的制约,就不可能纯粹自由,就是戴着脚镣手铐在跳舞。它不像绘画,绘画里面有写意画,没人去数你这朵花是多一瓣还是少一瓣,没有人去注意你这片叶子是长了还是短了。但书法不行,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这个东西做好。
《收藏·拍卖》:你从学秦汉印入手,后来有没有专门学过哪几家?
赵熊:说起来是学秦汉印,主要还是学汉印。因为当时秦印传世得少,出土得少。最近二三十年,秦印出土比较多,看得比较多。秦印和汉印之间肯定有关系,但是秦印比汉印要活泼。西安是秦汉印的故乡,这毫无疑问。从秦汉印以后,印章逐渐在走下坡路。一直到元明,有文人印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按我理解这是一种人文觉醒,它和过去工匠制印是两回事。秦汉印是防伪辨奸的,是权力的象征。文人印更多的是闲文印,实际上和艺术相关。它有实用性,但更多是文人搞点艺术。文人印的大本营在江南,所以秦汉印以后一千年,如果以篆刻来说,在陕西是一片空白。后来像北方的齐白石,南方的吴昌硕这些大家,西安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学习篆刻的时候也很彷徨,没有大家,就没有老师。但是有一个好处,老师是一座高峰,但有时候也是一座围墙,要辩证地看待。我们学篆刻有陈少默先生的指导,陈先生是人品最好,学问最好,接着下来是书法、鉴定、诗歌,但是他写的诗歌也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收集到的诗也不过120多首。陈先生50多岁开始学篆刻,他有一方印:“少默年五十始好金石”,可以为自己做证。事实上,我们考证,他在此之前也刻过,可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从50岁到70岁左右,大概前后有二十年,他才投入到治印。我从1971年跟陈先生学,要说刻印我可能比我老师学得还早,我是从1962年、1963年开始刻,但是他开始治印以后,和我们当时懵懵懂懂的小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
《收藏·拍卖》:你早年如何学书法?
赵熊:我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书法是汉隶,就是隶书。我也写过唐楷,像颜真卿,写后我就感觉有点法度森严,好像不太符合我的性情。隶书相较于楷书,给人感觉好像变化多一点,而且比楷书多一点古意。实际上,汉印的许多文字和隶书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可能对我也有影响。后来还学过一段时间北魏,因为北魏的书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带有很多民间书风的,所以形态上要别致一些,险一点,庙堂之气不是那么重。行书上,我还是喜欢颜真卿一路的,我过去不太喜欢二王的东西,40多岁以后,觉得需要关注二王,学习二王。从书法流传的发展史来讲,王羲之是做得最好的,之后的米芾、王铎,在行书方面写得也很好。
《收藏·拍卖》:有一位先生告诉我说行书是最见功夫的。
赵熊:应该说行书最见性情,每个人写出来的行书都有自己的风格。过去楷书最实用,但在今天书法创作中,行书应用最为广泛,而草书则最能代表书法高度。
《收藏·拍卖》: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现代,因为像钢笔、圆珠笔、铅笔等新的书写方式普及之后,毛笔渐渐退出生活了,毛笔书法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会不会影响书法技艺的发展?
赵熊:从目前来看,好像还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日本反倒是经济特别发达的时候,保存了大量的手工艺作坊,给好多人提供了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机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吃饱喝足,生活无忧的情况下。这时候反倒有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比搞群众运动的效果还要好。时代的进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中间有一种经验可以借鉴:于右任先生创造了标准草书,我认为这是两个时代的误会。最初的误会是于右任先生做标准草书的背景,实际上是响应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正好于先生对书法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从书写角度和新生活运动相呼应。当然他本身也很喜爱书法,深入钻研,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于先生没有想到的就是硬笔逐渐地代替了软笔,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于先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把文字怎么样写都有书法意味,但是他把文字简单地符号化了以后,一般没有书法功力、没有书法感悟的人写出来的是啥东西?但是,从普及的角度是为了惜时省力,要改掉国民的陋习,提高生活的效率和质量。于先生百年以后,好多人又要把这个标准草书作为书法艺术来推荐,这是不是很奇怪?艺术何能标准,标准哪有艺术。弄了个标准草书,然后给它冠上艺术的名号,这肯定是限制艺术的。从社会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来看,对书法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现在要求五六岁就必须要拿着毛笔去写字,并且一直生活化地坚持下去,恐怕是不现实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会使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更集中、更精良地去做这件事情。
《收藏·拍卖》: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可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了。于右任先生是陕西人,书法中有苍茫之气,他对陕西的书法有没有影响?
赵熊: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我感觉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比较大。对具体的技法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大家并不是趋之若鹜地都去学于右任的标准草书。
《收藏·拍卖》:于右任的书法气象也很难学的。我在嵩山看过于右任的一幅书法“天地正气”,写得好极了。
赵熊:我自己的感受是,学习书法,学习篆刻,学习美术,你模拟学习的对象的风格如果太明显反倒是坏事,你学进去以后,出不来。举例来说,我比较反对喜欢书法的年轻朋友一上手就学柳公权。从历史上看,学柳公权以后出来的也没几个人,这是客观事实。不是柳公权的字写得不好,他是写得好,问题是他把字写到极致了,没有留下空间,你完全变成柳公权又不可能。从宋代到现代,总有人说颜真卿的字看起来有缺点,但是他的书法非常大气,他留有空间,你进去之后还有可以挪身的地方,出来的余地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学颜真卿出来的人就多。
《收藏·拍卖》:于右任与沈尹默的书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沈尹默是典型的江南气韵,有温润的书生气,写得规规矩矩,书法是不是有地域的特性?
赵熊:过去一直有南人北人之说,也有南派北派之说。绘画上有这种说法,书法上也有这种说法。特别是自从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后,崇尚碑学,所以对陕西的影响大,对南方肯定也有影响,但是对北方的影响比较大。最近我们在整理民国时期陕西的一些老前辈的书法作品和艺术经历时,发现他们的书风真的有趋同之处,都是有写北魏的经历,好多面目出来之后都带有北魏的特征,当然这跟包、康的倡导有关系,也可能跟人的地域性的性格有关系。陕西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玩,我认为陕西是王道教化最早的一个地方,从周代下来十几个朝代,王道教化比较早,所以长期的民风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当然,过去说“南人北相”,比如吴昌硕先生像个老太太,个子也不太大,写出来的字,刻出来的印,很有金石味道,真是能力拨千斤。所以,不能想象从这么一个瘦老头的手腕底下,能出来这样的东西。当代,我也挺喜欢江南沙孟海的书法,包括他的印章。还有,像启功先生胖胖的,写出来的书法却瘦瘦的。
《收藏·拍卖》:从西安来讲,有碑林这样的地方,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
赵熊:有,我们从小就去碑林,碑林那时又不收门票,随便进去就玩,玩得高兴就爬到石碑上蒙上一张纸,用铅笔唰唰唰擦摹下来,拿回去玩。看哪几个字好看可能回去专门照哪几个字去写,我这一代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学习过程,后来碑林收门票,进去不太方便了,这个学习过程就没了。不过,在我们心中,碑林一直是书法的圣殿。
《收藏·拍卖》:近代的印家里面,你觉得谁比较有特点?
赵熊:近代的印家里边有特点的很多,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吴昌硕,他对篆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技法是最丰富的。书法和篆刻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现象。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要倡导的主旋律首先应该是光明正大。正大气象,不排除花前月下,不排除小桥流水,但是正大光明符合生命生长的基本规律,如果大家整天都沉浸在小情调中,对生命是不能起到更正面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吴昌硕的东西是光明正大,于右任先生也是如此。
《收藏·拍卖》:以江南来说,像陈巨来、方介堪的印,你如何评价?
赵熊:方介堪是王福庵先生的学生。从艺术形态上说,王福庵和陈巨来达到了一个高度。精工印风雅致清蕴,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在社会上有着极强的生存空间,今天仍旧如此。比如篆刻中的藏书印是很儒雅的,而且书籍上面能容许你盖印章的地方也不是太多,就很适合精工印的应用。虽然我自己刻写意印比较多,但是碰到给朋友刻藏书印的时候,我还是尽量平和一点。
《收藏·拍卖》:印章渐渐地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
赵熊:拿书、画、印三个门类相比较,篆刻肯定是属于一种小众艺术。造成小众艺术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是篆书的问题,因为什么文字都能拿来刻印,但是主流还是篆书。篆书从识读上来讲是一个障碍,好多人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去认篆书。篆书在印章里还要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难度。第二个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篆刻不如书法那么方便,投入也比较大,做起来也比较辛苦。所以我现在非常忧虑喜欢篆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可以学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功利思想都比较明确,年轻人把大量的精力、时间、钱财投进去,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回报。即便有回报,这个投入期也是很长的,这很影响篆刻艺术的发展。不过话说回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多年来篆刻的进步,真的要大于书法和绘画的进步。
《收藏·拍卖》:为什么会这样?
赵熊:主要是现在有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发现。比方讲,许慎在编《说文解字》的时候,他没见过甲骨文。中国人到清朝年间才接触到甲骨文,所以以前很少有人用甲骨文去入印的。到了近代,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文字大量地出土,给书法和篆刻的学习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收藏·拍卖》:印章的用石,有什么讲究?
赵熊:从我自己的习惯,和纯篆刻的角度来讲,对浙江的青田石感觉最好。青田石就好像宣纸里的红星宣纸一样。当然,所谓青田石是一个宽泛的说法,青田石也有好坏。从比较高的品质上来说,青田石对刻刀的运动的表现是最到位、最可心的,是最好的。石头的特点无非就是软硬粗细,太软了不受刀,线条不太容易塑造;硬了,用刀非常吃力,也不好塑造。青田石正好在中间,是不煤不腻,不硬不软。所以,大家过去都最喜欢用青田石,但现在好石料越开越少。而且真正的好石料开出来以后价格越来越贵,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收藏·拍卖》:你觉得写诗词,对自己的书法和印章的修养,有没有好处?
赵熊:绝对有好处。如果把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上是把书法“矮化”掉了,把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抽掉了。大家整天都是写“朝辞白帝彩云间”、“月落乌啼霜满天”,如果不写自己的东西,说明这个人没有文心,或者没有诗心。前人把“诗书画印”这么一排列,表面上看好像只是顺口,实际上也是很有道理的。诗肯定是第一,因为有文心诗心,才能牵扯到具体的艺术层面上来,然后才能讲绘画、书法、篆刻的问题。诗书画印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我退休以后时间比较充裕一点,所以就想在这方面综合性地补一补。散文也在写。有时候就是介乎散文和杂文之间的文章,也写一写。
《收藏·拍卖》:大变革的时代,艺术的发展有时候会有一种突变性,像诗书画印的传统在新的时代,会不会也有一些新的突破?
赵熊:这个比较难,现在这个社会的总体运行态势是快,而中国传统很多东西恰恰是慢。我有一个朋友说,在一个人生命里,很短的时间段,很有限的经历,把一件事情做到顶端去,在前人的基础上还想至少伸长那么一公分,都是很不容易。这种状态是不符合现在社会运行的速度的。再加上更年轻的人,有工作的问题,房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上边有父母,年纪老了还有养老的问题,实际上压力非常大的。身和心能够进入一个都比较自由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也都到六十岁上下了。在这种社会环境状态下,将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作为一种方向,对于他们来讲实际上还是比较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