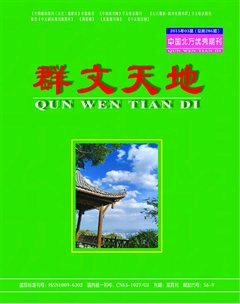不断淬炼的精神升阶书
核心提示: 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象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心灵史和生活史。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具有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但似乎有很多专业研究者对他以及他多年来的长诗写作缺乏必备的了解。
翼人的长诗写作在张扬出个体对自我、世界、生存、诗歌、历史、民族、宗教的经验和想象性认知的同时,也以介入和知冷知热的方式呈现出工业和城市化语境之下传统的飘忽与现实的艰难,尤其是急速前进的时代之下驳杂甚至荒芜的人性与灵魂。翼人多年来的长诗践行更像是一个个人化、历史化、生命化和寓言化的精神文本和一个诗人的灵魂升阶之书。
长诗无疑属于更有难度的诗歌写作类型,而中国又是自古至今都缺乏长诗(史诗)写作的传统。自海子之后中国诗人的史诗情结多少显得荒凉、青黄不接,而写作长诗甚至“史诗”一直是从“今天”诗派、第三代诗歌以及上世纪90年代诗歌以来当代汉语诗歌噬心的主题,甚至在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因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挑战,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语言、智性、想象力、感受力、选择力、判断力甚至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和全面的考验。在笔者看来“长诗”显然是一个中性的词,而对中国当代诗坛谈论“史诗”一词我觉得尚嫌草率,甚至包括海子在内的长诗写作,“史诗”无疑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多元化的书写和命名,而这是对诗人甚至时代的极其严格甚至残酷的筛选的过程。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会产生重要的长诗,但是“史诗”的完成还需要时日甚至契机。在笔者看来“大诗”正是介于“长诗”和“史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说到当代的“长诗”不能不提到几位重要的诗人,洛夫、海子、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廖亦武、梁平、于坚、阿尔丁夫·翼人(下文称翼人)、大解、李岱松以及江非等更为年轻的诗人。我从不敢轻易将当代诗人包括海子的长诗看作是史诗,我们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史诗,我更愿意使用中性的词“大诗”。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现实感的信仰式的诗歌写作成了缺席的显豁事实。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翼人的长诗写作具有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但似乎有很多专业研究者对他以及他多年来的长诗写作缺乏必备的了解。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翼人大量的长诗写作,如《沉船》《神秘的光环》《错开的花 装饰你无眠的星辰》以及《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我的青铜塑像》《母语:孤独的悠长和她清晰的身影》《光影:金鸡的肉冠》《放浪之歌》《古栈道上的魂》《西部:我的绿色庄园》《撒拉尔:情系黑色的河流》《蜃景:题在历史的悬崖上》《遥望:盛秋的麦穗》等都秉承了一以贯之的对宗教、语言、传统、民族、人性、时间、生命以及时代的神秘而伟大元素的纯粹的致敬和对话,这种致敬和对话方式在当下暧昧而又强横的后工业时代无疑是重要的也是令人敬畏的,“子不予怪力乱神/——撒拉尔/在这前定的道上/壮行 独美八百年/而这道啊!注定/以尕勒莽阿合莽的名义/铸造黄金般的誓言/灵魂像风 奔跑在美的光影里”(《灵魂像风 奔跑在美的光影里》)。翼人的这种带有明显的民族和诗歌的双重“记忆”的不乏玄学思考的诗歌写作方式和征候不能不让我们联系到海子当年的长诗写作。但是海子的长诗在最大的程度上祛除了个人的现世关怀和俗世经验,这就使海子的长诗拒绝了和其他个体的对话和交流,并也最终导致了在无限向上的高蹈中的眩晕和分裂。而可贵的是翼人多年以来的长诗写作是同时在宗教、哲理、玄学、文化和生命、当下、时代和生存的两条血脉上同时完成的,这就避免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单一和耽溺,从而更具有打开和容留的开放性质的和更为宽广深邃的诗学空间。撒拉尔、清真寺、骆驼泉、先民陵墓、古兰经以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合部、黄河之畔的循化都成为诗人永远无眠的星辰和恒久的诗歌记忆,“我刚刚从两莽的墓地归来/两膝的黄土翻滚着/历史的烟云在我眼前纷飞/我斗胆以卑微的思想/想象上千年两河流域的文明/和两莽直逼中西文化的巨人的光芒”(《错开的花 装饰你无眠的星辰》)。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红色政治年代过渡到商业化、娱乐化、物欲化、传媒化的后工业时代,剧烈的时代震荡和社会转变,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和灵魂信仰的缺失都如此强烈地淤积在翼人以及同代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一些更为强烈的倾诉和抗议的愿望已不可能在短诗中无以完成和淋漓尽致地呈现,只能是在长诗写作中才能逐渐完成一代人的倾诉、对话、命名和历史的焦虑,磅礴大气和温柔敦厚并存的诗歌方式成就了翼人长诗的个性。概而言之我们看到包括翼人在内的一些诗人写作长诗的努力印证了中国当代诗人写作优秀长诗的可能性,尽管其面对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这种可能性只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来完成的,历史总是残酷的。在巨大的减法规则中,掩埋和遗忘成了历史对待我们的态度,而语言和诗歌永远比一个国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诗人用语言创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终会在历史中停留、铭记,历史在寻找这个幸运者,这个幸运者肯定也是一个在个人和时代的轨道上发现疼痛和寒冷的旅人。作为6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翼人的个性和诗歌写作中具有强烈的文化寻根(同时具备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和民族叙事的抒写冲动。作为一个撒拉尔族人,翼人很容易被看作少数民族诗人,因为身处青海又更易于被贴上“西部诗人”、“边地诗人”的标签。当然无论是将翼人看作少数民族诗人还是西部诗人,这都无可厚非,甚至这种民族根性和西部的文化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翼人的诗歌写作个性,尤其是他的长诗写作谱系。但是我更愿意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看待翼人的身份和长诗的个性,因为他的长诗写作在当下的时代具有明显的诗学启示录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翼人的长诗写作就是毫无缺点和无懈可击,而是说他多年来的长诗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长诗的写作传统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而言确实具有需要我们重新认知的埋藏着丰富矿石的地带。翼人的长诗写作呈现的是既带有神秘的玄学又带有强烈的与现实的血肉关系的质地,无论是与诗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往事记忆、生活细节还是想象和经验中的更为驳杂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宗教性的场景、事件,这一切都在融合与勘问中呈现出当下诗人少有的整体感知、历史意识、人文情怀和宗教信仰。翼人的长诗写作在张扬出个体对自我、世界、生存、诗歌、历史、民族、宗教的经验和想象性认知的同时,也以介入和知冷知热的方式呈现出工业和城市化语境之下传统的飘忽与现实的艰难,尤其是急速前进的时代之下驳杂甚至荒芜的人性与灵魂。翼人多年来的长诗践行更像是一个个人化、历史化、生命化和寓言化的精神文本和一个诗人的灵魂升阶之书。
而1990年代以来,一些诗人普遍放弃了集体或个人的乌托邦“仪式”而加入到了对日常经验和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当我们普遍注意到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的呈现时,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诗歌的“个人化”(私人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和相应的诗歌写作语境的巨大转换,诗歌写作对以往时间神话、乌托邦幻想以及“伪抒情”、“伪乡土写作”的反拨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反拨的后果是产生了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即对“日常经验”的崇拜。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一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基于此,翼人不能不在诗歌写作中形成这样的体认,即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应该迫使自己的写作速度慢下来并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对现实与历史的强大的穿透力和反观能力,从而最终达到与生存与时代相契合的精准而真实的联系和见证意义,“或许我们本不该再次久留/本不该扶你送上祭坛/周围的一切都在蒙昧的花园里/投去鄙视的目光扼杀或挫败/无与伦比的梦幻在世界的中心旋转”(《神秘的光环》)。对于在诗路跋涉、探询、挖掘的翼人而言,在黑夜的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揭开诗歌漂流瓶,在物欲、金钱、权利和疯狂幻象围拢、挤迫的黑暗中沉潜下来,倾听来自语言、民族、宗教以及遥远而本真的灵魂独语或对话的神秘召唤是一种不能放弃的责任与担当情怀。这一切无疑是良知的体现,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从“诗”的造字含义上就含有记忆和“怀抱”以及宗教的精神维度。正是在此意义上翼人的长诗写作真正回到了诗歌的源头。他制造的诗歌漂流瓶盛满了集体的记忆积淀,而那明灭闪烁的火光中本真的宁静与自足闪现就是必须的,是倾尽一生之力追问和挖掘的高贵姿态。巴什拉尔说“哪里有烛火,哪里就有回忆”,是的哪里有倾听,哪里就有回忆。基于此,翼人在“深入当代”与“深入灵魂”的噬心主题的独标真知的吁求中彰显出执著的诗学禀赋和富有良知的个性立场,以诗歌语言、想象力和独创的手艺承担了历史和人性的记忆。翼人的长诗中持续不断的是诗人对天空、河流、土地、山脉、彼岸和精神乌托邦世界(当然也是个人化的)的长久浩叹与追问,这种源自于诗人身份和民族记忆的对诗意的精神故乡的追寻几已成为他诗歌写作的一种显豁的思想特征甚至征候。对于优秀的诗人而言,在后工业时代语境之下坚持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探询和诘问是最为值得尊重的一个维度,我是在整体性上来谈论翼人与理想主义、农耕文明、宗教情怀之间的尴尬和挽留关系的。翼人自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确实蕴含了一种独具个性而又相当重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深入现实的精神向度。这种个人的历史想象力较之1980年代以来的带有青春期写作症候的美学想象力而言更具有一种深度和包容力。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翼人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写作,有力地在历史想象力的启示下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和一代人的诗歌史、心灵史、生活史。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历史想象力在一代诗人身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展现与深入,清醒与困惑的反复纠缠,自我与外物的对称或对抗。
翼人的诗句有如长长的沉重的铁链顽健地拒绝锈蚀的机会,那抖动的铮铮之声在午夜暧昧而强大的背景中呈现为十字架般的亘古的凛冽和苍凉:
哦,沉默的土地啊
那是从遥远的马背上启程的儿子
亘古未曾破译这现实时间的概念
或有更多的来者注视:存在的背后
所蕴含的哲理被轻柔的面纱遮去
或是老远望去河岸的大片风景
在绚丽的阳光照耀下步步陷入深渊
——《沉船》
这些容留的力量、张力的冲突及其携带巨大心理能量和信仰膂力的诗句,在当下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是相当罕见的。这也只能说明在历史与当下共同构筑的生存迷宫和怪圈中,特殊的生存方式、想象方式和写作方式造就了一个张扬个性、凸现繁复镜像和无限文化与传统“乡愁”的诗人翼人,“在你面前我曾是一名无望的患者/使我重新确认物体的表面所蕴含的重量/远远超过草木细微的影子/或许这仅仅是传说或许我们早跟自己的影子相逢/且在光明的路上拖着尾巴/穿过大街小巷或那无尽的回忆/并把所有的梦想化为石头的训语/镌刻灵魂缄默的花树”(《神秘的光环》)。在一个信仰中断和放逐理想的年代,在一个钢铁履带碾压良知和真理的粉末状的年代,一个跋涉在精神之路上的歌手,一个不断叩问的骑手在工业的山河中与风车大战。因此,翼人的诗歌更为有力地呈现了时间的虚无和力量,换言之在具体的细节擦亮和情感的呈示中翼人的长诗更多显现的是诗人对时间和生存本身的忧虑和尴尬,在茫茫的时间暗夜这短暂的生命灯盏注定会熄灭,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干枯的记忆中最终模糊,“唯有你们/早晚在崇高诗篇的颂声中/平安度日再度忙碌/也不忘时刻的准点/严守时间的秘密/把最神圣的交换托付”(《错开的花装饰你无眠的星辰》)。有人说谁校对时间谁就会老去,但是翼人却在苍茫的时间河流上最终发现了时间的奥义和神秘的诗篇。
所以多年来翼人的长诗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语言方式、抒写特征还是想象空间上,它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无以言说的敬畏和探询的态度,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诗歌写作的源头。这无疑使全诗在共有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生存整体共有的精神象征的词句不时出现在长诗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向传统、语言、诗歌的致敬和持守意味,“相信或怀疑注有标记的旗杆上走动的人群/在我的耳旁号叫、嘶鸣/但我依然守候着他们/当他们远离亲人时/吹送柔柔的清风”(《沉船》)。
(作者简介:霍俊明(1975-),中国当代著名青年诗人、批评家、学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一个人的和声》《中国诗歌通史》等,主编《百年新诗大典》《诗坛的引渡者》《新诗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