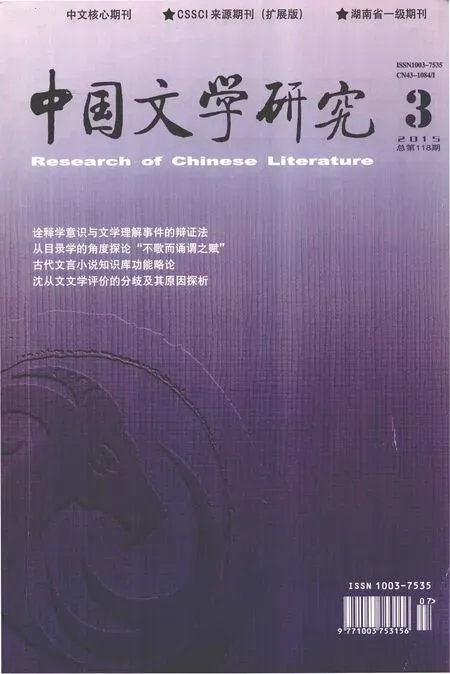论邓以蛰艺术美学的形意之辨
孙宗美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学术史研究的一大典型思路和做法,就是从宏观角度把握学者的思想体系和学术特点。对邓以蛰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学术个案,邓以蛰及其书画美学思想在近十余年来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面对为数不多的邓以蛰论著,研究者们力图在其中寻绎其美学思想体系和特征,甚至努力尝试为之命名。他们不仅注意到他融通中西的美学研究方法,指出他立足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发展的史论结合性研究特点,还注意到他对艺术创造和审美的主体性的突出与强调。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邓以蛰美学与艺术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那么,在上述观点之外,还能发现邓以蛰美学的其他特点吗?
邓以蛰美学以对中国传统书法、绘画两大视觉性艺术的研究为主。这两种艺术类型都以“形”为主,但又倾向于主体内在之精神表现,因此自古以来在书画领域就有“形意之辨”的话题存在。“形”与“意”这对立而统一的二元既是中国传统书画理论展开的进路,也是邓以蛰美学体系隐含的宏观理论架构:他不仅从“形”、“意”关系的角度出发区分西画与中画、北宗与南宗,而且更进一步建构了以“心画”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在邓以蛰美学中,“形意之辨”实有三重涵义:其一是形式、形质或形象与意境的关系问题,其二是艺术史上从“形”到“意”的发展趋势;其三则是“重形”与“重意”的问题。第一重涵义主要针对书画艺术“意境”的阐释而言,而与此相应,邓以蛰对中国传统书画美学的分析研究几乎都是从形、意两端分别展开的,这无疑使得他的美学体系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角度呈现出清晰的理论架构。第二重涵义则与邓以蛰对书画艺术发展史的梳理审视有关,其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重涵义实与第一重相呼应,即在诗与画、南宗与北宗、中画与西画比较等方面表现出或形或意的偏重。总体上讲,重意轻形不仅是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史和相关理论准确把握的结果,也是他构建以“心画”为核心的艺术美学思想体系的必然指向。追根溯源,来自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克罗齐等人有关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论及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形意观在邓以蛰的美学世界中相互碰撞交融,结出了硕果。
一、“形式”与“意境”
从王国维到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对“意境”的标举几乎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共同倾向。与其他学者集中对“意境”进行本体阐释不同,邓以蛰别出手眼地从“形”与“意”(也即形式和内容关系)的角度出发来阐释“意境”。邓以蛰认定“形”的重要,无“形”就不能成其为字与画,更重要的是“形”是意境表现的前提,没有“形”就没有“意境”。他说:
若言书法,则形式与意境又不可分。何者?书无形自不能成字,无意则不能成书法。字如纯为言语之符号,其目的止于实用,固粗具形式即可;若云书法,则必于形式之外尚具有美之成分然后可。如篆隶既曰形式美之书体,则于形式之外已有美之成分,此美盖即所谓意境矣。
意境亦必托形式以显。意境美之书体至草书而极;然草书若无篆笔之筋骨,八分之波势,飞白之轻散,真书之八法,诸种已成之形式导于前,则不能使之达于运转自如,变化无方之境界,亦无疑也。故曰,形式与意境,自书法言之,乃不能分开也。
画者形也。非摹拟外物之形似,但为绘画者心中之意境以形象也。
可见,“意境”与“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意境”虽要通过“形”而获得表现,但它却不受“形”的束缚,“形”完全以“意境”的表现为转移。这是因为“粗具形式”并非艺术的极诣,而“意境”的追求才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必然趋势和最高境界。邓以蛰认为,“意境”是成就美的关键所在,所以才说“必于形式之外尚具有美之成分然后可”。此处,“意境”就是艺术表现的内容。他从内容(“意境”)与形式关系的角度来解析“意境”,并将形与意之“意”阐释为“意境”,不仅充分尊重了书画等视觉艺术的基本特点,而且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邓以蛰对形式与意境关系的看法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中“理念”就是艺术的内容,而“显现”说明艺术要通过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作为绝对精神和“真实”的“理念”。黑格尔的定义不仅肯定了艺术是感性与理性契合无间的统一体,而且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他说:
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
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二分的观点,并且明确了形式对内容(意蕴)的指引作用。他同时强调,内容的决定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艺术作品的表现愈优美,它的内容和思想也就具有愈深刻的内在真实。”这与邓以蛰对形式与意境关系的阐释几乎完全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在邓以蛰的书画艺术视野中,“形”的所指内涵是多元丰富的。就书法而言,“形”有“形质”、“形式”、“形象”三层含义;而于绘画而言,“形”则主要指“形象”。邓以蛰在言及书法艺术中“形式”与意境关系的同时,也说明了“形式”与“形质”的关系。他认为:“意境究出于形式之后,非先有字之形质,书法不能产生也。故谈书法,当自形质始。”可见,“形质”是书法“形式”的重要构成与前提。书法的形质有三——“笔画”、“结体”(“体势”)、“章法”(“行次”),正是这些“形质”要素共同构成了书法的“形式”概念。而由“形质”要素组成的“形式”又是构成书法艺术“形象”的前提。刘纲纪在分析评价邓以蛰这一书法美学思想的时候指出:“那种认为书法是无形象的艺术的说法是不对的。书法艺术当然没有绘画中那种直接描绘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但它有诉诸视觉的、能唤起美感的形象。一切美的艺术都是形象的。美学上所谓的‘形象’,是在广泛意义上,相对于不可知的抽象概念来说的,决非仅仅指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这一分析说明是颇有见地的,不仅补充和丰富了邓以蛰书法美学中有关“形”的认识和看法,更从某种意义上完善和回应了邓以蛰有关形式与意境不可分的理论见解。相对于书法之“形”的内涵丰富性,绘画之“形”要单纯得多,仅有“形象”之意。邓以蛰认为,“形”为画之基础,人物山水画都必须托形以存在,但中国绘画又以无形迹之“气韵”为最高追求,故又引出了形似与气韵的关系问题。由此,根据邓以蛰对书画艺术之“形”“意”的关系探讨,可以得出以下图表(见表1):

表1
以上是从宏观层面就意境与形式的关系而言,而单就字的形质也即书法的形质来看,则形式(“形”)与内容(“意”)二分的视角依然在发挥作用。邓以蛰书法形质要素之“笔画”和“章法”的阐释都采用了剥除形式外壳进探内在精神的做法。关于书法之“笔画”,他认为:“今书法之笔画,乃为人运用笔之一物以画出之笔迹也;笔之外,尚有指、腕,心则皆属诸人;是以,此种笔画不仅有一形迹而已。古人论书法者类皆言形之外,尚有其实质。实质为何?曰骨,曰肉,曰筋。骨肉与筋之说,始于魏晋间,后遂未有废之者。”“笔迹”是笔画之形迹,其内在实质则是骨、肉、筋。这种观点既吸收了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理论的思想,又受到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的影响。因为他进一步说:
骨与筋可谓笔画之实质矣。但欲达到骨与筋之境地,则为表现之事也。骨与筋者,自其本体言,本已为笔法上之表现而非形式,观‘骨取指实’,‘筋取腕悬’诸说可知也,盖言非指能实不能表现骨之能事,非腕能悬不能表现筋之能事也。然骨与筋为笔画成立之根本,无此二者则无所谓笔画,亦无所谓书法也;故称之为笔画之实质,无不宜也。由此实质,然后书法乃可开始。……书法者,人之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
书法之笔画,非一画之痕迹,而为人之指、腕与心运用之笔墨之事以流出之美,所谓表现是也。
邓以蛰反复强调书法“为人之指、腕与心运用之笔墨之事以流出之美”,这一方面是他透过书法之形式进探内容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他重视艺术内在之精神的倾向——所以他说“骨与筋为笔画之基础”,为他建立以“心画”为核心的艺术美学体系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其后,他在阐释书之章法的时候同样使用了类似的视野和方法。他说:
书之章法,肇于自然。所谓自然者亦指贯于通篇行次间之血脉气势也。以血脉气势为章法之自然,此自然之又一面——内之一面也。前段所论,乃外之一面也。外之一面为章法之形式,故就字体及其形势两点观之,足矣。若内之一面,无形质者也;换言之,即精神也,活动也。精神,活动,言之者诚难,而听之者邈邈也。以其难言,益得根据血脉气势诸说以言;过此则更深入意境之域,而为书意篇之问题矣。
邓以蛰认为,血脉气势(也即精神)为书之章法的内之一面,外之一面为形式。这内之一面的又不外乎“势、笔墨、气韵”三事。“气韵为书画之至高境,美感之极诣也。凡有形迹可求之书法,至气韵而极焉。复为一切意境之源泉,其于意境实犹曲之于佳酿焉。”通观《书法之欣赏》之《书法》一节,可以发现:在形意二分的视角下,邓以蛰对书法艺术层层剖析,其逻辑思路呈现以下图示(见图1):

图1
气韵是意境的源泉,是一切有形之艺术的最高追求,也是艺术美的所在。
亚里斯多德将美的艺术称之为“摹仿”或“摹仿的艺术”。他认为诗歌、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摹仿的不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也即内在本质和规律)。对此,邓以蛰曾在《南北宗论纲》中说:“亚里士多德与艺术之定理曰:自然之摹仿。自然可供艺术之摹仿只有其外形。但外形只是物之外表,内部必有其活动之内容,……中国画学理论自六朝以来向有形似与气韵相对之说。形似者外形也;气韵者内容之意识也。故艺术表现之范围有内外两面。严格言之,画主外形,诗主内容。然中国画之理想以能表现到内容为目的。”可见亚里斯多德对摹仿对象——现实世界以及摹仿内容的认识,也影响到了邓以蛰的艺术形意观。邓以蛰强调“书”之肇于自然,虽不同于“摹仿”说,但也注意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尤其他充分吸收了“摹仿”说中对现实世界内外之分的看法,并结合克罗齐表现论进行创造性阐释。
二、从“形”到“意”的艺术史发展规律
邓以蛰谈艺,向来坚持史论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研究视野中,中国书画史也呈现从“形”到“意”(也即从单纯注重“形”到追求内在意趣)的动态发展过程。
邓以蛰在《书法之欣赏》中指出,从“形式”到“意境”是书体进化的轨迹。“一切书体可归纳之于形式与意境二种,此就书体一般进化而论也。”其所谓“书体”偏重于字形。中国古代书体种类众多,有古文、籀文、大小篆、古隶、八分、章草、行草等。他认为篆隶等书体由于间架、行次整齐端庄,常用于铭功颂德的金石丰碑、高文大册,故称之为“形式美之书体”。秦石汉碑几乎都采用这种书体。魏晋之际,“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的新书体——行草开始出现,是为“意境美之书体”。行草书体的出现得益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官方禁止立碑,社会对形式美的书体渐少需要;其二,绢纸笔墨的制造工艺日益精良,“书所凭借之工具,无复如笨重之金石类,而为轻淡空灵之纸墨绢素,其拘束之微,得使书家运用自如。”其三,“汉魏之交书家辈出,书法已完全进于美术之域,笔法间架,讲究入神”;其四,“魏晋士人浸润于老庄思想,入虚出玄,超脱一切形质实在”。可见,社会政治因素、书写工具制造工艺及书法技艺进步、哲学思潮都对意境美之书体替代形式美之书体起到了推动作用。
就绘画而言,从形到意依然是不变的发展趋势。邓以蛰在《画理探微》中先是别画于绘,然后离形于体,之后进一步就画之“形”的变化方式梳理。他以商周为形体一致时期,秦汉为形体分化时期,汉至唐初为净形时期,唐宋元明为形意交化时期。从这一阶段性划分和命名来看,前两个时期中国绘画尚未走出对器体的依赖关系,“其形之方式仍不免为器体所范围”,后两个时期才进入完全脱离器体并从形到意的阶段。具体来说,这四个阶段所产生的艺术种类有“体”(一切工艺及建筑)、“形”(绘画,以禽兽人物画为始)、“意”(山水画)三种,而在“意”这一类艺术中又进一步有层次之区分,有达到最高境界的“气韵”型艺术。邓以蛰指出:
形者脱于物质之拘束,而以物理内容(生命)为描写之对象者也。形者画也,欧阳之论画言难画之意,难形之心,是形与画相通也。画事异于体之造作而始于生命之描写,故形以禽兽人物画为始也……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束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则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由于“气韵则超过一切艺术,即形超乎体,神或意出于形,而归乎一‘理’之精微”,因此又可将这一艺术类型称为“理”。《画理探微》第二节标题“论艺术之‘体’、‘形’、‘意’、‘理’”即是此意。从“体”而入于“理”,其实反映了中国艺术从对器体的依赖到脱离器体,进而到追求生命之描摹,再到不拘于形似乃至完全以“意”之表现为核心的整体历程。从宏观角度看,其中恰恰隐含了从“形”到“意”的发展趋势。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到后期,尤其是“气韵”(“理”)型艺术,几乎全以画家主体之“意”为转移,“形”则成为次要的因素。因此,有学者指出,“邓以蛰对书画史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书画艺术的历史,是朝着表现书家和画家自我情感的方向前进的。越是后代的书画艺术,它们‘表意’、‘说理’的成分也就越发浓厚和明显。”而正因为把握到中国艺术的这一历史进程特点,邓以蛰才进一步得出“画为心画”的结论并做了深入阐释。1951 年,邓以蛰在回顾总结中国艺术史时说:“我们的理论,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决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养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因之,增我们民族的善于对自然的体验的习惯。”“画史即画学”,这既是他对中国书画艺术史及理论史发展特点的准确概括,也是他亲身践行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是从“形式美”到“意境美”的书体史,还是从“体”、“形”至“意”、“理”的绘画发展史都是在“画史即画学”视野下成就的发现,更准确概括了中国书画艺术从“形”到“意”的发展历史。
三、重形或重意
邓以蛰持“画为心画”看法,对“意”的重视是明显的。但对于书画等诉诸视觉的艺术而言,“形”又是必不可少的。他并不否定“形”的必要与重要,只是认为应该恰当把握和处理形、意二者在不同艺术类型中的关系。
首先,或形或意的偏重是了解诗画关系以及二者不同艺术特点的重要标准。诗与画之关系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关注重点,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者莫过于苏轼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苏轼此论是对诗画互融的褒扬和提倡,也代表了传统的观念。邓以蛰认为,一般以表现媒介区分认识诗画的做法不足取,因为“诗有声韵言词,画用颜色笔墨,乃艺术之区别,非诗画之究竟义也。”他从形意关系的角度对诗画互融的传统观念作了进一步申说。他认为“诗有意而无形,实则诗中无不有形。……画有形而无意,然山水画重气韵,气韵所以表出意境者也。”可见诗之“无形”与画之“无意”都只是浅层表象,真实的情况则是诗“主意而重形”,画则“主形而重意”。在这里,形与意既是区分诗画艺术的参照因素,又是标显诗画艺术特色的坐标。由形与意之关系来看诗画之关系、特点,邓以蛰有一段话至为深刻:
诗主意而重形,是以“情必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画主形而重意,是以画重气韵生动之意。意有首尾终始之变迁,动也;形为事物之结构与范围,静也。由动观静,则情景一致,事事如画,此诗人之态度也。画家之态度乃由静观动。由静观动,则盈天地万物之间者,莫非生气;生气运行实能一以贯之于万物……山水画取动静交化,形意合一之观点,纳物我、贯万物于此一气之中,韵而动之,使作者览者无所间隔,若今之所谓感情移入之事者,此等功用,无以名之,名之曰气韵生动。此山水画不重形而重理之故也!
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主形而重意,故能以静观动,达到“纳物我、贯万物于此一气(按:生气)之中”的效果。而作者和览者也可以在其中沟通并产生共鸣,这一切都可以归于绘画之“气韵生动”的效用。西方所谓审美“移情”的发生大概也不过如此。此时,山水画之“意”就等于“理”、等于“气韵生动”,而画之“形”或“形似”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非摹拟外物之形似,但为绘画者心中之意境以形象也。”因此,“形似”的涵义其实有两种:其一是摹拟外物之形的“形似”,其二是以绘者心中之意境为转移的“形似”。就后者而言,此种形似之“形”虽呈现物之形,但已非物之实“形”,而是融绘者心中意境为一的“形”。故曰:“山水虽写形,而实为心画”。邓以蛰在《画理探微》中用了较多篇幅论“形似”与“气韵”的对立。其所谓与“气韵”对立的“形似”即是第一种涵义。由此观之,主“形”的绘画对“意”的追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邓以蛰从形意二分的角度看诗画之分别对于认识中国绘画主形重意的特点也有重要意义。
其次,形意之辨还是邓以蛰判别南北宗差异的标准。南北宗之说自明代董其昌提出之后盛行不衰,直至近代在“五四”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思潮推动下,才受到徐悲鸿、滕固等大家的质疑和批判。而与徐、滕等人同时的邓以蛰却不受时论影响,从画史及笔法等角度对南北宗之说加以详析。而前述诗与画、形似与气韵的问题都与南北宗的辨析有关,这几个问题相互渗透交叉结合,最终形成一个有关中国绘画发展及艺术特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批判南北宗之说的观点不同,邓以蛰不仅认同于这种派别的划分,更进一步指出南北宗之分其实涉及到哲学上的见解和主张。这正好与他分析南北宗各自不同创作手法和艺术理念的做法相呼应。他为了突出中国画的独特个性,先将画与绘进行了区分,指出别于绘之“画”或者说书画同源之“画”的一大特点就是“笔法”。笔法之重要不仅因为它是画之必不可少的“工具”,更在于它是承载“形”、“意”的媒介,能体现不同的艺术个性,担负着绘画发展流变的使命。因此,“山水为画,画在乎笔”。作为中国自唐代开始的重要流派划分,南北宗的分别自然要表现于笔法。邓以蛰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就山水画言,所谓南北宗亦由笔法分派。南宗用中锋演为披麻皴,北宗用侧锋演为斧劈皴。”披麻皴脱胎于正锋,斧劈皴脱化于侧锋,侧锋易于取物之形势,故成勾砍之法。“勾砍者其用笔但为涂抹耳,绘或有之,其于画之能事实背道而驰。”所以,邓以蛰重南宗轻北宗的倾向十分明显,其别画于绘,突出画之“笔法”的用意也于此彰明。勾砍之法易取物形,而“以中锋笔法作画,再比之于浓艳勾砍之院体北派,似乎简率。”南宗与北宗,一简率一重物形,故邓以蛰在《南北宗论纲》中以一语简括二者:“南宗者心画也,北宗者目画也。心画以意为主,目画以形为主。”简率者因其重意不重形,故曰心画;重物形者自然以视觉效果为主,故曰目画。由于王维向来被视为南宗之祖,邓以蛰也围绕王维及其画学评论展开了论述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画以意境为主,后人师法王维主要祖其意境而非其画法。以意为主不仅超脱迹象,且以山林泉石之“天趣”为宗。同时,王维既是画家又是诗人的身份,不仅开辟了后世南宗山水画家必为诗人的先河,而且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表现特点相应。由于“画主外形,诗主内容”,提倡“画中有诗”其实就是主绘画重意的表现。
最后,邓以蛰对画之形意关系的探究也与其对中西方绘画区别的思考有关。在其发表于1935 年的《国画鲁言》中,他由中国绘画的表现工具——线纹说起,认为中国山水画画家最注重胸襟与笔法——这是与西方绘画的根本不同。他说:
中国山水画最初是诗人专有的艺术。唐宋山水大家如王维,郑虔,郭忠恕,范宽,米芾之辈,无一不是诗人。因此中国画的描写是诗人的胸襟,不一定是直接的自然。谢赫绘画六法首重“气韵生动”,次为“骨法用笔”。若“应物写形”,“随类傅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法,不过是画家学习的初步。若欲养成一真正画家,陶冶之功,要与诗人无异。
以胸襟沟通诗人与画家,其实就是强调绘画创作要以“意”为主、以“意”为先,中国传统画论的“意在笔先”即是此意。所以“欲于中国绘画中寻求彻底的写实派终属无望”。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林风眠在《国画鲁言》按记中不仅高度评价了邓以蛰比较中西绘画差异的做法观念,更由此进一步提出:“我觉得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发达,而缺少精神之表现,把自己变成机械,把艺术变成印刷物。东方艺术,于形式上之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上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消遣的戏笔。其实西方艺术之所短,正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西方艺术之所长。短长相辅,世界新艺术之产生,正在目前。”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汇的二十世纪初,中西对照的思维视角比比皆是,而邓、林二人的见解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有独到之处。其最终指向当然是彰显自我民族特色的同时,求得世界性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结 语
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曾在《谈中国画的特征》中指出:“我觉得中国画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意’字,所以古人一谈到作画,便要提到‘意在笔先’这句话。这个‘意’字,包括的内容很广,……六法论中的‘气韵生动’一词,可以说就是‘意’字的最高境界。……中国画的第二个特征,我认为是‘笔墨’。……其实它就是具体完成和表现出画面的东西,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凭它来分辨画家水平的高下的技法部分。它不能离开‘意境’与‘形’‘神’而单独存在,所以谢赫把‘骨法用笔’两者合为一词。”无独有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美学家之一的邓以蛰在他的书画艺术美学中也表现出几乎一致的看法。他说:“骨法用笔和气韵生动是我国自六朝以来,画理上两个基本问题。骨法用笔是技术上的问题,也就是画法上的传统的问题;气韵生动是效果问题,也就是鉴赏的问题。”技术画法关乎“形”,气韵生动关乎“意”。这既是对传统画学的理解,也是其研究视角的说明。从技术笔法入手进而至于艺术效果,邓以蛰对传统绘画的美学审视正是在技术与效果两条思路并行的基础上展开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形”的关注和重视上,邓以蛰表现出对书画艺术笔画技法独到而精深的分析理解。这是一般美学家常所不具备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多美学家或专注于哲学思辨的理论演绎,或从感性认识出发寻绎艺术的审美特质,较少有人如邓以蛰这样从专业技法入手进而及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其家学渊源的熏陶渐染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的形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总而言之,“形意之辨”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美学思想体系,成为除史论结合(即“画史即画学”)之外另一大研究视角和思路特点。
〔注释〕
①王有亮将邓以蛰的美学思想概括为“心物交感”美学(简称“交感美学”)(王有亮:《“现代性”语境中的邓以蛰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唐善林则认为应该将其命名为“心本”美学(唐善林:《“心本”:邓以蛰美学命名的一种尝试》,《文学评论》,2011 年第6期)。
②刘纲纪:《邓以蛰先生生平著述简表》,参见《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470 页。
〔1〕朱志荣.论邓以蛰中西融通的美学研究方法〔J〕.文艺理论研究,2011(3).
〔2〕凤文学.画史即画学——邓以蛰书画美学及其方法论意义〔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
〔3〕唐善林.“心本”:邓以蛰美学命名的一种尝试〔J〕.文学评论,2011(6).
〔4〕孙宗美.“意境”与道家思想——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范例论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
〔5〕邓以蛰.邓以蛰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王有亮.“现代性”语境中的邓以蛰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刘海粟.谈中国画的特征〔J〕.美术,19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