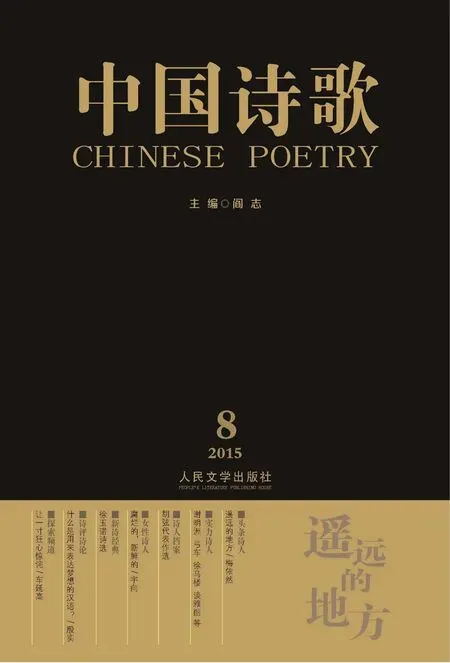外国诗歌选
□舒丹丹 树才 松风等/译
外国诗歌选
□舒丹丹 树才 松风等/译
蜡烛【法国】弗朗西斯·蓬热
黑夜有时使一种特殊的植物生机勃勃:它的光辉把带家具的房间分解成大块的影子。
金色的叶片由一根黑柄托着,静立在莹白小圆柱的凹处。
卑微的蛾子喜欢进攻的是烛光而不是那高高在上蒸腾着树林的月亮。然而,不是马上引火烧身、就是在战斗中精疲力竭,所有的蛾子都在几近木僵的疯狂边缘颤抖。
不过,在毕剥的烛烟中,蜡烛在书本上摇曳烛光鼓励读书人,之后倾向碟盘淹没在养料中。
我的一生【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这里又一次,饱含回忆的嘴唇,独特而又与你们的相似。
我就是这迟缓的强度。一个灵魂。
我总是靠近欢乐,也珍惜痛苦的爱抚。
我已渡过了海洋。
我已经认识了许多土地:我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
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
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日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与上次和所有人的相等。
致丽卡【俄罗斯】列·利·阿隆宗
请把这个夜晚珍藏在自己胸间
瑟缩于冬天的室内,走进去,如同落入水里,
你全身——是河流低沉喧嚷,
你全身——是冰块沙沙作响,
你全身——是我压抑的高呼与空气。
冬夜与寒风。拍打着街灯,
犹如冻僵的手指敲击着玻璃,
这些——一切都记得烂熟,
这些——一切要记得没齿不忘,
你还要重新变得一无所知。
阴影重现于河流,河流发出微弱的簌簌声,
那里冰块在边缘处破碎,
你——是冰块的新生,
你——是没有呼出的呐喊,
哦河流,你像天鹅从容不迫地飞行。
请珍藏好这个夜晚,这北方与寒冰,
它们捶打着手掌,如同舞蹈,
你全身——是河流的呼喊,是空阔的
白色奇迹之间的蓝色转弯。
夜间巴黎【法国】普雷维尔
三根火柴一根接一根在夜里划亮
第一根为了完整地看清你的脸
第二根为了看见你的眼睛
最后一根为了看见你的嘴
而完整的黑暗为了让我回忆起这一切
把你紧紧地拥在我怀里。
盛年【英国】菲利普·拉金
一种停滞的感觉……正如,我想象
直到孤单的身体变得
疲倦,不真切;
然后开始感到一种向后的牵引
在替代,令人厌恶而专横——
有人说,充满欲望。
这一定是生命的盛年……我闭眼,
仿佛疼痛;的确疼痛,想起
这场哑剧,
关于补偿与消解,
挫败与伪装,事实上,构成了
我生命的盛年。
缺席【英国】伊丽莎白·詹宁斯
我去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什么也没改变,花园照管得很好,
喷泉喷射着它们惯常的稳定的水流;
没有迹象表明某事已经结束,
也没有什么教我学会忘记。
一些愚笨的鸟儿从树里面窜出来,
唱着我无法分享的欢喜,
在我的思想里玩弄诡计。当然这些
欢乐里不可能有要忍受的痛苦,
也没有任何不和谐颤动着半静的风。
只因这个地方还和从前一样,
使得你的缺席像是一股残忍的力量,
因为在这所有的温柔之下
一场地震的战栗来临:喷泉,鸟儿和青草
因为想起你的名字而颤抖。
布朗尼为什么离开【爱尔兰】保罗·穆顿
布朗尼为什么离开,他去了哪儿
到现在还是个谜。
因为如果有人应该满足,
那就是他;两英亩大麦,
一英亩土豆,四头小公牛,
一头奶牛,一幢石板屋。
他最后被人看见是出去犁地,
在一个三月的早晨,大清早。
到中午布朗尼就出名了;
人们发现被抛弃的一切,
最后的农具还未解开,他的两匹
黑马,像丈夫和妻子,
换着蹄子承受负重,
凝视着未来。
来自漫长而悲伤的舞会【美国】马克·斯特兰德
有人在说着
一些事,关于阴影覆盖着田野,关于
事物怎样消逝,一个人怎样睡到天明
以及清晨怎样离去。
有人在说着
风怎样减弱又重新回来,
贝壳怎样变成风的棺材,
天气却在持续。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有人说月亮正倾泻银辉
在冰冷的田野上,前方杳无一物
除了更多的相似。
有人提起
战争前她一直居住的城市,房里有两支蜡烛
靠着墙壁,有人跳舞,有人凝视。
我们开始相信
这个夜晚不会结束。
有人说音乐放完,但没有人留意。
然后有人说起行星,说起恒星。
它们多么渺小,多么遥远。
雪【法国】伊夫·博纳富瓦
她来自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
她触摸草原,花朵的赭石色,
凭这只用烟书写的手,
她通过寂静战胜时间。
今夜有更多的光
因为雪。
好像有树叶在门前燃烧,
而抱回的柴火里有水珠滴落。
从橡树头步行回家【美国】玛丽·奥利弗
有什么东西
在这飘满飞雪的天空
在冬季
在这向晚的黄昏
将欢欣带给心
还有时间
可爱的无意义。
无论我何时回家——无论何时——
某人总在那里爱着我。与此同时
我站在同样黑暗的宁静里
宛若任何一株松树,
抑或缓缓向前游荡
就像那依然从容的风,
等待,
仿佛等待馈赠,
等待雪开始飘落
起初随意地,
继而,狂漫不已。
无论我生活在什么别的地方——
在音乐里,在词语里,
在心的火焰里,
我一样深深地安居
在这无名的、不可分的处所,
这个世界,此刻它正分崩离析,
白茫茫狂乱一片,
它忠实得超越了所有我们对忠实的表达,
我们最深沉的祈祷。
别担心,迟早我将回到家里。
双颊被激荡的风吹得通红,
我将站在门廊里
跺跺靴子,拍拍手,
我的肩头
落满了星星。
迷醉【法国】安·阿尔托
银白色火盆,木炭凹陷
连同它内在力量的音乐,
木炭被镂空,被释放,树皮
忙于献出它的世界。
对自我的苦苦追寻
穿透正超越自身,
啊!让冰块的柴堆
同想念它的精神会合。
深不可测的古老追逐
在欢乐中向外渗漏,
感觉灵敏的肉欲,
迷醉
在歌唱的水晶中。
呵!墨水的音乐,音乐
葬身地下的煤的音乐,
温柔,沉甸甸,解救我们
用它秘密的磷。
铁路儿童【爱尔兰】谢·希尼
当我们爬上路堑的斜坡
我们的眼睛便与电线杆上的白瓷杯
和咝咝发响的电线齐平。
像可爱的悠闲之手它们向东向西蜿蜒
好几英里直到我们看不见,悬垂
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
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
那些值得知道的事。我们料想文字在电线上行走
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闪闪发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种子般装满了
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我们
相比之下是如此地无穷小
简直可以一下子穿过针眼。
底片【波兰】希姆·博尔斯卡
在昏黑的天空中,
飘动着越来越暗的乌云,
还有围着一道黑圈的太阳。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白樱桃树枝上盛开着黑花。
阴影投射在漆黑的脸上,
你坐在桌子旁,
把灰色的双手搁在桌上。
你给人留下鬼魂的印象,
却试图摆出活人的姿态。
因为我是活人中的一员,
就该对他有所表示,
应该向他问候:
晚安或者日安,
告别或者欢迎,
也可以向他发出问题,
但不能期望他的回答。
不管是涉及到生活,
还是雷鸣后的寂静。
四月【美国】W.S.默温
当我离开石头将停止歌唱
四月四月
在姓名的沙砾间沉落
未来的日子
星星不在其中隐藏
你若安于等待你就在那儿
你若不曾丢失什么
你就一无所知
工程师【巴西】若昂·卡布拉尔
光、太阳和自由的空气
包裹着工程师的梦。
工程师梦见明亮的事物:
面积,网球,一杯水。
铅笔,角尺,纸张;
草图,方案,数字:
工程师琢磨着正确的世界
那里无须任何帘幕来遮蔽。
(有几个下午我们登上了
那栋楼。每日所见的城市
像所有人都在阅读的一份报纸,
它拥有了一个水泥和玻璃的肺。)
与河流相邻,上方是云,
水,风,明亮
将这栋楼置身于自然之中,
凭着简洁的力量,楼在生长。
田野【德国】保罗·策兰
永远那一棵,白杨树
在思想的边缘。
永远那根手指,立在
田埂边。
前面远远
黄昏中的田垄已经动摇了。
但见云朵:
飘过。
永远这只眼。
永远这只眼,遇见
沉沦姊妹的音容
你就抬起它的眼睑。
永远这只眼。
永远这只眼,目光吐丝
缠住白杨,那一棵。
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节选)【叙利亚】阿多尼斯
什么是路?
启程的宣言
写在一页叫作泥土的纸上。
什么是树?
绿色的湖泊,波浪是风。
什么是空气?
灵魂,不愿在身体内
落户。
什么是镜子?
第二张脸,
第三只眼睛。
什么是神圣?
一副面具,
用以称颂被玷污的事物。
什么是死亡?
在女人的子宫
和大地的子宫间
运行的班车。
什么是彩虹?
云彩的身体
和太阳的身体
在大地的身体之上
折腰相拥。
什么是波浪?
在大海的屏幕之上
浮动的画面。
什么是岸?
波涛休息的枕头。
什么是星星?
一本书,
最美的是书的封面。
什么是老年?
朝着两个方向生长的禾苗:
童年的黎明,
死亡的夜晚。
什么是夜色?
孕育太阳的子宫。
你从未见过蝴蝶【罗马尼亚】安娜·布兰迪亚娜
你从未见过蝴蝶
观望我们的模样吗?
你从未见过风
在我们走过时
向青草发出的信号吗?
倘若我蓦然转过身来,
那些树枝会愣住不动,
只等着我们一步步走远。
你没注意到鸟在降落吗?
你没注意到叶在凋零吗?
你没注意到沙沙声
就像朝北的树干上的青苔
在我们背上生长吗?
还有随处迎候我们的沉默……
所有事物都知道些什么,
只是对我们隐瞒。
也许我们都是罪人。
高昂的代价早已加在我们的头上。
夜幕降临,星星兴奋地闪烁,
而玉米叶子发出阵阵叮当的响声。
小紫菀【德国】贝恩
一个淹死的啤酒运送工被抬到解剖台上。
有人在他牙齿间
夹了一朵深紫色的紫菀。
当我用一把长刀
从他胸部
皮下切开,
割下舌头和上颚时
准是碰着了小花,
因为花儿滑进了旁边的颅脑。
在缝合切口时,
我把紫菀塞进了
他腹腔的木棉之中。
在你的花瓶里喝个够吧!
安息吧,
小紫菀!
路上的秘密【瑞典】特朗斯特罗姆
日光落在一个睡者的脸上。
他的梦更加生动
但他没有醒来。
黑暗落在一个在不耐烦的
太阳强光中行走于他人中间的
人的脸上。
天色如一场骤雨突然转暗。
我站在容纳每一时刻的屋里——蝴蝶博物馆。
阳光依然强烈如初。
它那不耐烦的画笔正描绘着世界。
消息【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关于地球文明,我们将说些什么?
它是用浅蓝色玻璃铸成的鲜艳球体,
有一条保持卷曲和舒展的闪亮而清澈的细线。
或者说它是一排旭日图案的宫殿
巨大的门在苍穹急遽升起
它的后面走着一个没有面孔的怪物。
于是每天都在抽签,无论谁抽中
将作为祭品走过那里:老人、孩子,年轻的少男和少女。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们生活在金羊毛里,
在一片虹的网里,在一片云茧中
悬挂在一棵银河树的枝干上。
而我们的网用符号织成,
作用于耳目的神秘符号,爱情的指环。
一种在内心回响的声音,塑造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轻快,颤动而婉转的语言。
我们根据什么才能编织成界限
在内与外,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如果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我们温暖的呼吸,
以及唇膏,薄纱和棉布,
根据寂静得使世界死亡的心跳?
或许我们对地球文明无话可说。
因为没人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早晨【美国】雷蒙德·卡佛
这个早晨不同寻常。一点小雪
盖在地上。太阳浮在清澈的
蓝天里。海是蓝的,一片蓝绿,
远到视线所及。
几乎不起一丝涟漪。静谧。我穿上衣出门
散步——在接纳大自然必然的
馈赠之前不打算回来。
我走过一些苍老的,躬着身子的树。
穿过散落着堆积小雪的石头的
田野。一直走,
直到悬崖。
在那里,我凝望着大海,天空,以及
在低远处白色沙滩上盘旋的
海鸥。一切都很可爱。一切都沐浴在纯净的
清冷的光里。但是,和往常一样,我的思想
开始漫游。我不得不集中
精神去看那些我看着的东西
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就是
紧要的事,而不是别的。(我确实看着它,
一两分钟之久!)有一两分钟
它从往常的关于是是非非的沉思中
挣扎出来——责任,
温柔的回忆,关于死亡的想法,以及我该如何对待
我的前妻。我希望
所有的事情这个早晨都会离开。
我每天都要忍受的事物。为了
继续活下去我所糟践的东西。
但是有一两分钟我真的忘记了
我自己以及别的一切。我知道我做到了。
因为当我转身返回我不知道
我在哪里。直到鸟儿从扭曲的树上
腾空飞起。飞翔在
我需要行进的方向。
高山【美国】露易丝·格丽克
学生们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我给他们解释:艺术的生命
是一种无尽的劳作。他们的表情
几乎没有变化;他们需要多了解一点儿
什么是无尽的劳作。
所以我给他们讲起西西弗斯的故事,
他是怎样被判将一块石头
往山上推,并清楚这种辛劳
将毫无结果,
但他愿意这样日复一日
没有期限。我跟他们讲
这里面有快乐,在艺术家的生命里,
一个人逃脱了判决的
快乐,当我说
我自己也正秘密地推着一块石头,
偷偷地沿着高山陡峭的一面
往上推。为什么
我要对这些孩子撒谎?他们并没有在听,
他们也不会被蒙骗,他们
用手指轻轻敲着木桌——
所以我收回
那个神话;我告诉他们
这发生在地狱里,而艺术家撒谎
因为他为抵达所困扰,
他觉察到顶点
将是他永久居住的地方,
一个将被
他的负担转化的地方:每一次呼吸,
我正站在高山之巅。
我两手自由。而那块石头
已经增加了山的高度。
仍然是囚室【美国】约翰·阿什贝利
隔着黄色的餐桌传来一句话(只是进入
这些脑筋不断翻新的时代的门票):你必须展示给他们你的形象。
仅仅说是一个人不管用了。他们很多人都喝啤酒。
危机或灾难在他们生活中每几个小时
就发生一次。他们不习惯,没有记性。
他们也不认为那样就会好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是他们的一部分,有机的组成。没有空间,无法后退一步
获得一个观点。那个老头子一边买东西一边思考。地窖里
散发着香味的洋葱也没用处。上周这儿有个男的。
但试着把它弄清楚吧,当你处于
命运巅峰的时候。就好像天使在针尖上互相推搡。
直到有人掉下来了,或迟疑了,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可那只能维持一小会儿,如同一个没有空调的
闷热的下午的一次呼吸。那时
我很害怕。现在不了。它可以像袜子一样脱下来
作一点小小的修补。写书的材料。
当我开口歌唱,很难再沉默不语……【俄罗斯】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当我开口歌唱,很难再沉默不语,
当我一声不响,很难去放声歌唱。
从清早嘴里便发出这样的忧伤,
任何溶液都不会把它洗净。
不要醒来,千万别!
楼里的人们早晨七点便都不睡了——
百叶窗咯吱咯吱地打开,
汽车钥匙也迫不及待。
既然醒了,那就越过汽车和窗子
环视一下生活。
泛绿的刺骨的幽蓝——
草木茂盛的群山,宁静的苍穹。
不,你不是夹竹桃的花朵,
不能减弱汽油的呼气。
你的窗口朝向东方,
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来沉默和呼吸。
吉尔伯特·怀特死后发表的信【英国】W.H.奥登
如此伤感我们仅能遇见这些人
他们的日期和我们的重叠,一个真正的耻辱
是你和梭罗(我们知道他读过你的东西)
从来没握过手。我们听说,他是,一个狂热的
反教者而且性情急躁,你这
最安静的助理牧师,我想他会很幸运地
发现你这个理想的友人,他给你写的信
是这样的富有趣味,但你们从来没有邂逅。
不变的,你们两个,只是热心步行的人,
而且有着自然生活的纯洁,它似乎是,免疫的
充满世俗力量的山溪,相类似的心灵,
发现所有的动物都使人欢欣,甚至
即使乌龟陷入了悲伤的昏迷,
它也仍然面对着天气飘忽不定的心情,
从迷雾的谦逊的品行
到闷雷的粗俗的打嗝声或者彩虹
联合的拱门,多么有趣你眺望着
两道对垒的风景还有那些候鸟,没有什么
猫头鹰在上面鸣叫的沥青,比较着
扬抑抑格和扬扬格的回声。
多么自私,我也,由查明而知道你的底细:
我已经学会了这么多。我敏于想象
我自己就是自然的一个情人,
但是没什么权利,确切地说。多少
鸟和植物我能够看到?至少两打。
你,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无知的人
一种烦人的厌倦。时间宽宥了你:我
尽可以,感谢上帝,重读你东西的权利。
雨中【美国】丹尼斯·莱维托芙
老人黑色的脸庞
闪耀着棕色,如同路灯下
湿润的鹅卵石,两只
一大一小的狗伴随着他,走在雨中,
走在傍晚空荡荡的大街上。
矮小健壮的那只狗打算停下,
眷顾垃圾箱哀求的灵魂,
而年轻高大、卷毛的那只,想继续
前进;闪烁不定的人行道诱惑他走向种种未知之中。
雨变大了。秃顶的老人
一边微笑着,一边自言自语。
灯光变了;大街上
连绵无尽的车轮反射着微光,如同礼拜式的
红色注解。他漂浮在
两只狗的欲望之间。
他们三个——
现在走上了横穿小镇的马路——沉浸在
彼此相伴的感觉中,沉浸在愉悦,
天气,角落,
彼此悠闲的冲突
以及隐秘的沉默中。
纪念一个诗人【立陶宛】托马斯·温茨洛瓦
我们将再次见面,在彼得堡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你是否回到了城市,它的规划、
副本和骷髅承诺过的地方?
暴风雪带着它的海军部快速行动,
它成几何级数增加的绘画工作
在压平一切的工序中衰弱。
当电力切断,
从冰冷的鬼魂中,阴影诞生,
锈迹覆盖的机车
潜行在伊兹马伊洛夫大街。
还是同样的电车,同样穿旧的大衣。
沥青路光秃秃托举着废纸屑,
来自上个世纪的寒意
淹没了整个车站。
轰鸣声,天空
封闭。年代苍白,
黑暗的城市如浓雾擦肩而过,
各种手势重新浮现如礼物,但是
从来没有人能出生两次。
他走进二月的早晨
走进另一个空间,测量着他
和大雪来临的时间距离。
母狼冻结的洞穴,
疯人院,监狱和泥浆在召唤他。
黑色的圣彼得堡是他熟悉的
有一回曾经提及。
标准与和谐不能重生,
木板噼啪作响仿佛传达着
时间点燃的壁炉的温暖,
而有一种壁炉之火万古长新,
光学已完成关于其命运的评估:
精髓在于快乐的可比性,
有时甚至在简单的会见里,
在可持续性中,具有永恒的形式。
现实没有镜子:清晰,干净。
一座岛屿,植根于水沫四溅的激流,
代表未实现的天堂
诞生于一次现场演讲,
仿佛在云层之上,在轮船的烟管之上,
鸽群在一只巨轮周围盘旋,
不敢从一个平常的转绿的山头
认出亚拉腊山。
开船!是我们启航的时候。
虽然岩石开裂,谎言流布,
见证者留下的惟有艺术
照亮最深的冬夜。
青草带着它的祝福留在冰层里。
河口在寻找幽黑的海洋。
现在一个简单、无意识的词破土而出,
几乎跟死亡一样毫无意识。
选自《故乡》/主编:游子衿/香港中波(管理机构)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