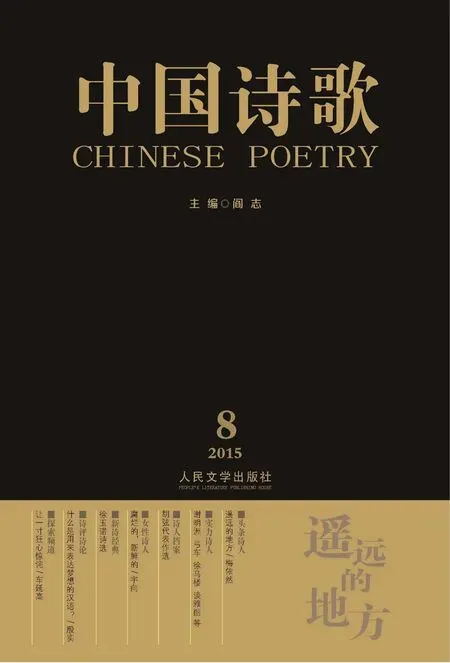腐烂的,新鲜的(组诗)
·组诗·
宇向
腐烂的,新鲜的(组诗)
·组诗·
每一个真正的人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是立在这星球上
由神的起重机
在魔鬼的深度里
垒起的高楼大厦
魔鬼袒露的秘密
有着一种向上的诉求
而从N层到底层
每一层都宅住一个神
每个房间都降下了
神的小孩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渴望高高站起
在恰当的地方
他召唤和哀嚎的剪影
是月下孤狼
刺向闪电的剪影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渴望先知般
截获神的字条
饮下第一滴雨
在清晨最早的阳光中
一层一层醒来
(像一条被光捋顺的蛇)
并在漆黑的夜里
最高的和那最低的呈同一水平
远
我曾倒在
登珠穆朗玛的路上
12年后
我从喜马拉雅头顶
缓缓飞过
从远开始的远
又白又冷
我曾倒在那儿
高原上,指尖触碰星星
“远”是垂首。刺目。寒气逼人
西藏是一种远。蓝毗尼
是远于西藏的远
童年是一种远
裹在暗红丝绒里的望远镜也是
寺院是一种远
相爱是。深海是。墓地是
咫尺是。一个人是
离世的心是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远
新的远离弃旧的远
真的远
在更远的远处
沉迷不语
你走后,我家徒四壁
我的家曾是一座坟
堆满死人的书
我读书,是给他们
狂热地,给他们
直到你循声而来
把这里栽成一朵巨大的花
那时,你身无分文,心为圣徒
还信着我的神
你在此点燃炊烟。建筑农园
研墨。浇灌。放牧。旋风般撕碎猎豹……
那时,诗行是噬咬着的
上一行成为下一行紧紧地
不能分开
那时,你无名,我便爱着空旷
像爱着濒死人的心,以为我是你
那时,仅仅一次,就能道尽终生
如今,诗行保持绝妙的平行
我衣袖尽空,跟别人没两样

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老妇
她站在人行道上,好像
在等我
没错
在片刻的意义上,以及
在一个凝固的
场景中。“等”
是如此的真实
一边是人。另一边
是其余的人
如果我,今天死去
如果我,今天死去
我的儿子活到六十岁的时候,我会成为他的女儿
他把我揽进怀里,抚摸我油漆斑剥的外壳,想
我该是高龄的华发,老泪纵横
如果我,今天死去
我儿子二十岁时,我是他梦想的情人
他用鼻子闻我,捧着我薄薄的诗集,却不翻动它,他早已熟记我所有的诗句
如果我,今天死去
我的儿子三十岁了,而我是他一生的挚爱
这永世的英雄,一只手就能把我托起,坐上他的马,他要带我游走天涯
2011,水平线
一旦登高
心就坠向大地
或投身于水
此时,上空,下水
太阳自两个方向
灼伤我,如同两种宗教
落单的白鹭在头顶
转一圈,又一圈
鸟在树林里
莫名地哀号
飞虫们念着经
参差不齐里是私下的虔诚
日日夜夜不间断
永远都在,你看不见
摸不到的地方
荧屏闪着亮雪花
山和树的倒影打着马赛克
这水不大,可它可以
一整个日子归我,单个的一个
它不是名水,有隐性的博爱
机缘要我遇它,就像
某种细微的难以抚触的在我的一生里
某种我的某一段脉搏只跳动它的事物
突然
一条鱼跃起,一块石子落下
波纹是一样的
动静是一样的
欢迎来到不死的农庄
只要有星空
我就仰面倒下
很多天以前,我就这样
倒在病床上
淡蓝色被单裹着我
点滴。封锁的新闻。氧气
一点点走失的体温
一本滑落的诗集
一个向下的天堂。好像
瞬间就化作这农庄
我怎么成为这农庄的压寨夫人?
我忘记了我应该忘记的
摩托车拖拉机卡车和汽车
白天曾经从这里驶过
此刻在我身体的下方
积满厚道、热力又潮汐样的命运
在寂静之外
是虫子们各自放歌
是口袋里响一曲
雪的消息
不惑的人听到雪的消息。面色平静
年少的情人在天亮打来电话:
下雪了,下雪了,我们去黄河吧
不惑的人想起初相见。他曾是
那个年少的情人。雪是他的老相识
他见过更美的雪更不值一提的雪更大的
大风雪。他看见一场雪粉碎着另一场
一朵雪拥抱着另一朵
他见过诗人的雪。犹太人的雪。他见过
雪的镇压。他看见了红色的雪。见过
雪的珠穆朗玛和雪的卡瓦格博
他看见不化的雪。他看见雪
落向土墙上穿着开裆裤啃硬馍的男孩子
落向土墙下小手肿裂如红薯的女孩儿。他见过
落向贫困的雪。落向天空的雪,落向一个问号,落向
母亲落泪的雪
不惑的人听到下雪的消息。看上去,面色平静
在关闭的屏幕上,你看到
一个独自在家的人
一个伟大的演员
一场蹩脚的室内剧
一个所有角色的扮演者
一个众人
独自的众人
一个人,众所周知
信
每天都有一些信在途中遗失
它与不信有关
它被风吹进树林,吹向
林中的坟地、墓碑以及碑前的
枯枝败叶
经过光线,它弯了一下
把死亡吹成一个美妙时刻
每天都有一个美妙的时刻
它与信有关
它落向焚烧的落叶。落在
乞丐指尖,落得下落不明
或被狗叼着,进入
动物世界
每天都有一封美妙的信,落在
雨中的路面
就像脚印
尘世被一步一步走远
被神之手
我家阳台对面
轮番修建世界各地的风光
今天,为了建百花大教堂
(外壁是令人哭泣的苍白)
一座印度寺院正被拆除
妈妈来到阳台
问我昨天有没有哭
我答,不过是想出门远行
三座新塑的橙红色头像倒了
绿砖红瓦发着铀光的一面墙紧接着坍塌
在楼前,像一个个被神的手
迅速抽空的麻袋
尘土一下子掩埋了我的房间
女巫师
我高龄。能做任何人的祖母
当我右手举起面具
左手握住心,我必定
货真价实。拥有古老的手艺
给老鼠剃毛。把烛台弄炸
被豹子吞噬。使马路柔肠寸断
分崩离析那些已分崩离析的人
我懂得羞涩的仪式
会忍痛割爱。当太阳自山头升起
照耀舞台中央的时候
我就是传统,无人逾越
当我把祭器高举
里面溅出幽灵的血。是我
在人间忍受着羞辱
我是思想界最大的智慧
最小的聪明。调换左右眼
就隐藏了慈悲和邪恶
而在每一个精确的时刻
我到纺织机后配制泪水
把换来的钱攒起来
现在我打算退休
成为平凡无害的人
爱国者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
随身携带一口棺材
乌木的料。空虚的里
防不胜防的谚语
他常常肩负众多外交的小旗远行
死亡就常常敲打他的驼背
看上去他多像个平常的老人
对荣耀深藏不露
对细节不屑一顾
且不再在意后辈
效仿他的一举一动
如今他要为国家利益
环球一周,在有生之年
计划。恩准。筹备
中国大棉袍、棉鞋
筹备褐色的眼球
灰白的毛发,以及
一颗中国心
而一想到心死国外
真正的爱国者便浑身颤抖
大诗人改诗
大诗人本是不改诗的
他的行走其实是
爱好者们的传阅仪式
这便是他“行走即传阅”的来历
他也会到小诗人当中去
自然是被请去的
大诗人亦愿意被请
在诗歌自习室里,偶尔
赞叹某人写得真好
多数时候沉默
他要找出那个一念之差的人
破一次例。试着加深一次拙劣
比如这次,一句“爱和恨都是卑微的”
让他眼睛一亮
他用铅笔把“卑微”改成
“卑鄙”,说,力量就出来了
我有
我有一扇门,上面写着:
当心!你也许会迷路
我有几张纸,不带格子的那种
记满我没有羞涩的句子
而我有过的好时光不知哪里去了
我有一个瘪瘪的钱包和一点点才能
如果我做一个乖乖女
就会是一个好女儿、好公民、好恋人
我就丢了自由并不会写诗
而我是一个污秽的人,有一双脏脚和一条廉价围巾
这使我的男人成为真正的男人
使他幸福、勇敢,突然就爱上了生活
我有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有手臂,用来拥抱
我有右手,用来握用来扔用来接触陌生人

我有左手,我用它抚摸和爱
而那些痛苦的事情都哪里去了
那些纠葛、多余的钥匙环和公式
我有香烟染黑肺、染黄手指
我有自知之明,我有狂热也有伤口
我有电,如果你被击痛你就快乐了
我有藏身之处,有长密码的邮箱
我有避孕药和安眠药
我有一部电话,它红得像欲望
我有拨号码的习惯,我听够了震铃声
为什么我总是把号码拨到
一个没人接电话的地方
腐烂的,新鲜的
阳光直射的中午
我蹲在阳台上择韭菜
手指上粘满绿色的浆液
和褐色的土
我折断粗茎
分开腐烂的和新鲜的菜叶
腐烂的和新鲜的
都再也不能重生
几只苍蝇和一只黄蜂
在菜叶上面飞,哼叫着
瞪着七彩的眼睛
它们喜爱浓烈的腐烂气味
它们的刺是被这正午阳光加热的
滚烫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