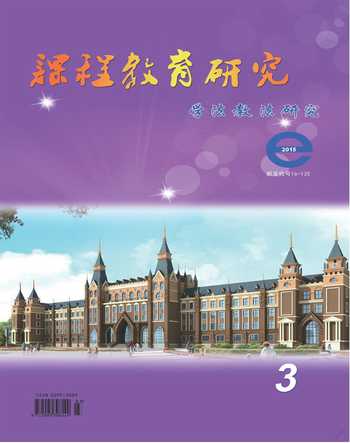浅论《儒林外史》科举文化下的异化人格
李光艳
摘要:《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文学中的巅峰之作,刻画了一系列被科举文化扭曲与异化的人物。本文具体以周进、范进、严监生为例,从封建社会所存在的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儒林文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生存状态,从而探究他们人格异化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儒林外史》 科举制度 异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9
一、《儒林外史》中人物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
科举制是我国由隋朝建立至清末废除的一种选拔人才、分派官职的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明清时期,古板的“八股取士”因其形式遵循守旧,日益僵化,完全脱离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丧失了积极意义,成为残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
明清两代,科举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读书、参试、做官是清代科举制度下文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增加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因此,文人几乎把科举中榜看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了民间流传的名言警句,“遗子黄金满篇,不如一经”是知识分子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入仕为官成了他们终身奋斗的目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科举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共识。士子们经受着严酷的精神摧残和生活压力,人格破损萎缩,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用尽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榜上有名,一举成功。由于“官本位”思想,让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考场,变成了士子们角逐的战场。在这样的利益目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的学习风气日益败坏,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科举制度也随着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败落。《儒林外史》正是清代科举制度社会的产物,吴敬梓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大批儒林形象,这些士子在科举制钳制之下,性格被异化,灵魂被扭曲。
二、《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下的异化人物
1.科举制度下的畸形儿“二进”
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他们耗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但在科场上却屡试不中,几十年的科场失意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辛酸、困顿和屈辱。
周進一生参加无数次科举考试,却“不曾中过学”,60多岁还是老童生一个。新进秀才梅玖当众嘲笑挖苦他一大把年纪了还是“童声小友”,不屑与之“序齿”,甚至还编了一首诗来挖苦他“呆,秀才,吃长斋……。”一个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能把周进的尊严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发了”的举人王惠更是在周进面前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扫了一早晨。周进打扫的是残渣剩屑,但呈现的却是穷塾师的卑微和辛酸。如果不中举,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以保住。长期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终使他有朝一日爆发。当他去省城参观贡院,见到因为自己不是秀才而无权沾边的号板时,不禁万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后伏着号板放声大哭,致使口中鲜血直流,郁结在他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此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范进,也是老童生,屡次参加科考,都以失败告终,在家遭受冷落,在外遭遇冷眼。在那样一个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妻子竟对他呼东唤西,老丈人胡屠户对他更是百般喝斥。因参加乡试没有路费,去找老丈人商议,却被老丈人一口唾沫吐在脸上,还嚷嚷大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发榜那天,家里无米下锅,范进却抱着唯一一只生蛋老母鸡去集上卖,邻居找来报喜,却不肯相信,可怜哀求不要开玩笑,不要去戳那淌血的伤口。正是由于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才不敢相信中举。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却惊喜发疯,“噫!好了!我中了!”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让人不寒而栗,也隐含着作者对于科举制度摧残人尊严的悲愤。
周进的“哭”,范进的“疯”,都是在内心积蓄大半辈子的屈辱和辛酸的总爆发,是在特定时刻情感的宣泄。他们极度渴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突然降临,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和疯这两种极端的情感表达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文人们对于八股科举如痴如狂的心态,作者以震撼人心的艺术之笔,揭露了科举制度害人之深。
2.科举制度下的“守财奴”
严监生本来叫做严致和,只因是个监生就被称作严监生。“两茎灯草”是他的一个经典性细节,被定性为爱钱如命的吝啬鬼、守财奴,是《儒林外史》中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
按科举律例,从秀才里选拔出来贡献到国子监肆业的叫贡生,贡生与举人、进士出身者一样,被视为正途。而监生只是标志着具有了同秀才一样参加考试的资格,监生比贡生功名低,更何况监生还是花钱买来的。在生存的大环境里,科举盛行,功名高低甚至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在朝廷和社会的双向作用下,一般进了学的文人,即使不做官,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结交达官贵人,横行乡里。
在这种境况下,严监生活得卑下委屈。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钱积得不够多,而是未能进学。在病重时向王德、王仁吐露了肺腑之言:“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所谓的“大房”也就是哥哥严贡生,就是因为没有“进个学”,终日受气。这种未曾进学的情结与胆小性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严监生的卑微人格。他深感自己生存的卑微,凡事畏灾惧祸,处事小心谨慎,唯恐不周全得罪了人。金钱也就成了他生存的武器和保全自己和家人免受伤害的重要手段。他收地租,开铺,兢兢业业管理着自己的产业,也是为了积聚金钱。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金钱越来越多,而是为了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更好地安身立命,为了在人际交往中为自己加一份砝码。对两位秀才舅爷,严监生是恭恭敬敬,惟恐怠慢不尊。为了子孙大业,严监生欲将生儿子的妾扶正,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严监生不敢得罪两位舅爷,先以妻子“留为遗念”为由各送了一百两银子,接着又送给两位舅奶奶些许首饰。妻子死时,两位舅奶奶将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光,连妾在仪式上戴的赤金冠子也拾起来带走,但这一大批价值昂贵的财物严监生哪敢追讨,只是“舍钱求安”的态度,反而又送了两家许多物资,又各封了二百两银子作为舅爷们的盘缠,如此慷慨,充分显示了严监生活得不自信。
他再三笼络两位舅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未进学,功名低,借两位有科举前程的“秀才”来给自己壮胆撑门面,以此与霸道的严贡生抗衡;另一方面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势单力薄,需要亲戚们的照应。严监生就是这样,活的卑微,死的窝囊。通过对严监生这一守财奴的无情批判,让我们认识到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异化人物的悲悯和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