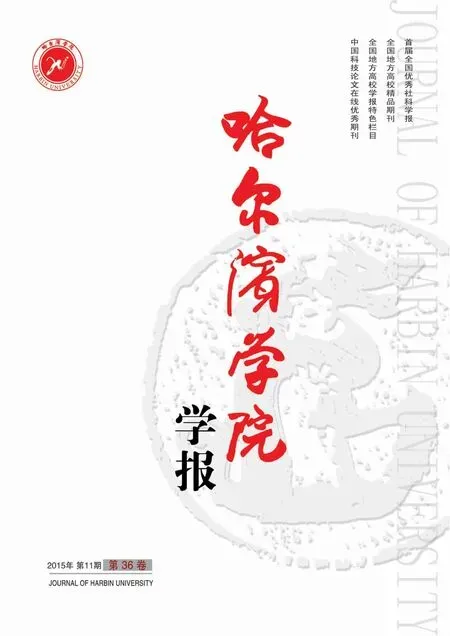近百年来国内外勿吉研究综述
王禹浪,王俊铮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22)
勿吉是南北朝时期我国东北地区强盛一时的重要民族,曾占领北沃沮,袭扰高句丽,驱逐夫余国,隋唐时期发展为靺鞨(靺羯)七部,其中靺鞨粟末部建立“海东盛国”渤海国、靺鞨黑水部后裔女真完颜部建立大金帝国,大清帝国的建立者建州女真与勿吉—靺鞨古族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勿吉在隋唐及其后历代王朝先后被写成靺羯、靺鞨、兀惹、乌惹、兀的改、兀者、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近百年来国内外勿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勿吉族称及含义、地理分布及考古学文化、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学术界的研究历程。
一、我国历史文献所见勿吉综述
勿吉之名始见于北魏,大致在隋代消失于历史文献之中。我国历史文献中对勿吉系统记述的只有《魏书·勿吉传》和《北史·勿吉传》。
《魏书》卷一百专设《勿吉传》,对勿吉的历史面貌进行了系统记述,主要涉及勿吉的风土人情及朝贡中原王朝的历史:“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似形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醎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酝酒,饮能至醉。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皇’,有虎豹罴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迳山者,皆以物盛。”随后还记述了北魏延兴、太和、景明、兴和年间勿吉多次遣使朝贡北魏的相关史实。
《北史》是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对北朝历史的删减和汇编《魏书》《北齐书》《周书》而成的纪传体通史。全书记述了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年)到隋义宁二年(618年)的历史,涉及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朝二百三十三年的史事。《北史·勿吉传》内容与《魏书·勿吉传》相似,唯记载了勿吉七部的相关情况。然而,今人多认为李延年对勿吉七部的记述是将《隋书·靺鞨传》对靺鞨的记述移植到勿吉身上,只是将“靺鞨”换做“勿吉”,并云勿吉“一曰靺鞨”。[1]
此外,在唐代杜佑的《通典·边防》以及成书于宋代的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四夷》、李昉的《太平御览·四夷部》等历史文献中亦有对勿吉的相关记载。综观诸史记述,其内容无外乎是对《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两部正史的整理和传抄,并无关于勿吉的新材料。由此可见,《魏书》和《北史》无疑是今人了解和研究勿吉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考》是后世典志体史书中对勿吉记载较为详尽的一部,对勿吉及其七部的地理分布、风土人情、朝贡北魏以及隋唐时期靺鞨特别是黑水靺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皆有较详细记载。马端临依据《北史·勿吉传》《隋书·靺鞨传》、新旧《唐书·靺鞨传》等前人文献,明确将勿吉、靺鞨的历史融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作者对勿吉与靺鞨关系的认识。明代史学家王圻撰写的《续文献通考》、清代张廷玉等奉敕修撰的《清朝文献通考》等历史文献也同样将勿吉和靺鞨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可见,前代学者对勿吉与靺鞨(靺羯)的关系在历史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述,二者前后相继并非今人发现和创造,所以目前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一些争论毫无意义,我们应在尊重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而不应盲目创新。
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对勿吉朝贡中原王朝进行了详细记录,结合《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文献通考》等历史文献,据笔者对史料进行爬梳和统计,自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至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勿吉朝贡中原王朝共计29次,其中朝贡北魏22次,朝贡东魏6次,朝贡北齐1次(见表1)。
与勿吉族称相关的还有沃沮、兀惹、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等民族、部落或氏族的名称。这些称谓在历史文献中也有些许记载。
沃沮族在西汉时期即已形成,大致分布在今图们江流域。历史文献中有“东沃沮”“北沃沮”“南沃沮”等称谓,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对此作了很好的辨析和考证。关于沃沮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东沃沮》和《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这两部文献分别对沃沮的地理分布、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中原王朝郡县制管辖情况进行了记载,特别是对曹魏毋丘俭讨伐高句丽致“句丽王宫奔沃沮”一事记载较为详尽。
“兀惹”又称乌舍、乌惹等,其名称始见于《辽史》。《辽史·景宗纪》:保宁七年(975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抟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可知兀惹城邻近辽代黄龙府。《辽史·奚和朔奴传》:“(统和)十三年秋,迁都部署,伐兀惹。驻于铁骊,秣马数月,进至兀惹城。”同书《地理志》又载:“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宋史·渤海国传》则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赐乌舍城浮瑜琰府王诏”。这里的“乌舍城”应即为《辽史》之“兀惹城”,“浮瑜琰府王”则为领导渤海反辽的燕颇。《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又东北六百里至乌惹国”之语。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的《中州集》亦云:“本出辽东乌惹族国,迁之隆安神黄县。”《辽史·百官志》:“迭剌葛部兀惹部亦曰乌惹部。”这里的“乌惹”亦是“兀惹”的同音异写。
“兀惹”又作嗢热、兀的改、乌底改、斡拙、吾者、如者等,《金史》等正史文献对其略有记述,该书《太祖纪》载:太祖二年(1116年)十一月“仆虺等攻宾州,拔之。兀惹雏鹘室来降。”同书《地理志》:“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同书《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洪皓《松漠纪闻》还记载了一个叫“嗢热”的小国:“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契丹徙置黄龙府南百余,曰宾州。”上述文献中的“兀的改”“乌底改”“嗢热”均是“兀惹”的同音异写。除以上文献外,《钦定满洲源流考》《吉林通志》等地方志书,以及明代一些文人著作笔记如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方孔炤的《全辽略记》、何乔远的《明山藏》、雷礼的《皇明大政纪》、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陆应阳的《广舆记》等均有关于上述“兀惹”系列族称的只言片语,多是在论述北方民族相关史实时对其有所提及。
“兀者”是“兀惹”又一称谓,“兀者”在明史文献中记载较多。据《明太宗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历史文献记载,明朝前期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兀者卫、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兀者前卫、兀者后卫、兀者揆野木千户所等一系列卫所行政机构。其行政建置名称应源自“兀惹”族称。

表1

朝代 皇帝 朝贡次序 时间参考文献《魏书·勿吉传》 《北史·勿吉传》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文献通考·四裔考》18 熙平二年正月孝明熙平二年正月,勿吉国、地伏罗、罽宾国。孝明帝元诩19 熙平二年 是年(熙平二年),勿吉国贡楛矢。20 神龟元年二月神龟元年二月,……勿吉……诸国。21 神龟元年八月(神龟元年)八月,勿吉国并遣使朝贡。22 神龟二年六月(神龟二年)六月,高昌国,勿吉国。23 天平三年(天平)三年,高丽、勿吉并遣使朝贡。24 兴和二年兴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不绝。兴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兴和)二年,蠕蠕国、高丽、勿吉并遣使朝贡。延兴(应为兴和,笔者按)二年六月,遣使贡方物。25 兴和三年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三年,蠕蠕、高丽、勿吉并遣使朝贡。东魏26 武定二年 (武定)二年,……勿吉并遣使朝贡。27 武定四年(武定)四年,……勿吉……并遣使朝贡。28 武定五年 (武定)五年,……勿吉并遣使朝贡。北齐灵炀帝(后主)高纬29 武平三年 以至于齐,朝贡不绝。(武平)三年,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至齐朝贡不绝。
“窝集”为吉林、黑龙江一带当地人对原始森林的称呼,为满语“森林”之意。明清时期则有“窝集部”,这一名称很可能源自其作为森林民族的特性。如《清太祖实录》云:“上命巴图鲁率亦都率兵千人,往东海窝集部之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招其路长……”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对“窝集”记载较多,并指出“沃沮者应即今之窝集”。清代文人笔记中也有对“窝集”的记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二》:“(齐某之子)得父骨,以箧负归。归途于窝集遇三盗,急弃其资斧,负箧奔。”汪洋的《渡叶森河桥》:“贫儿拾芥归窝集,宿鸟冲寒入太清。”上述笔记文献所云之“窝集”均为森林之意。
二、勿吉族称谓与民族源流
勿吉作为一个民族称谓,与东北地区众多古代少数民族族称一样,是汉字对其族称的一种标音。在其称谓及其民族指代的问题上,张云樵认为勿吉是肃慎、挹娄的后裔,原是肃慎族系中一支的自称,因勿吉在肃慎诸支系民族中势力最强,遂逐渐成为中原对肃慎族系各支的泛称。[2]程尼娜认为,“勿吉”是拓跋鲜卑对其之称呼,是他称。[3]梁玉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勿吉这一民族称谓的指代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广义的勿吉是指南北朝时期由勿吉之名代称的整个肃慎族系;狭义的勿吉则是指肃慎族系中一个民族或部族,南北朝时期勿吉应为七部之一,由于泊咄部为后来莫颉府所在地,勿吉发音又与拂涅部接近,因此泊咄、拂涅两部可能为狭义之勿吉。[4]
关于勿吉族称含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其著作《东北通史》一书中做了如下阐述:“今满洲语谓‘林木丛杂地多沮洳之地曰窝集,亦曰沃沮’,三国魏志东夷传有东沃沮南沃沮北沃沮之异,肃慎挹娄之地,在北沃沮,故又去肃慎挹娄之旧名,而称勿吉。”[5]据此可知,金毓黻认为勿吉来源于“窝集”,为山林、大森林之意。金先生此说可谓奠定了勿吉为森林之意的基石,后世学者多从此说,今日仍是学术界主流观点。
傅朗云、杨旸先生认为:“秦以前的居就,秦汉时期的夫租、沃沮,都源于诸稽,即勿吉。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等民族、部落或氏族的名称都与勿吉有关。近人考证:‘乌稽、窝集、渥集,皆沃沮一声之转’,‘或即森林民族之称’。如前所述,勿吉源于诸稽,即森林,东北人叫‘树窝子’。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地区,原始森林既是古代人类的好住所,也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好场所。”[6]张云樵以为勿吉族称的含义与辽金“吾的改”、明代“兀狄哈”、清代“窝集克”“吴德盖”一样,皆与森林有关。[2]佟冬认为,勿吉是通古斯女真语“丛林”的意思,以其地多山林而得名。[7]蒋秀松、朱在宪合著《东北民族史纲》,[8]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9]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等著作均依据文献记载认为勿吉即“沃沮”,由地多林木及水泽而得名。[10]赵展认为北魏政权开创者发迹于大兴安岭丛林中,称久居东部山区的社会群体为“勿吉”,即“weji de tere niyalma”(住在森林的人)的略称,表示“森林人”之意。[11]
虽然森林说是勿吉族称含义的主流观点,但仍有学者提出与此不同的观点。笔者按照众家之说出现时间的先后归纳如下:
其一,傉鸡说。林树山依据《晋书·肃慎传》中“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的记载,考证“傉鸡”不可能是朝贡之物,应是当时肃慎王的名字,而且也是肃慎氏族之名,而“傉鸡”与“勿吉”正是真正的一音之转。[12]但笔者以为,“傉鸡”也可能是与“锦罽”“绵帛”并称的贡物之名,且定非普通鸡一类动物。因此“傉鸡”一词究竟系人名抑或朝贡物名,还尚难确证。
其二,东夷诸稽古族说。张国庆认为勿吉之名源于今徐州地区古代民族诸稽,该民族后北迁至东北地区。汉代居就县即是诸稽北迁后的聚居地,勿吉即诸稽(居就)的同音异写。[12]孙进己、冯永谦等先生考证,汉代居就县隶属于辽东郡管辖,其地望可能在辽阳东南约九十里的汤河东岸亮甲山村汉代古城。[13]经过数十年考古发掘,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松花江上游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批很可能属于勿吉—靺鞨的古族遗存,且根据文献记载,勿吉的活动方向是自北向南移动,如果此时勿吉祖先尚在今辽阳一代,那么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发现的大批汉魏时期古族遗存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盲目套用古族称谓“同音异写”方法的结果。
其三,江人说。张博泉认为勿吉并非肃慎—满语系语言,而是东胡系民族语言,为“江人”“江民”之意。[14]勿吉作为肃慎族系的重要一环,其族称若为东胡族系语言,恐难以令人信服。
其四,猪说。喻权中、麻晓燕从勿吉人“好养豕”的生活习惯和原始人猪灵崇拜等神话学角度认为勿吉为女真语“兀甲”的转音,为“猪”之意。[15]这种仅仅依靠神话的推断,显然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臆断。且“好养豕”习惯广泛存在于东北古代民族之中,亦不能因此判定勿吉为“猪”之意。
其五,东夷族系说。这一观点为近年李德山提出,他认为勿吉是东夷族群中貊族和羊族的合体:“勿吉,也即靺鞨,原本系‘貊羯’一词的转写;而其含义,同前论的夫余、高句丽及真番等一样,是两个族名的合称,表示构成这一人类共同体的主体人群,来自东夷族系的貊族和羊族。貊族主要以游猎为生;羊族主要以游牧为生,两族中的部分族民混居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勿吉族。”[16]李德山提出了著名的“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认为东北古族与东夷民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风俗习惯上均可看出,东北古族是东夷部落的一支北上并逐渐定居下来。[17]该观点集中见于《东北古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一书。[18]笔者以为,勿吉、靺鞨等古族称谓应是一种汉字标音符号,从汉字的选取上可能渗透了中原士人对东北古族的轻蔑态度,但不能仅就其字形去论证东北古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这也更加难以解释勿吉(即“貊羯”)是以游猎为主的貊族和以游牧为主的羊族混合后形成的新民族。
其六,张广才岭说。都兴智认为勿吉民族称谓与马纪岭有关,马纪岭是张广才岭的古称,这一带是古勿吉族的聚居地,其族称源自于附近山岭名称。[18]东北许多古族称谓皆源自于山脉、河流等地理事物,因此此说有其合理性。
其七,活祖族称说。尹郁山认为“勿吉”一词源出“活祖”族名的代称和谐同音转写,是北魏时期勿吉大酋长乙力支内服于中原王朝时的自称。因此有关勿吉源于“窝集”,满语译为“林中人”的解释有误。[19]
在上述观点中,“傉鸡”“诸稽”“活祖”虽可作为勿吉族称含义的一种解释,但笔者以为,“傉鸡”“诸稽”“活祖”似乎是中原士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汉字标音,其族称来源和含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勿吉的族源问题,由于东北古代各民族并非各自隔绝、互不交往,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因此,勿吉的族源问题较为复杂。傅朗云、杨旸认为勿吉人原在松花江流域定居,一度加入了挹娄族。勿吉强大后取代挹娄族,名誉中原。勿吉还与室韦有同源关系。[6]言外之意,勿吉与挹娄是同时存在的两个部族,勿吉曾被挹娄统治,后逐渐独立,征服挹娄。张国庆详细考述后指出:“(勿吉)初称‘诸稽’。诸稽原居住今江苏徐州地区的大彭部落。殷商时期,诸稽沿海岸北上,在山东诸城一带有过停留,后迁徙至辽东地区。然后沿鸭绿江北上,入今吉林省松花江流域定居。诸稽又称居就,秦汉时又名夫租、沃沮等。南北朝初期灭挹娄后,才以勿吉之名见于史书。勿吉人的祖先北迁时在辽东停留时间虽很短,但族名对地名产生了影响。如汉代辽东郡居就县,就曾是诸稽(居就)人居住过的地方。居就县名即取于诸稽(居就)族名。居就县遗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东南九十里亮甲村汤河东岸。”[12]李德山等认为勿吉源自东夷族系中的貊族和羊族。[16]梁玉多考证了勿吉的多民族来源,分别为秽貊族系的夫余、沃沮、豆莫娄。[4]
学术界普遍认为,勿吉在隋唐时期改称靺鞨。清代大学士阿桂奉乾隆皇帝旨意编修《满洲源流考》一书,作为一部民族史专著,作者在论述满洲族源时这样阐述勿吉的民族发展:“按勿吉始见于北魏,亦谓之靺鞨,故《魏书》为勿吉传,《隋书》为靺鞨传,而《北史》云勿吉一名靺鞨,其事实为一国,盖南北音殊译对互异,并不得谓一国而二名也。第自唐武德以前则勿吉与靺鞨互称,武德以后则黑水一部独强,分为十六部,始专称靺鞨。而粟末部自万岁通天以后改称震国,又称渤海,无复目为勿吉者亦。”赵展引唐代杜佑所撰《通典》“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一语,认为勿吉与靺鞨发音接近。而《通典》将《北齐书》所载之“靺羯”改为“靺鞨”,可能是出于“靺羯”称呼不雅的缘故。[11]孙进己认为:“靺鞨(勿吉)的原意是指秽貊的一部,以后才作为东北各部的统称,包括肃慎系在内。事实上,在唐代靺鞨这一泛称下,不仅包括秽貊、肃慎两系,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族系。”[20]刘佳男将1635年皇太极宣布更族名为“满洲”这一事件作为满足共同体正式形成的标志,并将其起源追溯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系。[21]
范恩实与乔梁是近年在勿吉与靺鞨关系研究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学者。范恩实根据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有关前近代族群的“族类—族团”理论分析,勿吉与靺鞨并不是简单的顺承关系,前者是族团概念,指称公元475年入贡北魏的一支政治势力;后者则是族类概念,囊括了拥有类似文化特征但未经政治整合,因而也不具有内部群体意识的一系列人群。从时空线索判断,勿吉只是靺鞨之一——粟末靺鞨。[22]乔梁则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勿吉之名自北魏出现后可能一直沿用到北朝较晚阶段,尽管对于北齐、北周一些活动的记述出现了靺鞨之名,但可能更多的是反映隋唐时期的认知,所以《北史》所撰仍是《勿吉传》。其二,北朝阶段中原王朝对于勿吉的了解比较有限,《魏书》虽然为勿吉设传,但除去朝贡使臣所述外,大多是一些传闻或猎奇。而《北史·勿吉传》的相关记述可能更多体现的是隋代靺鞨的状况,并非北朝时期勿吉的真实情况。其三,勿吉在取夫余故地之前已具相当实力,并与高句丽有所接触或冲突,所以两者间可能并非完全由夫余相隔绝。其四,关于勿吉和靺鞨承转延续关系的认识即使按照传统的官方文献,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因此还需慎重对待。[23]
关于勿吉族称与沃沮、靺羯、兀惹、兀者等一系列东北古代民族称谓的关系方面,由于其发音接近,学者们对其研究在清代即已开始。清代地理学家何秋涛在《艮维窝集考》中认为“窝集”义为森林,“盖其人散居窝集之中,即以为部落名也。至古人以此为国,尚不止沃沮一国;如元魏之勿吉国,隋唐之靺鞨国,唐之拂涅部,辽之屋惹国,皆即‘窝集’二字,译写各异;其以老林为窝集而因以名国,则数千年未有改也。”凌纯声先生认为,“汉魏时代的沃沮、挹娄、夫余,隋唐时代的勿吉、靺鞨,明代的兀者,清代的渥集,都是同名异译,或相互转音。”[24]金毓黻先生认为勿吉、沃沮均源自土著语言对森林的称呼“窝集”。傅朗云、杨旸先生不仅认为沃沮源于勿吉,隋唐以后的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等称谓也都与勿吉有关。贾敬颜先生亦认为,“乌若,又作兀惹、乌舍、嗢热等,《五代史》作兀儿,金、元、明人称兀的改、乌底改、斡者、兀者、乌者、斡拙等,或于名后加‘野人’两字,与所谓野人女真为同义语。”[25]这即是说,沃沮、乌惹、兀的改、斡拙、吾者、如者、乌稽、窝集等民族称谓群均是勿吉的同音异写。至于勿吉与靺羯的关系,“靺鞨”首见于《北齐书·武帝纪》:“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靺鞨在这里被写作“靺羯”。关于“靺鞨”与“靺羯”的问题,学术界已有定论,无论历史文献记载,还是旅顺唐鸿胪井刻石、日本仙台多贺城碑、蒙古土拉河流域仆固乙突墓志铭等碑刻的相关内容,均说明“靺鞨”与“靺羯”实为一个民族的不同称谓,勿吉与靺鞨(靺羯)则是同一族称的同音异写。
三、勿吉的地理分布及考古学文化
有关勿吉的地望,《魏书·勿吉传》记述:“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这段文献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勿吉族地理分布极为重要的文献。
民国年间,傅斯年、冯家升等学者对此问题均有论述。傅斯年《东北史纲》云:“《满洲原流考》以为兴京(今辽宁新宾县)亦是肃慎之一地者,乃误以后来勿吉之范围逆论挹娄,且《满洲原流考》是清代官书,清代认肃慎为其远祖,故不免为之夸大。”傅先生将新宾县置于勿吉的地理分布范围内无疑是错误的,根据今人研究可知,勿吉南界至远不过吉林市一带。冯家升先生在《豆莫娄国考》一文中认为:“勿吉之根据地,……以今哈尔滨附近最相当。”[26]此“根据地”不论是作发源地解释,还是作地理分布中心之意,均不正确。时至今日,对勿吉地理分布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其“根据地”当在三江平原。而后又在《述肃慎系之民族》中论述道:勿吉于“元魏时,部族蛰伏于今瑚尔哈流域;其后并肃慎,逐夫余,部族繁滋,土地张大。”[27]此说将勿吉定位于瑚尔哈流域,即今牡丹江流域,这无疑是正确的。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学者们又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杨保隆认为,文献中所载之“速末水”为第二松花江中下游。勿吉地域有前期和中后期的差异,在勿吉驱逐夫余人之前,其西南部边至与挹娄时期大致相同,约北起哈尔滨市附近,南到敦化一线,未达于今吉林市一带的松花江地区,其地理分布的中心在牡丹江流域。北魏太和年间,即勿吉逐夫余之后,勿吉西南边至才逐渐扩展至今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一带。[28]干志耿、孙秀仁认为勿吉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29]张云樵认为勿吉地域南达长白山,东极日本海,西越过今第二松花江,北抵今嫩江东流段、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此时的勿吉地域,在挹娄基础上已有所扩展,越过了张广才岭,占据夫余大片土地,其中心区域已至今吉林第二松花江流域。[2]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认为勿吉所辖地域,南至长白山,与高句丽相接;西至太沵河,即洮儿河,与室韦为邻;东达日本海;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10]魏存成考证勿吉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主流松花江流域。[30]范忠泽认为,勿吉的地理位置应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即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31]范恩实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认为北魏延兴五年(475年)首次朝贡的勿吉分布在东流松花江中游地区,到正始(504-508年)中,勿吉势力已经逆北流松花江而上扩张到原夫余统治核心所在的北流松花江中游地区了。[1]
笔者综合以上观点认为,对勿吉地理分布的研讨应对其南下前和南下后分别论处。其早期居地与挹娄地域大致相合,北魏年间南下夫余地,其地域向南及西南有所扩大,占据北沃沮、夫余旧地及部分秽貊人分布的部分地区。
在上述勿吉地理分布区发现了不少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勿吉—靺鞨族遗存,代表性遗存有黑龙江蜿蜒河类型遗址、双鸭山滚兔岭遗址、以友谊县凤林古城为代表的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绥滨同仁遗址、东宁团结遗址、萝北团结砖厂墓地等。
1974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对鹤岗市绥滨县蜿蜒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蜿蜒河类型因此而得名。这次考古发掘成果的报告《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由杨虎执笔,发表于《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据此考古报告可知,蜿蜒河遗址发掘面积共计203平方米,遗址以房址为主,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F1房址同于同仁文化二期类型,其年代相当于中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F2房址为典型的蜿蜒河类型。F2房址为半地穴式,出土喇叭口球腹罐、青铜饰牌等文物,其年代与俄罗斯波尔采文化相近,大致相当于中原两汉时期。从遗址地层及年代上可知两处房址有前后继承关系,应为挹娄、勿吉、靺鞨的考古学遗存。[32]由于蜿蜒河类型与俄罗斯波尔采文化面貌接近,因此也将其二者合称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双鸭山市发掘了滚兔岭遗址。滚兔岭遗址位于双鸭山市与集贤县交界的滚兔岭上,安邦河在遗址东侧缓缓流过。滚兔岭遗址是黑龙江东北部三江平原西南部聚落遗址群中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据发掘报告可知,滚兔岭发掘面积达1 500平方米,清理方形半地穴式房址14座,分大、中、小三种规格。房址底面经过加工,十分坚硬。有些房址沿四壁下部发现有排列密集的小柱洞和沟槽,可知房屋曾立有木柱或木板。房址中部有火灶遗迹。房址多数未见门道。发掘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均为手制夹砂陶,以褐色为主,红衣陶次之。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锯齿状附加堆纹、凹弦纹、凸弦纹等。器形均为平底器,有瓮、罐、壶、碗、钵、杯等,在一些罐和杯的颈腹部之间安有一斜向上翘的角状把手。石器中有穿孔刀、镞、刮削器、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还有环、管饰等装饰品。还有刀、镞、凿等铁器,还见甲片、扣环等遗物。发掘成果与研究主要见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33]贾伟明、魏国忠最先详细论证了滚兔岭遗址的内涵,他们通过研究挹娄邻族的地理分布,逐步圈定挹娄的活动地域,进而与考古遗存相结合,指出滚兔岭文化应是挹娄人的遗存。[34]黄星坤从时间上、地望上分析了滚兔岭文化的族属,应为挹娄系,该文化上溯肃慎,下及勿吉。[35]王乐文赞同滚兔岭文化为挹娄遗存,但他以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与滚兔岭文化陶器等文化特征差异显著,应是南北并存的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此蜿蜒河—波尔采文化恐并非挹娄文化,而应是靺鞨先世文化遗存。[36]言外之意,他认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可能是勿吉遗存。
魏晋时期,滚兔岭文化中心由安邦河流域转移至七星河流域,形成了新的凤林文化。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这次考古计划力求以重建七星河流域汉魏文明为最终学术目标,对友谊县凤林城址、宝清县炮台山城址、双鸭山保安2号(畜牧队)城址等重点城址进行了发掘。通过数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课题组最终形成大型报告《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37]报告刊布了在七星河流域己调查发现的426处遗址,其年代范围为两汉至魏晋时期,书中除介绍了该区域的自然地理和考古工作状况外,重点介绍了各遗址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分布范围、时代、功能、保存现状及所暴露的遗迹、遗物等情况。对了解三江平原地区汉魏时期古遗址的分布状况、文化发展和人类活动等,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解决古代遗址的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记载,可知七星河流域在考古学年代上早期为两汉时期的滚兔岭文化,晚期为魏晋时期的凤林文化。七星河流域共发现汉魏遗址426处,其中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呈现集群分布,并有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之分。[38-40]凡此种种皆表明,当时的七星河流域聚落群已进入复杂社会,形成了国家机器的雏形,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处在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
在凤林文化及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遗址群族属的研究上,学术界力求实现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学研究的对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应主要为挹娄遗存,但也有其他观点,如勿吉说;挹娄、勿吉与北夫余、豆莫娄杂处说等。黄星坤考证了挹娄地理分布的四至,即东过乌苏里江至鞑靼海峡,南到佳木斯市桦南县的倭肯河流域,西至牡丹江,北达黑龙江。双鸭山市友谊县汉魏遗址群从地望上看可知是在挹娄四至范围内,因此其应属于挹娄、勿吉文化遗存。[41]他在论证凤林文化内涵及其所体现的早期国家萌芽的基础上,认为凤林城址应是汉魏时期挹娄—勿吉王城之所在。[35]马全占将凤林古城晚期所反映的文化定义为挹娄文化,从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居住形式、经济生活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六个方面论证了挹娄文化的特征,并认为凤林古城既是王城,也是满族祖先——挹娄和勿吉的居住地。[42]魏存成对蜿蜒河类型、团结文化、滚兔岭文化、凤林文化等内涵予以阐述,认为上述考古学文化聚落、山城的形制与《魏书·勿吉传》所记勿吉“筑城穴居”的习俗相符合,应属于挹娄、勿吉遗存。但由于上述诸文化面貌既有相同因素,又有不同因素,说明勿吉南迁前就已存在不同的部落或群体。勿吉南下后逐渐衍变为靺鞨,分布在吉林第二松花江流域永吉杨屯、榆树老河深、永吉查里巴墓群便反映了勿吉南下后该族群的文化面貌。[30]尹郁山认为凤林遗址的主人先是挹娄人,后是勿吉人。[19]王乐文认为,以友谊县凤林城址命名的凤林文化,是滚兔岭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同时又明显包含了南部团结文化的因素。他以凤林文化分布之七星河流域与勿吉地理分布中心区域吻合、考古发现房址及所反映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文献记载相合、凤林文化由滚兔岭文化发展而来与挹娄和勿吉关系一致、凤林文化中包含团结文化因素与沃沮北上的历史有关等为据,推定凤林文化的族属应为勿吉。进而指出,文献中的勿吉在早期是南区文化系统(凤林文化)先民,晚期却是北区文化系统(河口四期类型、同仁一期文化等)先民,而作为凤林文化创造者的早期勿吉则可能是被来自北方的“勿吉”(实际是后来的靺鞨)所灭。[36]刘晓东认为凤林文化年代为魏晋时期,相当于勿吉—靺鞨文化的勿吉早期阶段。[43]乔梁认为凤林文化与目前所知明确的靺鞨文化基本不具备直接的演进关系,尚无法将凤林文化认同为勿吉的考古学文化。就基本内涵而言,蜿蜒河或波尔采文化与滚兔岭或凤林文化并非谱系相同的直系亲缘关系,因此无法证明蜿蜒河类型或波尔采文化是由所谓挹娄发展而形成的勿吉。在现有考古学知识的框架中,恐怕只能得到如果文献记载的靺鞨确实是由勿吉演化形成的话,那么蜿蜒河类型或波尔采文化作为靺鞨考古学文化的来源或来源之一,确实是探索勿吉考古学文化的最明确对象。[23]王禹浪则认为滚兔岭文化晚期、凤林文化晚期、炮台山文化晚期均已进入勿吉阶段,应是勿吉人的考古学遗存。[44]
同仁遗址位于绥滨县福兴乡北5公里处、同仁村北侧黑龙江右岸阶地上。1972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将其分为同仁一、二期。同仁一期相当于南北朝至唐初,二期遗址相当于五代至辽,为一处居住址,有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铁器等文物。同仁类型中的代表性器物为盘口鼓腹罐、口下饰附加堆纹的高领鼓腹罐等器物,它与渤海早、晚期的陶器有着明显的渊源演变关系,对研究渤海主体民族的族源与文化源流有着特殊意义,对探讨黑龙江地区考古文化序列有着重要价值。成果主要为《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发掘报告》。[45]张泰湘对绥滨同仁文化进行了深入论证,他指出同仁文化遗址从陶器器形上看,应为蜿蜒河的继承类型,石器中有压制石器和磨制石器,铁器已较为普遍。同仁F3的年代是距今1 420±80年,这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F2距今约1 200年左右。根据其年代和分布地域,应为隋唐时期勿吉—靺鞨的考古文化遗存。同仁文化的分布地域已远远超过了海青类型(乌里尔文化)、蜿蜒河类型(波尔采文化)的分布范围,往东北延伸到黑龙江下游(萨卡奇—阿梁村),西北至结雅河,甚至已达呼玛县境,西边则越过了张广才岭,抵达哈尔滨一带,往南已至绥芬河流域和吉林省敦化、吉林市一带。这一时期松嫩平原上属于夫余先世族群的白金宝文化和绥芬河流域属于沃沮的团结文化因素已基本消失,却同时出现了同仁文化的遗存,即勿吉—靺鞨人的地理分布已扩大至上述地区。结合文献可知,这是勿吉—靺鞨人对外扩张的结果。[46]黑龙江东宁团结遗址,位于东宁县西南约14公里处大肚川乡团结村,坐落在大肚川河右岸的阶地上。团结遗址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原始社会晚期,经发掘又可分为一、二两期,同时还发现早期和晚期的房址、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存在着叠压打破关系。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居址,居址内出土有高圈足浅盘豆、双柱耳筒形罐、敞口碗等。灰坑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区和北区,在上层渤海时期的灰坑中出土有刻花骨雕牌饰、唐三彩残片、铁提梁、铁镞、铁刀、筒瓦、板瓦、铜扣、玉带饰、牙饰等文物。萝北团结砖厂墓地是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铁器时代墓地,位于萝北县东南10公里团结乡团结砖厂西部的椭圆形沙岗上,在1982年砖厂烧砖取土时被发现,经合江地区文物管理站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出土文物近100件。团结砖厂墓地随葬陶器的风格,与绥滨同仁遗址下层出土的同类陶器基本一致,可归属为年代相近的同一文化类型。从出土的鼓腹罐、铁矛等以及合葬式特点分析,团结砖厂墓地应属勿吉—靺鞨的遗存。发掘成果见于《黑龙江省萝北团结墓葬清理简报》《黑龙江省萝北县团结墓葬发掘》。[47-48]黑龙江流域的其他相关遗迹还有哈尔滨黄家崴子,成果见于《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考古调查收获》;[49]宾县老山头,相关成果为《黑龙江宾县老山头遗址试掘简报》;[50]望奎厢兰头,发掘成果见于《呼兰河中游考古调查简报》;[51]海林河口四期、振兴四期,见考古专著《河口与振兴》;[52]海林渡口二期,成果为《黑龙江海林市渡口遗址的发掘》。[53]除此之外,干志耿、孙秀仁合著《黑龙江区域考古学》还将绥滨四十连、哈尔滨黄山南北城址、呼兰河左岸八方前、通江、桦川长发屯、逊克西砬子等遗址列入勿吉—靺鞨考古学遗存。[29]
随着勿吉族逆松花江南下,由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迁徙至今松花江上游一带,并灭亡了曾强盛一时的夫余国。勿吉族的到来使这里遗留下了一批丰富的考古学遗存,引发学术界关于勿吉考古学遗存热烈探讨的代遗存主要有永吉杨屯三期、永吉查里巴、榆树老河深、舒兰黄鱼圈等。
1971年,永吉县乌拉公社杨屯大队社员在村南挖土造肥时发现了杨屯遗址,吉林省博物馆遂于同年8月和10月,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1979年和1980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陶器、铁器、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遗物。编号为79M17号墓葬中还发现一枚“开元通宝”,说明该遗址年代已晚至唐代。学界一般认为,吉林永吉杨屯三期为勿吉—靺鞨遗存,其发掘和研究成果主要见于《永吉杨屯遗址试掘简报》《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等。[54-56]1980-198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发现并清理了一批墓葬,共计发掘墓葬37座,其中石棺墓7座、木棺墓6座、土坑墓23座,有火葬、二次葬等葬俗。出土了陶罐、陶碗、铁器、银器、石器、玉器、玛瑙珠、琉璃珠等大批珍贵文物,其中以铁器数量最多,还出土了铅块两个。榆树老河深的考古发掘成果详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专著《榆树老河深》。[57]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早有学者关注,1985年发表的《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认为老河深墓地应为鲜卑遗存。[58]随后,刘景文等撰文专门探讨了老河深的族属,认为应是夫余族的部分遗存。[59]关于老河深墓地的年代,其主体主要是东汉时期,有学者指出,其文化上层已晚至北朝至唐代,[60]因此推断其为勿吉遗存。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于1960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0年和1981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取了一批考古学材料,发表了《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认为黄鱼圈珠山遗址以侈口重唇的深腹罐和种类繁多、富于变化的纹饰陶为代表的文化面貌应是靺鞨—渤海早期遗存。[61]1987-1988 年,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清理墓葬45座,出土随葬品500余件。随葬品中数量较多的是装饰品、兵器和马具,陶器较少。其中多件为一组的青铜牌饰较为引人注目。遗址M27还出土了一枚唐开元通宝,据此推断此墓地的年代为隋末唐初至唐中叶。查里巴墓地的发掘研究成果主要见《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发掘报告认为查里巴墓地位于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之畔,应是粟末靺鞨的遗存。[62]
对于上述诸勿吉遗存的研究,学术界多从类型学角度对其文化谱系进行探索。主要成果有金泰顺的《关于渤海陶器的时期划分》、[63]乔梁的《靺鞨陶器分期初探》、[60]孙秉根的《渤海墓葬的类型和分期》、[64]严长录的《论渤海陶器的特征》、[65]刘晓东和胡秀杰合撰的《渤海陶器的分类、分期与传承渊源研究》、[66]郑永振的《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比较研究》[67]和《渤海文化的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68]刘晓东的《靺鞨文化研究》[69]和《靺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70]以及日本学者臼杵勋的《铁器时代的东北亚》[71]等论著。
范恩实综合考察了几乎所有关于勿吉的考古学遗存。他以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有关前近代族群的“族类—族团”理论为指导,对以“靺鞨罐”为典型文化特征的“靺鞨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研究,试图将勿吉考古学遗存从中剥离出来,以实现对“靺鞨考古学文化”的进一步细化。他对我国境内的吉林永吉杨屯三期、吉林永吉查里巴、榆树老河深上层、舒兰黄鱼圈、哈尔滨黄家崴子、绥滨同仁、绥滨四十连、萝北团结、宾县老山头、望奎厢兰头、海林河口四期、振兴四期、海林渡口二期等,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布拉戈斯洛文诺耶Ⅱ、奈费尔德、特罗伊茨基等考古学材料进行梳理,结合文献记载的北朝中晚期勿吉正从第一松花江中游逐步进入夫余故地,从时空线索和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最终认定,典型的勿吉考古遗存应该是榆树老河深上层、永吉杨屯三期。[22]但他在其后出版的《靺鞨兴嬗史研究》一书中论证勿吉考古学文化时只将榆树老河深上层视为北朝中、晚期的勿吉考古学文化,他认为榆树老河深上层和永吉杨屯三期的文化面貌虽整体相似,但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永吉杨屯三期的年代要稍晚于榆树老河深上层,是榆树老河深上层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另外,永吉杨屯三期与永吉查里巴也有颇多相似之处,此两者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1]这反映了他学术思路和观点的变化。
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考古发掘虽揭露了不少珍贵的可能是勿吉古族遗存,但由于年代久远,勿吉地理分布又不断变动,并与同一谱系的挹娄、靺鞨等及同时代的周边民族水乳交融,导致对勿吉考古学遗存的确证较为困难,但应该肯定的是,滚兔岭文化、凤林文化、炮台山文化、绥滨同仁遗址、东宁团结遗址、萝北团结墓地以及吉林永吉杨屯三期、永吉查里巴、榆树老河深、舒兰黄鱼圈等考古学文化和遗存应与勿吉有关。
四、勿吉其他研究与海外研究综述
勿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部落联盟的政体,即著名的勿吉七部,分别为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白山部和黑水部。其中粟末部和黑水部势力较为强大,但由于各自为战而被高句丽征服,直至唐高宗灭亡高句丽后才重新独立和强盛起来。从此勿吉诸部协同作战,进军高句丽,并攻灭了存在八百多年的夫余国。在勿吉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张杰较为详细论述了勿吉与夫余、高句丽的关系及对中原王朝朝贡的历史。[72]杜晶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梳理,较为详细地考述了勿吉与夫余、豆莫娄、高句丽和北魏的民族关系,较全面地反映了勿吉数百年与周邻的战与和。[73]郭威全面论述了勿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74]梁玉多全面考察了勿吉的对外扩张。勿吉在南北朝时期强大后,不断对外扩张,通过占领北沃沮、袭扰高句丽、占领夫余、侵蚀豆莫娄,把疆域从三江平原一隅扩大到几乎占据东北的一半,影响也随之扩大。其攻守举动对东北全局都有影响,成了东北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渤海国之所以能成为“海东盛国”以及女真、满族两次入主中原,建立大金、大清两大帝国王朝,皆肇于此。[75]程尼娜细致梳理了勿吉朝贡中原王朝的历史经过。[3]在其他方面,庄严从经济生产生活、社会结构、婚姻形态、丧葬习俗等多方面对勿吉进行了文化人类学剖析,认为勿吉经济以狩猎为主,有少量农业和牲畜饲养业,尚不会冶铁,已掌握酿酒技术。还未进入复杂社会,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由酋长组织生产生活。婚姻还处于父系大家族阶段。丧葬习俗既保留一定的原始天葬习俗,也已逐渐受汉文化影响而出现土葬。[76]栾凡对包括勿吉在内的肃慎族系诸族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风俗人情等及其特点作了梳理和研究。[77]张杰根据文献记载论述了勿吉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生活,特别阐述了满族先民们对长白山的早期开发。[72]杜晶通过分析《魏书·勿吉传》对勿吉的语言、居住、服饰、婚俗、葬俗进行了研究,认为勿吉语言应为阿尔泰—通古斯语系。[73]陈柏霖对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勿吉“俗以溺洗手面”的记载进行了历史人类学解读,认为尿液是狩猎、游牧民族的洗涤剂,可以用尿液洗手、洗头发甚至洗澡,因为尿液中含有生物碱,具有去掉油污之功效,其洗涤效果胜于清水。尿液还是狩猎、游牧民族的医疗用品,从现代医学看来,尿中含有微量尿素,具有杀菌消炎止痒之功效,这对于长年生活在森林地带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78]梁玉多、辛巍结合古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对勿吉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研究,对“偶耕”的含义及耕作方式、农作物种类、嚼米酿酒技术等进行了深刻论述,全面反映了勿吉民族的农业状况。[79]
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者便已开展了对勿吉的研究。俄罗斯学者研究起步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俄方学者利用地缘之便,在黑龙江流域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发掘了一些可能是勿吉—靺鞨的文化遗存。日本学者则从多角度对勿吉的历史面貌进行研究,一批优秀的研究论著面世,至今仍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18-19世纪,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向远东地区扩张,俄国学者开始对远东地区包括勿吉—靺鞨文化在内的一些古代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如俄国学者Г·Ф·米登多尔弗在其著作《西伯利亚和东部旅行记》中记载了1842年调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南部地区的勿吉—靺鞨遗存的相关资料。这可能是勿吉相关遗存的最早调查和研究成果。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进入苏联时代之后,俄罗斯学者对勿吉—靺鞨的研究日益深入和系统。Л·Я·施天堡、А·Я·古罗夫实地调查了一批古族遗存,其中可能涉及勿吉遗存。Г·С·诺维科夫相继撰写了《濒于绝迹的古代遗存》《伊格纳基耶沃、马尔科沃、叶卡捷里诺夫卡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的考古调查》《古代的阿穆尔边区》等多篇文章。H·H·科兹明在《何为卡马辛人》一文中考辨了靺鞨部落的分布。
从1953年起,远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开始由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主持。1962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北亚(远东)考古考察队接替苏科院考古所列宁格勒分所的主持任务,而实际上所有的发掘工作都是在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的领导下进行的。奥克拉德尼科夫先后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地区发掘了数处靺鞨遗存,重要的有:哈桑湖地区岩杵河口、克拉斯基诺村附近的遗址,阿努钦地区刀毕河右岸、克尔格莱山丘北麓的城址,夹皮沟河岸两座山丘上的两座寺庙遗址,还有距夹皮沟河口不远绥芬河岸、波里索夫卡村附近,发现了渤海寺庙遗址及其附近的居住址等。他发表了《1955年的远东调查》《关于阿穆尔河上游考古遗存的首次报导》等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在远东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综合性著作《滨海边区的遥远过去》,对黑龙江中游关于勿吉—靺鞨遗存的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这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之后,他于1973年出版《苏联远东考古新发现》,概括地叙述了肃慎、勿吉、靺鞨、渤海、女真人等众多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他还有诸多合著,如与捷列维扬科合作的《犹太自治州纳伊费里特村的靺鞨墓地》,①与麦德维捷夫的《关于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西南的两处中世纪墓地》等。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黑龙江中游流域的勿吉—靺鞨遗存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学家杰列维扬科长期参与奥克拉德尼科夫主持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勿吉—靺鞨居住址和墓葬,其中发掘面积最大者为特罗伊茨基墓地,其发掘面积达到1 600余平方米,共发现200余座墓葬,为判定公元4至8世纪靺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位于今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比罗比詹市奈菲尔德镇的奈菲尔德墓地亦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勿吉—靺鞨遗存,共发现41座墓葬,墓穴多为椭圆形或长方形,盛行二次葬,墓内多发现马骨。俄罗斯境内的布拉戈斯洛文诺耶Ⅱ、奈费尔德、特罗伊茨基等均已可认定为靺鞨考古学遗存。关于上述考古学遗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克鲁沙诺夫主编的《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80]杰烈维扬科撰著的《奈费尔德古墓地》、[81]《特罗伊茨基村附近的靺鞨墓地》、③《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④《阿穆尔河中游沿岸地区的中世纪遗存——根据1977调查资料》、⑤《阿穆尔河沿岸的部落》、[82]《苏联亚洲部分的石器和古金属时代》⑥以及她与Я·В·库济明、С·П·涅斯捷罗夫合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早期中世纪遗存的年代学(初步成果)》。⑦
我国学者冯恩学先生在《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83]一书中对俄罗斯学者关于勿吉—靺鞨遗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清晰的梳理。
俄罗斯学者普遍将早期铁器时代之后到女真文化之间的分布于以黑龙江中下游为主的口下有附加堆纹的平底陶罐为特征的遗存看作是靺鞨人的遗物,所以定名为靺鞨文化。但他们对靺鞨文化的内涵、分期、类型等问题尚存在一些争议。以杰列维扬科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米哈伊洛夫卡古城、奈菲尔德遗址、特洛伊茨基墓地等黑龙江上、中、下游及其支流的发达铁器时代早期遗存都是靺鞨文化。安德列耶娃与杰列维扬科共同执笔的《苏联远东史》(1989年版)将靺鞨文化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有库尔库尼哈遗址、奈菲尔德墓地等,时间约在公元4-5世纪;第二阶段有特洛伊茨基墓地、新彼得罗夫卡墓地等,时间初定在6-8世纪,修订后认为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第三阶段以奥西诺湖遗址为代表,年代不详。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涅斯杰罗夫将米哈伊洛夫卡古城认定为室韦文化,缩小了靺鞨文化的分布范围,并将靺鞨文化分为两个并存发展又不同起源的类型——奈菲尔德类型和特洛伊茨基类型。他从陶器、墓葬等多个方面对这两个类型进行了详细比对,认为陶器是两个类型主要差别的体现。奈菲尔德类型的代表性陶器是长颈敞口小鼓肩平底罐,形体较为瘦高,形状似瓶,看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波尔采文化陶罐的风格。特洛伊茨基类型的代表性陶器是平地筒形罐,没有长颈,腹部不鼓或略鼓。从陶器造型上看,特洛伊茨基类型与外贝加尔的布尔霍图伊文化、贝加尔湖沿岸的库鲁姆钦文化、叶尼塞河的黠嘎斯文化陶器类似,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两种类型陶器都出现盘口,冯恩学推测可能与受到中原南北朝时期流行盘口瓷器的影响有关。
日本学者的勿吉研究起步也很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东洋史研究热潮促使了对勿吉的研究。受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委托,致力于“满鲜史”研究的白鸟库吉等人于1913年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以及之后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研究报告》,考证了靺鞨的源流、居住区域等问题。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勿吉—靺鞨研究成果当属津田左右吉的《勿吉考》、⑧池内宏的《铁利考》,[84]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津田左右吉在《勿吉考》中认为勿吉是南北朝时期东北类似部落中的最强者,东魏北齐之际,勿吉衰落并逐渐被粟末靺鞨取代,勿吉族称也衍变为靺鞨。1937年池内宏再创新作《勿吉考》⑨提出靺鞨夫余说。小川裕人的《关于靺鞨史研究诸问题》,[85]综述了靺鞨七部住地分布、族属与高句丽关系等方面内容并提出存在的若干问题。同年,小川裕人又发表《关于铁利的住地》[86]列举了以往研究中对铁利住地的各种比定,并加以批判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学术界在经历了短暂消沉后,学术研究逐渐复苏,又有一批重要的勿吉—靺鞨研究论著面世。
三上次男从民族学的角度,根据使用毒箭和人尿液的习惯,认为挹娄、勿吉、黑水靺鞨都是古亚人种。[87]日野开三郎的《关于靺鞨七部的住域》⑩针对《北史》和《隋书》两书中记载靺鞨七部的住地作了分析论述,把靺鞨部族的不同部落归属为不同的来源,粟末部来自夫余,白山部来自沃沮,拂涅来自挹娄,而安车骨、伯咄两部则来自勿吉。
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与靺鞨民族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力图从考古学资料中寻找靺鞨民族的历史身影。
菊池俊彦的《东北亚的古代文化》[88]从考古学角度系统研究了以北海道地区为中心的古代日本北方与东北亚大陆靺鞨等古族之间的文化关系。菊池俊彦的另一研究论著《靺鞨の同仁文化》[89]详细考察了同仁文化和靺鞨文化的关系。臼杵勋的《靺鞨文化的年代与地域性》[90]以俄罗斯的乃伊费尔德墓地、特罗伊茨基墓地和中国吉林杨屯大海猛墓地出土的陶器为考察对象,分析靺鞨文化各地域的地域性差异,认为这与周边近邻文化影响有关。菊池彻夫的《靺鞨与鄂霍茨克文化》[91]一文根据史料及考古学材料,将挹娄、勿吉、靺鞨的各个文化、经济要素列表进行对比分析,提出鄂霍茨克文化就是以渔猎代替农耕、以养熊代替养猪的靺鞨文化。菊池俊彦的《黑龙江省萝北县的靺鞨遗迹》[92]一文综述了中俄两国在黑龙江两岸以及绥芬河畔的考古发现,综合俄罗斯境内靺鞨遗迹与同仁文化,详细叙述了萝北县团结遗迹,通过器形对比,确认了中俄两国几种考古发现之间的相互关联。萝北团结墓葬中发现了与阿穆尔河北岸靺鞨文化初期的勃拉戈斯洛文诺耶Ⅰ号遗址居住址几乎一样的陶器,其中花瓶形陶器被认为同波尔采文化陶器有关联,由此推测靺鞨—同仁文化的起源在阿穆尔河中游一带。而罐形陶器的分布区域已到松花江中游,可知靺鞨—同仁文化曾向南扩展。
美国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博士《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中收录的《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探索了创造辉煌历史的女真—满族的祖先——勿吉—靺鞨人是当今匈牙利民族的远东祖源。他认为:“我们猜测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亦作‘靺羯’)或‘勿吉’的源音,而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等),以及相当于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93]
综上阐述可知,俄罗斯学者利用与我国接壤的地缘优势在黑龙江流域及滨海地区进行了长期针对勿吉—靺鞨族遗存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成果。日本学者对勿吉的研究则更加立体和全面,对环鄂霍次克海古族考古学文化十分关注,但至今俄日学者均尚无法做到明确将勿吉遗存从广义上的靺鞨考古学遗存识别和剥离出来,仅能通过地层学和C14测年法及地理分布大致考察可能属于勿吉的遗存。美国学者则从族源角度探索了勿吉的民族流向。
勿吉研究是东北古族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其与沃沮、靺鞨、靺羯、兀惹、兀者、窝集等众多民族称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经过中外学界近百年的探索,勿吉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然而,就总体而言,对于勿吉的研究更多是将其置于靺鞨或渤海的研究中“一锅烩”而进行讨论的,鲜有学者将其独立出来单独进行研究,目前也并未见有任何关于勿吉的专著面世。由于勿吉活动范围不断处于变动和扩张之中,又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中,因此对其地理分布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显得困难重重,特别是对其考古学文化的识别可以说是国际性难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应过分强调和依靠考古学材料,对勿吉考古学的研究应与历史文献记载紧密结合起来,考古材料如离开文献佐证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中外学术界尚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文献和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来尽可能地还原和解析勿吉兴嬗的历史脉络。
注释:
①《西伯利亚考古汇编》,新西伯利亚,1966。
②《西伯利亚科学偏通报》1973年第1期。
③《1970年考古发现》,莫斯科。
④E·И·杰列维扬科著,1975。
⑤苏联科学出版社《考古普查—北亚》诺沃西比尔斯克,1980年。
⑥新西伯利亚,1988。
⑦《西伯利亚人文科学》1995年第3期。
⑧《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1915。
⑨《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十五,1937。
⑩《史渊》三六、三七合辑,1947,后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卷十二,三一書房,1989。
[1]范恩实.靺鞨兴嬗史研究——以族群发展、演化为中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2]张云樵.吉林满族的渊源及衍变考略[J].社会科学战线,1992,(2).
[3]程尼娜.汉至唐时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2).
[4]梁玉多.论肃慎族系诸称谓的关系及勿吉的来源[J].满族研究,2010,(3).
[5]金毓黻.东北通史[M].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
[6]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7]佟冬.中国东北史: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8]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9]薛虹,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0]李治亭.东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1]赵展.对肃慎及其后裔的考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12]林树山.肃慎姓氏傉鸡考[J].北方文物,1986,(3).
[12]张国庆.略谈东北地区源于古代少数民族名称的地名[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1).
[13]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4]张博泉.女真新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15]喻权中,麻晓燕.肃慎系统族源神话的历史考察[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1).
[16]李德山,栾凡.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7]李德山.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18]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8]都兴智.略论东北古代族名与山水之名的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01,(1).
[19]尹郁山.友谊凤林、兴隆山、长胜三处汉魏时期遗址足迹考[A].王学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黑龙江历史第一都[C].双鸭山: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
[20]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1]刘佳男.满族共同体起源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22]范恩实.勿吉兴亡史探微[J].北方论丛,2010,(1).
[23]乔梁.关于靺鞨族源的考古学观察与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
[24]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5]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26]冯家升.豆莫娄国考[J].禹贡,1937,(4).
[27]冯家升.述肃慎系之民族[J].禹贡,1935,(7).
[28]杨保隆.勿吉地域西南部边至考[J].北方文物,1985,(4).
[29]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0]魏存成.靺鞨族起源发展的考古学观察[J].史学集刊,2007,(4).
[31]范忠泽.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及对鹤岗地区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09,(3).
[32]杨虎.黑龙江省绥滨县蜿蜒河遗址发掘报告[J].北方文物,2006,(4).
[3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J].北方文物,1997,(4).
[34]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J].北方文物,1989,(3).
[35]黄星坤.浅谈“滚兔岭文化”[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5).
[36]王乐文.挹娄、勿吉、靺鞨三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J].民族研究,2009,(4).
[3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8]许永杰.关于探索黑龙江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J].北方文物,2001,(1).
[39]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A].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0]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J].考古,2000,(11).
[41]黄星坤.友谊县汉魏时期遗址的分布与形制[J].鸡西大学学报,2007,(3).
[42]马全占.挹娄文化挖掘及其利用初探[A].王学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黑龙江历史第一都[C].双鸭山: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
[43]刘晓东.挹娄、靺鞨关系的考古学讨论[J].北方文物,2013,(1).
[44]王禹浪,刘加明.三江平原地域族体考古文化研究综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2).
[4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6,(1).
[46]张泰湘.从最新考古学成就看历史上的肃慎、挹娄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5).
[47]李英魁.黑龙江省萝北团结墓葬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1989,(1).
[48]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萝北县团结墓葬发掘[J].考古,1989,(8).
[49]热列兹涅柯夫,孙秀仁.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考古调查收获[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2).
[50]赵善桐.黑龙江宾县老山头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62,(3).
[51]绥化地区文物管理站.呼兰河中游考古调查简报[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2).
[5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河口与振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5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海林市渡口遗址的发掘[J].考古,1997,(7).
[54]刘振华.永吉杨屯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73,(8).
[55]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J].考古学集刊,1987,(5).
[56]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J].考古学集刊,1991,(8).
[5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8]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长春市文管会,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5,(2).
[59]刘景文,庞志国.吉林榆树老河深墓葬群族属探讨[J].北方文物,1986,(1).
[60]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J].北方文物,1994,(2).
[61]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J].考古,1985,(4).
[6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J].文物,1995,(9).
[63]金泰顺.关于渤海陶器的时期划分[A].方学凤.渤海史研究[C].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
[64]孙秉根.渤海墓葬的类型和分期[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5]严长录.论渤海陶器的特征[A].方学凤.渤海史研究[C].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
[66]刘晓东,胡秀杰.渤海陶器的分类、分期与传承渊源研究[J].北方文物,2003,(1).
[67]郑永振.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比较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
[68]郑永振.渤海文化的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J].东疆学刊,2008,(4).
[69]刘晓东.靺鞨文化研究[D].吉林大学,2007.
[70]刘晓东.靺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2014.
[71]〔日〕臼杵勋.铁器时代的东北亚[M].东京:同成社,2004.
[72]张杰.满族先民与长白山的早期开发[J].满族研究,2006,(3).
[73]杜晶.勿吉的语言习俗及与周边各族的关系[J].东北史地,2008,(6).
[74]郭威.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5).
[75]梁玉多.简析勿吉的对外扩张[J].北方文物,2012,(1).
[76]庄严.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社会性质[J].黑河学刊,1986,(4).
[77]栾凡.肃慎系民族的社会发展及特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3).
[78]陈柏霖.勿吉—靺鞨以溺洗手面之俗的历史人类学解析[J].学习与探索,2011,(6).
[79]梁玉多,辛巍.勿吉的农业及相关问题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2).
[80]〔苏〕克鲁沙诺夫.成于众.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
[81]〔俄〕杰烈维扬科.王德厚.奈费尔德古墓地(上、下)[J].北方文物,2002,(1,2).
[82]〔俄〕杰烈维扬科.林树山,姚凤.黑龙江沿岸的部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83]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
[84]〔日〕池内宏.铁利考: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一册[M].东京:获原星文馆,1943.
[85]〔日〕小川裕人.关于靺鞨史研究诸问题[J].东洋史研究,1937,(5).
[86]〔日〕小川裕人.关于铁利的住地[J].史林,1937,(2).
[87]〔日〕三上次男.论东北亚细亚使用毒箭的习惯[J].民族学研究,1943,(3).
[88]〔日〕菊池俊彦.东北亚的古代文化[M].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5.
[89]〔日〕菊池俊彦.靺鞨的同仁文化[M].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5.
[90]〔日〕臼杵勋.靺鞨文化的年代与地域性[A].岩崎卓也,等.日本和世界考古学[C].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94.
[91]〔日〕菊池彻夫.赵晓丽.马秀红.靺鞨与鄂霍茨克文化[J].北方文物,1992,(2).
[92]〔日〕菊池俊彦.于建华.黑龙江省萝北县的靺鞨遗迹[J].北方文物,1992,(2).
[93]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M].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