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老宅
夏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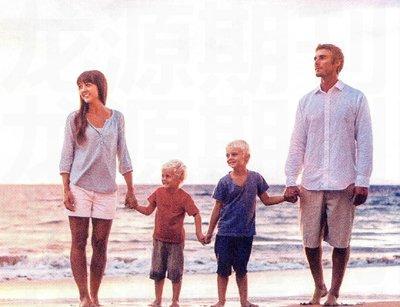
人称有钱难买东南角。故乡老屋位居村子东南第一户。老屋后有庄墩,墩后是庄河,东西又有河,三面界皆有水;前面有长渠,大半年有水。渠边有棵水杉树,树高、枝繁、叶茂,树下长满了如剑的菖蒲;门前还有口小水井,都与水有关。曾有路人说老屋有水环绕,后墩依靠,风水好。且说且听,一笑而已。
祖父去世早,父亲年幼,家产未得分毫。父亲成家时几乎是上无片瓦下无块砖。无奈之下插标为基,无意间选中庄子前面的这片荒芜之地。又凭着年轻体壮,雇亲聘友,用碎砖黄泥块垒起三间草房子。从这算起,老屋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其间三次翻建,直到现在的三堂两厨,砖砌瓦盖,外封水泥,内饰天壁。虽然比不了庄上的别墅小楼,但也算有模有样。
老屋曾经三代同堂,住过祖孙三代七八口老小。那也是人丁最兴旺、住家最集中的时期。但时过境迁,劳燕分飞,后来只有老母亲和腿残的三弟在家撑持门面。
七八年前曾把母亲和三弟接到城里,就近找了个比较宽敞的房子让其相邻而居,便于相互照应。可是仅仅待了半年时间,母亲便感到邻居间相互不往来,不能随意串门拉家常。而且出门要乘车,买菜要花钱,不如老家散漫、省钱、方便。于是他们又回到故乡老屋,依然故我地串门拉呱,依然邻居间摸摸纸牌,依然是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日子反而过得逍遥又自在。
一晃四五年又过去了,村情发生些微变化。年纪较轻的出门打工去了。与母亲年纪相仿的一些老人有的先后离故,有的随子女进镇入城,照顾孙辈颐享天年。曾经数百人的老庄子居然只剩下几十位老弱妇孺。虽然也通电视电话自来水,但毕竟人去村空,白天都人迹寥寥,晚上更是寂如幽谷。
于是动员母亲和三弟还是到城里共住一起,但他们不允,说老屋灵气不能空,有人住才能守住灵气。但是随着母亲年岁的增长,若是有个伤风头疼的总归不太方便。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在镇上寻了个合适的老房子,让他们跟我大妹相邻,这样有个依靠,离老宅又不太远,想回去看看也方便。母亲于是搬到了镇上。临走时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老屋,看着几位相送的老邻居不住地抹泪。
老宅关上了门,庄上又少了两个人。时间一长,门口的水泥砖块缝里长出了青草,檐口下也织上了蜘蛛网,老宅荒芜之态毕现。当初母亲和三弟不肯背井离家,就是怕祖屋生朽,祖宗孤寂,祖地抛荒。如今果然如此。
每每谈及老屋,母亲还会黯然神伤。为此,我们时常安慰母亲,虽然暂别了老屋,但离老屋并不太远,可以常回去看看。况且老屋也不孤单,至少还有桃树、燕子和大花猫这三样宝贝替我们守着老屋呢!知道母亲除了牵挂老屋,也惦记着她心爱的三样宝贝。果然如此,每每提到这“吉祥三宝”,母亲就开心地笑,然后叨咕说不知它们现在怎么样了。
桃树是来得最早的,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母亲三十多岁的时候,在田间忙农活,常在一户叫俞三妈的人家小憩。俞三妈家的田边有棵桃树,桃大,色艳,香甜,口感好。俞三妈人心好,每当桃熟红艳的时候,总会摘上几个又熟又大的桃子塞到母亲的衣兜里。母亲舍不得吃,收工时带回家给我们解馋。后来母亲把这桃核埋在自家东南角的田边上,也想长出棵桃树来。想不到第二年初夏还真的冒出个小桃苗来,两三年后长到一人多高,第四年竟然开花结桃了。
我们兄妹欣喜若狂,早上盯晚上瞅,中午还要看上几眼才上学。等到桃子成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俞三妈家的大,也没有那么红艳那么甜。后来才知道,果树要嫁接,不嫁接就是第二代,品质会退化。嫁接又不懂技术,本想砍掉算了。可母亲舍不得,说既然长了就由它去吧。这一留就是几十年,如今已是干粗枝壮桃叶茂。可能是树大根深养分足了,每年都能结上几十斤的黄红色大桃子,口感也有了明显改观。想不到它愈老愈俏。
来得迟些的是燕子。但在我们家落户也有四十多年了。过去家里没有独立的厨房,主屋西房间的西南角砌了个灶台,在家里做饭又烧菜,烟气熏蒸得房梁乌亮油腻。每年开春燕子飞进屋子转几圈,然后又迅速掉头飞去。父母到外面拾碎砖,起早带晚,用烂泥碎砖垒起个厨房,家里再无烟熏热气蒸。第二年春天,燕子前来探察后果然垒巢安了家,这让我们乐开了花。后来翻建的新房子,又大又亮又清爽,燕子更是青睐有加,年年都来垒巢落户,有一年还做了两个巢,共有七八只燕子来来往往,直到现在还是络绎不绝。
临搬家时,母亲想到人走门上锁,燕子还要进出家门,于是专门找了个长柄老式大铜锁,把门中间隔留下个大空档,以方便燕子出入。如今老屋虽主人不在,燕子倒是守承得很,依然如约来,也算替我们守护着老房子,不致毫无生息空自叹。
来得最迟的是大花猫,才仅仅四五年。母亲感到寂寞无趣,又有老鼠日夜作祟,便想到找个小花猫回来养。想不到这猫长得好看、乖巧、还管用,不仅整天绕着母亲腿脚转,还把嚣张的鼠徒们吓得无踪影。去年搬家前,母亲把大花猫蒙上眼睛送到很远很远的庄子上有炊烟的人家收养它。哪知道过了四五天,大花猫居然又出现在自家门前,还呈现出一副委屈可怜相,母亲心疼又自责。在腊月头上带它走时居然又不走,就蹲在门边猫洞口双目凝视,似乎不解我们究竟为何。母亲只好专门准备些鱼、饭之类放在厨房灶台边,又托邻居王二奶奶帮着照应点。
一晃过了十多天,春節后母亲无论如何要回老屋探望一下大花猫,并带上一些鱼肉类。想不到大花猫从大门口看着来路,大老远就迎上前去,对着母亲“喵喵喵”地叫得欢,绕着母亲不离左右。身子虽然瘦了不少,但眼睛依然还是那么犀利有神韵,还不时闪着泪光,颇似委屈的小孩子。母亲嗫嚅着说:“难为你还这么诚心地守着这老屋呢!”而花猫则越发地绕前跟后,玲珑欢快叫不停,让人心疼又心酸。
我想,花猫终归不会长久下去,但桃树只要不砍,它会一直生长下去;社燕虽然春来秋去,但也依旧会常来常往。燕子和桃树都会继续陪伴老屋度过每一个晨曦和落日,每一个春夏和秋冬。
(摘自《盐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