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智库是怎样形成的
柳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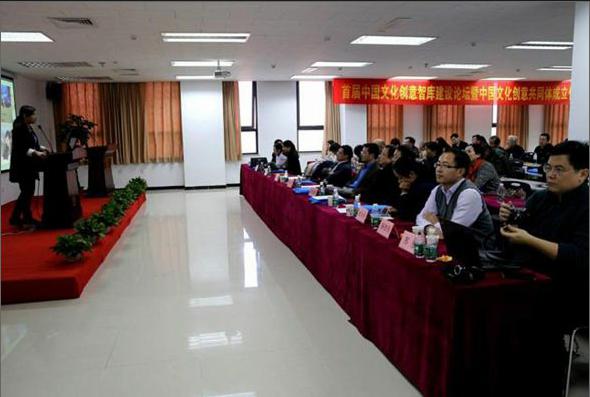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其实,中国古时就有类似智库的人物,如幕僚、门客、谋士、师爷之类,其建议是王公大臣等决策的重要参考。不过,“智库”这个词也是舶来品,中国对现代智库的初识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如今,现代智库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上智库最多的三个国家。美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大名鼎鼎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依然稳居世界顶级智库第一。报告中的“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上,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最高排名第27,但中国智库在专业化、筹融资以及影响决策等方面还有很大不足。而欧美智库经过多年发展,在各领域的研究水平都相对较高,并且整体发展更加成熟。
美国智库何以繁荣
以美国智库为例。在美国,智库自称“没有学生的大学”,但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机构,而是一支影响巨大的政治力量,其存在的真正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全美约四分之一的智库设在首都华盛顿,那里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认为,尽管不同智库存在许多差异,但从根本上都是政治和政策系统的“智囊团”,更多作为“影子政府”影响美国政治和政策。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智库并不是国家权力机构,而且原则上要保持非政府、非营利、不隶属任何党派、客观中立的特性。实际上,美国智库的运作更像商业组织,或者说是特殊的非营利公司。
比如位于美国加州、久负盛名的兰德(Rand)公司。Rand是研究(Research)和发展(Development)的缩写,是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但它仍称为公司(Corporation)。 这家智库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员工,包括1200名研究人员,在工作经验、学术背景、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种族、性别等各方面充分体现了多元化。这些人分别来自学术界、政府和私营企业,这样的好处是在研究上能够使得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而多元的社会关系也有助于兰德公司在各界发挥影响力。
多元的组成、深厚的背景,会让一家智库吸引到更多研究项目,这自然意味着能带来更多研究资金。据兰德公司官网介绍,该机构目前有1000个正在开展的项目,超过300家客户和资助者,研究收入高达2.53亿美元,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很多合同是同国防部、卫生部、教育部、国家卫生研究院等联邦机构签订的。
知识等于影响力,影响力也会反哺知识。1970年以来,兰德公司运营着一所受人尊敬的创新型研究生院,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公共政策分析学博士孵化基地。这所研究生院现在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约100名博士生就读,毕业生多成为政府、商界、非营利性组织及学术机构领袖。
除了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美国智库大多都有定期出版物。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等,都成为它们保持并扩大影响力的核心手段。
“旋转门”优势
政策制定者身边不仅需要智囊,其本身也需要专业。于是这就催生了政府和学者的“旋转门”机制,也成为美国智库政治影响力的写照。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唐纳德·阿贝尔森总结了美国智库蓬勃发展的六大条件——高度分权的政府结构、政策制定者倾向于政府外部建议、非终身制的文官职位、强大的政策企业家、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学者和政府的“旋转门”。细看一下,其中四条都或多或少与“旋转门”相关。
先看一串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名字。最大名鼎鼎的要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职于著名智库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之后历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从该中心走出的还有布热津斯基和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费正清。布热津斯基还曾就职于兰德公司,从政后就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费正清则曾在美国政府当过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横跨外交界和学术界,退休后也进了智库做高级顾问。此外,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曾任克林顿政府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国务卿赖斯也都曾是兰德公司的重要参与者。
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分别向政府输送了数十名官员。这些智库借助“旋转门”向政府提供人才,靠人际关系路线来影响领导人本身。由此一来,智库专家能够获取更多实践经验,政府官员也得以将经验运用到政策研究中,从而形成一种良性战略互动,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也避免了纸上谈兵。
不过,“旋转门”也是把双刃剑。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就会使得“旋转门”越出职业转换的通道而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为利益冲突提供滋生土壤。
独立性VS影响力
美国智库的运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以及政府合同。此外,美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有十几亿美元资金用于资助各种智库;政府对智库还有税收扶持,智库免征所得税和财产税,公司和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不过,这难以避免1800多家智库经济状况的冷热不均。
智库作为研究政策的组织,独立性是研究客观的保障。然而,研究对于资金和影响力的依赖使得智库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也容易让智库的客观性打折扣。《纽约时报》去年9月刊发多篇报道,讲述了美国智库接受他国资助并代表他国影响美国政策的诸多案例。
阿尔贝森指出,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获得影响力成了它们的主要诉求。因而,它们在给予政策制定者以政策建议或帮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独立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认为,美国智库与政府间保持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政府在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为智库提供大量有力的支持,有的公开有的隐蔽。智库通常以影响政府决策为己任,热衷于输出思想、制造话题,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提供咨询或研究报告。
赵可金对中国智库建设提出五点建议:一是保持智库相对独立性;二是鼓励政策研究和智库间的交流,减少智库两极分化;三是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四是支持智库基础建设,其中离不开资金支持,例如支持基金会、民调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外围组织建设;五是完善智库政治和政策的制度性渠道,完善相关法律。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对于西方的智库经验不能奉行拿来主义,而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