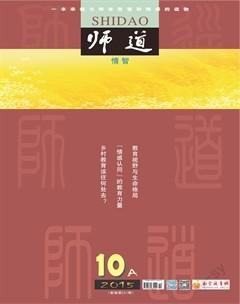乡村教育该往何处去?
王淦生
高考结束后,高三老师便处于一种赋闲状态。领导自然不会让我们闲着,便将我们“打包发送”到一所位于城郊的普通高中去充任监考——那里今年设了一个中考的考点。
来这里考试的都是周边地区的乡镇初中的学生。监考培训会上,培训人员一遍遍强调这里的考生素质之低、纪律之差,目的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承担的任务的艰巨——仿佛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监考,而是一场战役;我们不是普通的监考老师,而是看守,是刑警。
到了接触考生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不是这些孩子的“素质”和“纪律”,而是他们的神情——从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孩子应有的天真和稚气,甚至也不是农村孩子常有的那种淘气和顽皮,很多人都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落寞、麻木甚至愚昧。他们看人时那种空洞的眼神和不屑的表情让为人师、为人父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痛。
更为可悲的是,开考铃敲响之后,考场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填好考号、姓名后便趴到桌上呼呼大睡——他们甚至连作弊的欲望都没有,你唤醒他便是惩罚他,因为两个小时左右时间的枯坐对谁都会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们监考便是看着三分之一的考生睡觉,三分之一的考生枯坐。一个考场30名考生中认真答题的绝不会超过10人,稍好些的也就三两人。
在与送考老师的交流中我得悉,如今的乡镇初中大多处在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学校规模日渐萎缩,教师和生源日见减少——优秀生源和优秀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吸走,剩下的学生大多是一些留守儿童和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留守的老师也都是一些年龄偏大或教学水平平平的教师。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严重,更有甚者中途辍学,流入社会;老师固然有坚守岗位卖力苦干的,但更多的人则难免心灰意冷得过且过。如此,便使得乡村教育呈现出 一种每况愈下的态势。一个“混”字,足以概括出时下许许多多农村中小学学生、老师的生存状态。从这样的学校里走出的学生,且不论其学业状况如何(其中很多人近乎文盲),单看其精神面貌、言谈举止,就很令人沮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发展中国的乡村教育,那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诸如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陶行知、晏阳初等人都曾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驱。当时,他们都是怀着一颗“救国”之心来发展中国的乡村教育的,很多文学作品——如《倪焕之》《二月》中都曾有过红红火火而又如诗如画的乡村教育场景的描绘。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心驰神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乡村教育也曾有过如火如荼的阶段,我大学毕业后就曾在一所乡村中学整整待过10年。 弥漫在校园中的那种清新、纯朴、向上的氛围让我在日后遇到种种挫折和坎坷时不时冒出“不如归去”的念头——可是,最近我才知晓,那所乡村中学也已离关门不远,其生源已不足以支撑其作为一所学校而存在。也就是说,“归去来兮”对我来说已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梦!而这,是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乡村教育的一个缩影?
中国乡村教育的式微应该说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都不会比现在“有钱”。但为何我们的经济总量上去了,我们的农村富裕了,我们的乡村教育却呈现出一种颓势?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如今也愈来愈表现出对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的关注,比如在高校招生时重点高校要专门划拨一定指标定向分配给农村学生。可是,我觉得与其划拨指标给那些很少在乡村中小学待过的农村优秀学生,还不如想方设法先将那些在考场上呼呼大睡的学子唤醒。因为没有坚实的乡村教育的根基,而靠划拨一定数量的招生指标去照顾农村学生是无法带动起我们的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腾飞的。
当我们的乡村教育能够与城市教育相距不远甚至平分秋色时,当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再想方设法逃离乡村时,当我们的农村考生高考再不需要政策性照顾也能凭实力考进985高校时……我们才敢说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成功的。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
责任編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