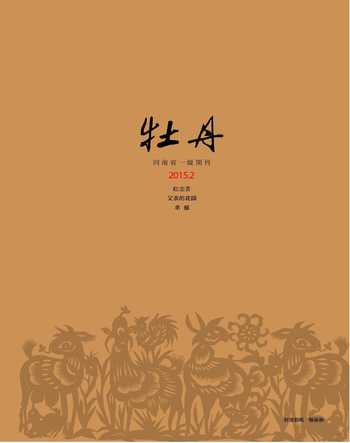阿尔志跋绥夫的生与死(节选)
布洛克波夫
死看似可怕,但当你回忆和思考生活时,行将逝去的生才让人恐怖。
——列·尼·托尔斯泰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很少有哪篇能不让人悲伤其不祥的命运。死亡也几乎是他长篇和中篇小说的主角。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从中读出了某种对规范的病态偏离——也许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作家理智和心灵上的绝境,他多舛的命运大概真的让人惊悚不安吧?也许这里有他命运隐私的秘密,即使快乐时也不可阻挡地把他推向绝地和沉沦的灾难。
有一次,阿尔志跋绥夫本人也坦率承认:“我只有三十岁,可当我回头观望时,觉得自己仿佛走在一片巨大的墓地,除了坟墓和十字架,我一无所见。迟早会在某处树立起一座新的坟墓,给它装饰上什么样的纪念碑,普通的十字架抑或大理石的庞然大物,全都无所谓——这便是我所留下的一切。归根结底,这无关紧要:不朽是种无聊的玩意,生命也鲜有乐趣。糟糕的是,死亡非常可怖,似乎你为此也打不定主意是否要主动让自己去见鬼;你还要活很久,要在这个被称为生的墓地上久久地行走,而在两侧,新的十字架在无休无止地生长,它们一直在微微闪耀。所有珍贵的,所有亲爱的,都留在了身后,内心里生长着的一切都在剥落,如同秋天的树叶,而你将孑身一人徜徉到最后。”
阿尔志跋绥夫在1909年写下了这段阴郁的话语,当时他刚刚送别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什金——自己的朋友,文学事业上的战友。到那时为止,我们大概第一次在随笔《巴什金之死》中觉察到精心掩饰的痛楚——肺痨把作家巴什金带入了坟墓,而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与痨病艰苦而英勇作战的,还包括阿尔志跋绥夫。死亡的幻象一旦在少年时震惊并难以挽回地伤害了他炽热的艺术想象力,从此便伴随他的所有时日和所有岁月,无形地渗透到他全部的成就和行为。
当然,死亡阴森可怖的影子首先会弥漫于他所有的创作——作品时而节庆般明快、灿烂,时而压抑、忧郁、毫无出路。与此相应,批评者们——他同时代人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一些人狂热地把他誉为太阳崇拜者——作家、永远欢快的爱情和生命的歌手;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作死亡征集人和掘墓者、无良的死亡鼓动者、人类道德的破坏分子。
这种批评上的对峙伴随阿尔志跋绥夫的一生。一旦偶尔安静下来,只要他的一篇新短篇、新中篇、新长篇刚一问世,它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自己被书写的数量上,阿尔志跋绥夫几乎超过所有同代人:除了以各种途径提及的不计其数的综合性报道,仅在他创作活动的十二年间(到他1923年被迫流亡为止),他就出版了146本著作和大量的报刊文章。如果把这个数字平摊到每天和每年,那么,很少有一个星期没人在某处热烈地谈论、诟骂他,或是把他抬到天上。
阿尔志跋绥夫有幸生在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并在那度过了自己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家乡的美景让他像个忠贞不渝的情人似的一再描绘。这是纯朴的阿赫特尔卡小县城和远离城市喧嚣的哈尔科夫边区多布罗斯洛夫卡田庄,它们隐没在葱郁的花园和森林,鱼虾丰肥的沃尔斯克拉河四下流淌,修道院静穆庄严。作家曾把无数行饱含诗意的感恩的文字,献给自己渺小然而又让他敏感的心灵感到那么迷人的故乡。他让几乎所有作品里的主人公都迁居到了此地。
“冬天时,小城冷清下来”,作家向我们讲述道。“它年轻而不安的一切都四散到大城市去了。只有一些老人留下来,他们全身心地过着稳稳当当、千篇一律的日子:打牌、工作、阅读,而且觉得这就是正当的生活。街上安详地铺着一层宁静冰冷的白雪,屋内,没有希望的人们在心平气和、昏昏欲睡地忙碌。但春天时,当湿润的黑土地开始散发出气息,到处再次微微泛绿,太阳倾听着每一次抽节的响声,也惬意地朗照起来,每到傍晚,周围又变得静谧和敏感——每天都有人随火车归来,大街上重新出现生动鲜活的面孔,他们像春天一样年轻、欢快。如此地自然,就像鸟儿飞回旧巢,就像青草在老地方重生,本来就是这样,只有到了春天,所有为生命感到愉快的年轻人才会回到自己宁静的略带伤感的小城”(《兰德之死》)。
一个类似的春天,阿尔志跋绥夫遭遇到给他心灵和命运留下终生伤痕的一场悲剧。关于这次不幸,叶甫盖尼·阿加福诺夫这样记述:“大概是1897到1898年间,当时我在阿赫特尔卡的哥哥家做客,他刚刚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地主。一次开心、热闹的午餐,在座的有这里的警察局长——他在就餐中间被赶来的警士叫走了——警察局长为自己必须赶往城里去处理一个重要事件而道过歉,并且表示一旦脱身便会赶回来。在这样祥和平静的小城会发生什么事件呢?我们迫不及待地等警察局长归来。两三个小时以后,他终于回来了。原来是场未遂自杀,一个叫阿尔志跋绥夫的年轻人向自己开枪。从留在我记忆里的警察局长的只言片语了解到,自杀企图源于一次严重的家庭争端,开枪的人伤势严重,几乎无法救治,连内衣都陷进了伤口,失血的情况令人担忧……”
然而,未来的作家活了下来,但这已不是原来那个充满幻想、热爱生活的少年了,而是一个成熟而自闭的人。就在这年秋天,从童年就迷恋绘画的他去了哈里科夫绘画学校学习。阿加福诺夫回忆说,新学生“外表奇特——黑长发,黑色的大胡子,面色灰绿,消瘦且微微驼背,穿一件黑色的俄罗斯式偏领衬衫。”一个活死人——阿尔志跋绥夫被费尽力气救活了;从那时起,他一生患病,经常被送往南方,却永远牵挂着多布罗斯拉沃夫卡——这个迷人而又潮湿的疟疾发源地。
阿尔志跋绥夫在绘画学校只待了一个冬天。为什么那么短暂呢?关于在寻找自己生活位置时的这种忙乱,阿尔志跋绥夫保存在档案中的个人手稿里不无讽刺地讲述道:“童年时想当猎人,但也不反对做个军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成为画家,但又非常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作家。之所以如此,源于哈里科夫的一家报纸为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而付给了我8卢布,我用它买了颜料。后来,我还想多挣些钱,于是又写了起来,就这样,学习绘画开始让我感到无聊,所以我就转道文学。再后来,我喜欢上了文学,渴望获得文学家的名声,而且必须是世界性的名声。如今我仍在期盼。我暂时还能靠父亲的钱生活,但后来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了:画漫画,写报屁股文章。不过,首要的是更加勤奋地玩台球。所有让我激动的世界大事中,最让我欣喜和担心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我能否把这个或那个球打进袋里去……我也非常喜欢随处流浪……我活到十六岁的时候,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以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永远不会射杀自己了。我一直酷爱唱歌,却又受不了器乐。我曾幻想做一个歌手,时而唱低音,时而唱中音,时而唱高音,可糟糕的是,这种事竟然那样令我难过,有一回我甚至大哭了一阵子。”十六岁时,阿尔志跋绥夫在哈里科夫的《南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1895年1月27日)。正如阿加福诺夫所追忆的那样,“他在小说中描写了自杀,把自杀者的感受写得细致入微、恐怖异常。”
当《神界》杂志1902年12月号刊出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阿尔志跋绥夫的《下级准尉戈洛罗波夫》时,谁也没有料到,他所预见和提出来的问题以自己成倍加强的悲剧色彩,很快就变成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那些失去生活信念的已经颓丧、愤怒和绝望的人,艺术家的思考其实是世纪初被普遍关注的焦点。就这样,作家的个人体验突然处在了疯狂增长的社会灾难的旋涡中心。
写完这部小说,阿尔志跋绥夫几乎第一个让自己同时代人关注起世纪初愈加成熟的深刻危机,这个世纪初属于“普遍毁灭的鼓动者”,以及用“死亡的黑雾”笼罩身边万物的狂热的“灭亡先知”。孤独的主题和人与社会的失调很快便充斥于革命前的文学。自杀者们从一本书游荡到另一本书:蒲宁的《快乐庭院》、高尔基的《马卡尔的生命奇遇》、吉皮乌斯的《月光下的蚂蚁》,以及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和、布留索夫的剧本、小说和诗歌(被读者视为神奇的人类自毁标志的布留索夫的诗歌《自杀之魔》尤为著名)。
“我们整个国家好像在突然变成一个自杀者俱乐部”——当时还很年轻但已颇有名气的批评家科尔内伊·丘科夫斯基在《言论报》上惊恐地写道。他是积极参与这个几乎充斥了所有重要报刊的辩论话题的人。哦,“话题”这个词所适用的是那种普遍化的讨论。瞧瞧当时能让所有不太冷漠的人感到惊慌的数字吧:“在彼得堡,1905年发生295起未遂谋杀和自杀事件;1908年,每月的企图自杀者为121人,1909年,每月则为199人,增速惊人。”
阿尔志跋绥夫作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以自己的文章和小说卷入了这场争辩。并且,最终就这场辩论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绝境》。如我们所见,从踏进文坛的第一步起,阿尔志跋绥夫就为我们展示了他主要的创作特点。首先是要求作家表达“纯粹个人的体验”和“经过内心检验的内容”的自传色彩,其次是始终要努力经过社会事件检验,在这个前提下寻找自己独特的个人视角,即再现经过这种检验的独具个性的人格化途径。在随笔《小女人生活片断》中,阿尔志跋绥夫颇为赞赏地引用了作家巴拉金的话语:“人们只阅读文字。他们探寻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作家的个性,但要知道,在每个人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自己”。阿尔志跋绥夫在随笔《契诃夫之死》里再次回到这个观念——“重要的不是作家写什么,不是这种或那种被他鲜明揭示的真理,而是他独特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既博大又丰富。”
“滚开,超人文学家,滚开,无党派的文学家!”——就在阿尔志跋绥夫写完关于“超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最初未得到出版社和杂志认可的时候,首次爆发出了这句街战口号。这便是他的《萨宁》——一部个人主义小说,同时也是观念小说,但从作者的构想上说,它首先是一部作家的独特个性得到高度艺术表现的作品。
《当代世界》杂志1907年11月号开始刊登这部小说,而它的最后一个句号被24岁的作者点上时还是在1902年。为了弄清楚手中是部什么样的尽管有爆炸危险但颇具新意的作品,编辑们耗去了五年时间。阿尔志跋绥夫的同时代人一面惊奇地阅读小说,一面从中摘录那些随后被引入所有关于作家的批评文章和专著的主人公的言论。
“我只知道:我活着,并且希望,生活对我来说不是一场磨难……为此,首先要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欲望——仅此而已!”——萨宁
“如果夺去女人的贞洁世界,与那些非常柔弱却又美丽动人的春天里的鲜花如此相似的贞洁,那么,人身上还有什么圣洁之物呢?……”——斯瓦罗日奇
“死亡就守候在我身后,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倍倍尔跟我有什么相干!”——谢苗诺夫
“只有已经在生活现实中发现快乐的人才有资格活着。而那些受难的——最好去死。”——萨宁
瞧,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所表述的作品的核心观念:“我们给肉体欲望贴上兽欲的标签,开始为欲望感到羞耻,给它们蒙上侮辱性的礼服,创造不健全的生命,而我们中间那些本性虚弱的人不会发现这一点,他们给生命套上锁链,那些虚弱的人不过是被虚伪的生活观和自我观束缚的结果,而那些感到痛苦的呢:遭受蹂躏的本能力量向外挣扎,肉体在渴求快感并折磨他们自己。他们一生都在分裂中彷徨,拼命抓住新道德理想范围内的每一根稻草,于是,到最后,他们畏惧生活,他们闷闷不乐、害怕感受……既然在人和幸福之间一无所有,既然人将自由无畏地屈从于他所能实现的享乐,所以我一直在梦想着幸福时光。人们只为温饱而活的那个时代是野蛮而贫穷的时代,可我们这个肉体降服于精神、人被简化为未来规划的时代却毫无意义地衰退了。但人类也并非白活:他们能创建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兽行,还是禁欲主义,都不会在新环境里获得存身之地。”
小说《萨宁》以动人的力量表达了20世纪初俄国人身上业已成熟的东西——即那种反对道德和政治的所有监牢和枷锁,反抗所有桎梏他自由的装置的特征。这本有关20世纪的巴扎罗夫(萨宁也的确有这个称谓)的著作给了普遍规范致命一击,这些规范被所有那些授予自己武断地裁决善与恶、低俗与高尚权力的人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掌控。这本书给了虚伪的偏见以更大的打击,那些偏见自古以来便约束着作家和思想家的笔尖,指示他们什么是人身上可以表现的,什么是不能表现的,强行转移他们探究的目光,让他们无视人不仅仅是神圣、纯洁和高尚的仓库,同时还是缺陷、罪恶、龌龊和卑鄙的载体;崇高至极的精神和卑下的肉体在人身上同样存活。阿尔志跋绥夫追随自己的伟大导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试图解开“天性统治者”的这种隐秘的矛盾,他也因此立刻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谴责和另一些人的善意的狂喜。
高尔基第一个权威性地为小说《萨宁》贴上了“反革命”这个修饰语,并由此注定了几十年与之相应的对待该书作者的态度。直到多年以后,已经到了生命尽头的高尔基在思考日后的俄国文学史时,认为如果缺少类似于反映了“时代混乱”的阿尔志跋绥夫的那一类作家,文学史称不上完整。“我在把自己称为‘典型化的同时”,他在1927年写给格鲁兹杰夫的信中说道,“也把这个封号带给我过去的一些同志: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蒲宁、库普林和很多其他人。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大家有某种共通的东西,显然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情感上的。猜想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我要提醒批评家们的。上面提到的作家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到了为给当代的文学工作者提供益处和教训而做这件事的时候了。”可这样也于事无补。
另外,已经是在1917年之后了,高尔基似乎带有忏悔意味地首先尝试再版《萨宁》,把它编入《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卷,但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萨宁》还有第二个骇人听闻的标签——“淫秽小说”。如果说它的“反革命性”(如果愿意,20世纪初的大多数俄国文学都可以被置于这个模棱两可的判决之下)激怒的是“左派”,即态度激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那么,作家在描写爱情时的那种被认为是过分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勇气引起的则是“右派”的愤怒抗议,而与他们一道的还有那些在神圣俄罗斯永远不缺的伪君子和假绅士。很快,这些人和那些人,“左派”和“右派”,就像毫不妥协的敌人突然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同处一个阵营:小说《萨宁》的对面,更确切地说——是在沸腾中达到最高温度的对它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时候,针对它的诉讼开始了。
围绕“萨宁主义”和“阿尔志跋绥夫主义”的激烈纷争甚至立刻便冲出了国界,蔓延到了欧洲,在那里,这本“反叛”小说立刻被翻译成几种语言,而且也像在俄国一样,首先便遭遇到教条主义者和道德家们的抨击,随后,对这本书提起审判的已经是真正身穿检察官长袍的人了——他们宣称,这本小说“因为宣传淫秽”需要抄没,而作者则要受到拘捕和适当的惩罚。多亏国内文学界的强烈干预,小说在柏林才得以幸免。以官方鉴定人身份参与法庭审理过程的德国作家路德维格·汉克霍费尔把这部小说称为“具有高于艺术性的创作”,按照他审慎的证词,这部作品“同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的古典作品一样占有自己崇高的地位”。
但关于《萨宁》及其作者的争论又过了很久也未能平息,一直到了那个年代,当书和人都被严格查禁,禁止其实变成了漫长而严厉的所有伪君子们的咒骂。
而实际上,连列夫·托尔斯泰都曾读过阿尔志跋绥夫。在他1909年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一条笔记:“……阿尔志跋绥夫身上活跃着——而且独特地活跃着——无论高尔基还是安德烈耶夫都不具备的思想……库普林质朴的天赋没有内涵;阿尔志跋绥夫既有天赋,又有内涵。”而这是托尔斯泰另外一则关于阿尔志跋绥夫的笔记:“这个人很有天赋且思维独特,尽管极大的自负会影响正确的思考。”
或许阿尔志跋绥夫既有“极大的自负”,也有迷惘和偏颇,但他也把握着另外一种东西——即真理,诚实而没有任何修饰地被他表达、但当时却被人恶毒而愤怒对待的真理。正因为这样,他整个创作生涯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家笔记,字里行间都浸透着对不解的怨恨、对我们这些阿尔志跋绥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读者的指责。他捍卫女人的软弱——谴责对女人无礼的态度,他揭露男人的自私自利——以回应“你真正的英雄在哪里”这种愚蠢的责难。他揭示了崇高和卑下在人类身上的冲突——并因为败德和淫秽而被起诉。了解这一点,我们怎能不理解他满含痛苦的不由自主的坦白呢:“上帝赐给我可能降临到作家命运中的最大的不幸——即做一个真诚的人。”
1923年,当时,被不公正、不理解和不认可逼到绝境的作家就像他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必须踏上自愿的流亡。前往异乡时他便预感到,这是永远的离去,自己将会死在他乡。但有一点他没料到——自己只能再活三年了,因此,似乎前方是永恒一样,病人毫不吝惜自己,在赤贫中热情洋溢地工作,“并在战斗的火焰中燃烧殆尽了”。
1927年3月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阿尔志跋绥夫在华沙逝世。祖国的《星火》杂志以刊登作家肖像的方式对这个噩耗做出了反应,而在肖像下面——则是我们在今天都羞于阅读的简介:“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在国外去世。俄国读者中或许有人会为这个在自己的时代享有盛名的俄国作家感到难过……”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