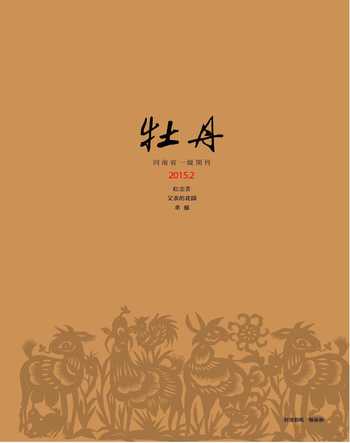父亲的花园
向迅
一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父亲终于从遥远的新疆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家了,而没有临时改变主意,和他的两位兄弟一道在中途下车。
我私下里以为,父亲背井离乡的历史可能要画上句号了。
几年前,我们就呼吁不让他出远门了,可他还是像一只疲惫的老候鸟一样裹着一身稀薄的羽毛年年东出景阳关。他扔给我的理由,无非是“靠你一个人,怎么搞得走呢?”我这个只是动动嘴皮子的泥菩萨,每每都是抱愧以对。
今年他又出去了,这让我更加不安。
回家前,他和他的伙计们被困于冷锅冷灶的工地,在那儿焦急地等待项目部给他们结算那笔尚不足以充作盘缠的薪水。我们父子在此期间进行过一番简短的交谈。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谈话。
那天,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父亲显得犹豫不定。他用商量的口气征询我的意见:“我是直接回家呢,还是跟着你的叔叔们去江西呢?”我很坚定地告诉他:“回家吧!”他这才下了决心:“好吧,听你的!把账结了,就回家!”听起来,好像是要我承担他回家的责任似的。
我已不记得,独断专行了一辈子的父亲,是从哪一天开始转变态度的。
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每况愈下的身体,根本不适合再在工地上从事重体力工作。尤其是他的那只伤痕累累的右脚,早已不堪重负。自从2002年以来,他的身上就又多了一个 “阿喀琉斯的足踝”。那是我们一家人共有的一道伤疤。
其实,父亲一早也怕出去了。
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想必这也是父亲告诉她的。
我在春节期间给父亲和母亲许下承诺:“只要有时间,就多回来看你们。”农历三月中旬,父亲六十大寿,是必定要回一趟的。然而,他在生日前夕突然远走新疆,我没能回家给他祝寿,敬他一杯酒。
那时正值清明,我便将归期推至“五一”。而父亲从新疆回来时,恰是四月末梢。我本已买好车票,却又因那时手头紧张,临时退了票,还很一本正经地向母亲解释:“单位临时有事回不了了。端午一定回!”
“五一”的前两天吧,父亲打来电话:“你们回不回来的,不回来的话,我又要出远门了。他们邀我去河南呢!”
“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出去了,在家里给妈搭把手算了。现在家里又没有多少开支。”
“那我就看情况吧……”停顿了好一会儿,他继续说,“他们明天邀我走的话,就跟着他们去。”
不知是伙计失约,还是他终于考虑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最终留在了家里。
可身为一介草民,不可能像个退休老干部一样,每天无所作为,一茬茬农事,多如牛毛,繁如乱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父亲刚刚在家歇了两天脚,母亲就告诉我:“你爸爸又出去了,在村子里修水库,利川人承包的活路。”
二
端午节时,我多请了两天假,终于携女友回家了,算是给他们一个交代。
第一次跟我回家省亲的女友,在参观完我们家的房子后,也直夸她未来的公公婆婆有本事:“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还建起了这么宽敞的大房子!”她不知道,这是他们花了一辈子的心血而换来的一句荣誉呢!也就是这句类似于精神支撑的荣誉,支撑着他们熬过了最为艰苦的岁月!如今熬水成珠了!
院子前方,在落木萧萧的冬天见得着一方开阔的视野,可一眼望见轿顶山、五花寨以及江北的凤凰山等被乡人津津乐道的自然风光,现在却挂着一道翡翠屏风——披着一身厚厚枝叶的阔叶林树木,把远山都给挡住了;也像是荡漾着一座碧波起伏的大海,鸟雀在翡翠般的浪波上像鱼儿一样跳跃、飞翔呢。
天地间这样旺盛而蓬勃的生命气息,深深地感染了我。
那棵在正月里被移栽到院坝西边空地上的银桂,全身上下已抽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嫩黄色的新枝。很显然,它已经缓过神来了。可以想见,农历八月,它就要开出一院子金黄色的花香来。
西边的山田,历来是我们家的菜园子,里面还种了不少果树,核桃啦,苹果啦,樱桃啦,橘子啦,柚子啦……翠生生的东北菜生得很淑女,明明是小家碧玉,却起了个与其容颜和脾气相差千里的男性名字;黄瓜的藤蔓,已经在鬓角斜插上了大朵大朵的黄花,像有孕在身的年轻的母亲。
把目光收回来,柿子树下的一小块花圃引起了我的注意。
多年以前,这里也是菜园,只不过后来因为修马路而变成了一块空地,于是在此种些花花草草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父亲一早就在田埂边培植过几株常青树,如今已出落得有些模样了。爱花的妹妹,几年前也在此种过一株月季,现在已经繁衍成一大丛了,尽管父亲年年给其修剪打枝,它们却不予理会,你剪你的,我长我的。大冬天的呢,它们都会把小拳头一样的水红色的花骨朵高高地举在北风呼号的冰雪地里。
引起我注意的,自然不是常青树和月季花,而是一小块花秧子。
这些像向日葵幼苗的花秧子挤挤挨挨的,簇簇拥拥的,繁密极了,我真担心它们透不了气。
事实上呢,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简直是杞人忧天,你看那块绿毯子上已经绣了好几朵花了,深红的,纯白的,像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正抿着嘴微笑呢,也像是弱不禁风的蝴蝶,歇在叶尖儿上,风一吹,它们就翩翩起舞,摇曳生姿了。
不过,开花的,是另一种花草。
这种花的藤蔓颇像茴香,茎杆细细的,叶子也是细细的,与小巧玲珑的花朵倒是极相宜。金黄的花蕊,是缩小了一千倍的向日葵的花盘,在一川草木间,像三两盏灯,绽放着细碎而迷人的光芒。
母亲见我们赏花,便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你爸爸从新疆带回来的花种,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一窝猪草呢!”她俯下身,用手抚了两下花秧子,接着说,“这么密,他也不知道除一下!”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花,叫不出名字。热衷于花草知识的女友说,这是波斯菊呢。妹妹插话,上网查了,是格桑花。新疆内蒙境内不是生长着大片大片的格桑花么?
格桑花的旁边还栽种了数株海棠,都开花了,一朵一朵紫红相间的花儿,爬满了宝绿色的茎杆。母亲介绍,这都是你爸爸从谁谁家门回来的。
海棠下方,是一架蓬蓬勃勃的葡萄,叶子下挂满了密密匝匝的玛瑙。
这个秋天,该有葡萄吃了。
不记得是这天中午,还是第二天的什么时间,我们在谈论父亲的花圃时,母亲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让我深感意外的话:“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品性呢!” 很显然,这是她将我们的父亲与她的小叔子们作了一番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她说:“你爸爸不管走到哪里,都晓得门这些东西。果树啊,花种啊,家业啊……不远千里地门回来。不像那些人家,门口就看不见一株花草,也不见一棵果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如此评价父亲,尚属首次。我试着把母亲的原话用书面语翻译了一下,大约是这个意思:“你爸爸的品性与他人不一样,骨子里还是有几分雅气的。”
我也在想啊,一个晓得不远千里往家里移几株花草的人,一个把劳作之余难得的休息时间都花在了种花种草上的人,多少是有一些“闲情”的吧,就像母亲说的那样,品性异于他人。
父亲不是花匠,只是一个爱花之人;一个爱花之人,必然是懂得美的。
他种花的历史未曾中断过,多年以前,他就在院子里种过刺玫、娇花、绣球、海棠、美人蕉等花草,都是他从外面移回来的。一到花季,院子的角落里全是绿叶红花,极养眼的。
我多次说过,父亲如果再多读一点诗书,凭他过人的天赋,不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忽然发现,与父亲斗了一辈子嘴的母亲,原来是理解父亲的,而且能够一针见血地说出存在于父亲骨子里极易被生活的表象所遮蔽的东西。
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三
这天下午,天气突变,落起了雨。我们正在屋里同母亲说话呢,门外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猜测是父亲回来了。
我开门迎他,戴一顶草帽的父亲,正弯着腰跺鞋子上的泥。
父子相见,虽不及母子见面时那般热闹,心底总是高兴了一场。
他跛着脚蹒跚着进来,随手把头顶的草帽摘了,将之挂到了墙上,才转过身来跟我们搭话。
他依然留着领袖头,尽管头顶有些秃,但因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也就掩盖了这一点美中不足。
眼角的几道皱纹像刀痕,很深刻。即使相谈甚欢,也难得见到他的笑容。他的那张历经沧桑的脸,总像是被一种极遥远的痛苦和淡淡的愁绪包裹着,与照片上那个正处于年轻时代的相貌英俊的父亲相去甚远。
或许是又在工地上硬撑了一天吧,他始终没有把腰背挺直。记得母亲多次提醒过他:“一辈子都没看见你有一个挺拔的时候。”不屑于为自己辩解的父亲,一次终于道出了原委:“这都是早年做木匠落下的毛病。”
一番问候之后,父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去换被雨水淋湿的衣裳。就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第一次留意到,他蹒跚的背影,跛得是如此厉害。脚步一高一低,一深一浅,步步不易。那只右脚,更像是出于惯性,被左脚牵着走一样。不知他咬着多大的疼痛呢。
我不禁想起我曾经描述他在十一年前练习走路时的一句话:“他每走一步,都让人感觉到世事的艰难。”
年过花甲的父亲,早已被命运折磨得对生活只剩下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一次次被生活逼出家门,一年年被命运这条狗追赶着四处奔波。
刚开始,父亲一直关注着外面的天气,时不时踱到门口望一眼。
雨下得很薄,雨脚一会儿就住了。
他站在门口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自顾念叨着:“不知道还要不要去。”直到母亲搭腔:“如果要开工的话,他们自然会通知你的嘛!”他才心安理得地坐下来。
不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或许,除了母亲询问了我女友的一些情况外,什么也没有聊吧。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下午电视。
一脸倦容的父亲,坐在一把木椅上,脑袋一起一落的,终于打起了瞌睡。
他是越来越和蔼可亲了,脾气越来越好了。
当年那个敢对任何人任何事叫板的人,已与他渐行渐远。过去的那个严厉的金刚怒目的父亲,也已成为记忆中的形象。
或许,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理想中的父亲的形象,具备了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父亲身上所具备的品质。
但是,我还是怀念那个年轻的父亲。
已经不止这一次了,看着打瞌睡的父亲,我都觉得他像是一个刚刚在外面玩累了的孩子。
我想像一个父亲那样去爱他。
四
我们终于和父亲谈论起了他的花圃。
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这些花,都是我从新疆玛纳斯带回来的。我们在那里干活时,看到公园里的花开得那么乖,就随手摘了一些花种。总共有十几种呢!”又不无遗憾地补充道:“不过,奇怪得很,在玛纳斯时,那些花长得跟葵花一样高,花开得跟小碗一般大,可到我们这来了,却长得这么秀气,花也只开这么大一点点,而且只长出了四五种花。或许是摘的时候,一些花种还没有长成器吧!”
他一边比划,一边给我们讲述花事。
作为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和有着丰富嫁接经验的农民,他该是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的,可在这花事上,他却犯糊涂了。
端午节那天,久违的阳光落了一地,就在我们准备启程去双土地老街的那一刻,或许是因为看到了那块小小的花圃而有所触动吧,忽然就萌生出了与正在忙碌的父亲和母亲合影的想法。
对于这少之又少的合影的机会,他们很重视,父亲脱掉了棕色的夹克外套,母亲进屋换了件蓝白相间的新衬衫。合影的背景,就是那一丛开着水红色花朵的月季和那一块正在蓬勃生长的花圃。身后呢,是一方草木葳蕤、碧绿生光的夏日。
拍照时,父亲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一张被皱纹雕刻的脸,像是一个历经劫难的花骨朵,终于绽开了。
看着父亲和他脚下繁密的花圃,我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父亲和母亲其实就是一座花园,同时也是这个花园的园丁,而我们兄妹,是他们种在花园里由同一根脉生发出来的三枝花。
我们兄妹,确实像是几株花,原以为会在那个乡间花园抽枝发叶,开花结果,却被那两位目光渐长的园丁送入了一个更大的花园。
他们是想让我们开出更灿烂的花朵。
回家的第二天清晨,我在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竖耳一听,是父亲的声音。他喊得很轻。我到底是答应了一声。他在窗口告诉我:“你妈到坡里打猪草去了,我也要上班去了。”
我匆匆起床,来到院子里目送父亲。那时晨雾甚大,遮天蔽日。父亲戴着那顶草帽,沿着屋后那条黄泥小道蹒跚而去。他的背影,不一会儿就被大雾吞没。
我的心有一点慌乱。
父亲走路时的样子不可模仿。两个脚印,一个深,一个浅。
他佝偻的背影,像一座秋天的苍山。
我曾以为与这样的父亲难以和解,但在我经济独立自己当家以后,尤其是到了睡不着觉的而立之年,我才开始理解父亲。作为掌舵者,要把那么大的一个家撑下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这几年,我一直想与父亲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一次,与他谈谈人生和理想,但终是碍于什么,而不了了之。有时候,我想我是了解父亲的,但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已经与我做了三十年父子的人。
古人说,知子莫如父。然而,谁又知我们的父亲呢?难怪父亲留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沉默而不善言辞的。或许还有些孤独吧。
这是中国父亲的文化形象。
责任编辑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