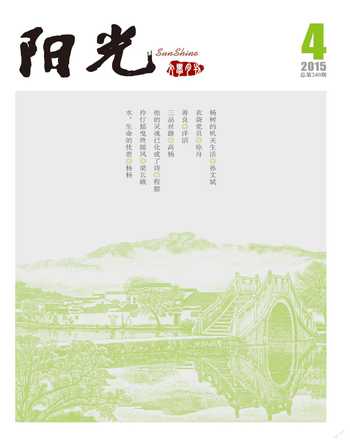七哥
一
开采百年的矿山日渐衰败,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废墟。就连昔日围着矿山流向远方的河水也断了流,露出光秃秃的河床。从远处看,那一座座山坡没有了昔日的葱绿,树木稀疏,山雀凄凉地鸣叫穿行。不规整的农田爬到了山顶,像被打了一块块补丁。还有数不清的废弃小煤窑和大小不一的矸石山,如狰狞的野兽将山川撕裂成一个个伤口,流淌着血。
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大山深处,原本被人美誉为世外桃源。上个世纪大跃进的时候,国家缺煤,天南海北的人们响应号召汇集到这里,靠驴拉人扛,硬是建起了大型煤炭生产基地。矿山有一条街,坑洼不平。阴天下雨街道泥泞,戏称“水泥路”,“马蹄坑”积满了水,躲都躲不过去。到了艳阳天则称“扬灰路”,车走过,就扬起了蘑菇云似的灰尘。改革开放之后,有了“肥水快流”之说,矿山有了繁荣的景象。新开的小煤窑围着国有大矿如雨后春笋不断地蚕食资源。满山遍野的小煤窑立了起来,随之一片片的树木倒了下来。开小煤窑的多了,人多了,临街做生意的日趋红火,商铺一个挨一个,这条街也修成了柏油路。
资源的枯竭,意味着矿山的没落。曾经兴盛的国有大矿破产倒闭,年轻人走了,到山外谋生。开小煤窑的人把煤掏空,赚足了钱,也走了,留下的是脆弱的环境,还有那些经历了矿山的兴衰、曾在矿井血与火的考验中日渐衰老的老矿工。
退休后,闲在家里的七哥一副清瘦的面孔,中等的个子,穿着早已经褪去了本色的肥大工作服,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口已经起了毛边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在一座废弃的小煤窑旁刨出了一块儿贫瘠的地,种植了西瓜,寄望有个好收成,换点儿零花钱。多日不下雨了,低矮的西瓜苗长得很慢,在阳光的烘烤下,叶子打着卷儿没了精神。身体单薄的七哥看着心疼,跑到八里外一处池塘提取浑浊的水,挑着锈迹斑斑的水桶吃力地行走在山路上。长长的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儿,浸入一道道皱纹里淌成了流儿。他停下了脚步,放下担子,气喘吁吁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拽下搭在肩上薄薄的发了黄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这时,从山坡上走来一个人,是老九,一位曾在井下一起挖煤的兄弟。
老九,实名李赞,七哥与他拜过把子,排行第九,所以称为“老九”。俩人小时候都在农村生活过,对土地特别亲。俩个人刨出的地挨着,不过老九种的是玉米。每天俩人早出晚归,一起忙活着这片地儿,一起聊聊天打发时间。和七哥不一样,老九身材不高,长得敦实,肤色黝黑,生性温和,是个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着自己的主儿。
俩人将镐头撇在了一边儿,来到一棵老榆树下乘凉,抽起了老旱烟。偶尔说上几句,更多时候是沉默不语。即使不说话,也知道对方想什么。
这时,热得鼻孔都在冒火的七哥熄灭了手中的半截旱烟卷儿,焦虑地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脱掉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老头衫,露出了单薄的躯体。打开随身携带的玻璃罐头瓶,抿了一口水之后,放在了一边,说:“他妈的,这天贼热,像下火。”
“是啊,咱们住的地方地下水都被小煤窑破坏了,许多水井已经枯干了,吃水都成了难事儿……”老九拿起七哥的罐头瓶子,也抿了一口水,舌头舔去了挂在嘴角的水珠儿,摇摇头,情绪低落。
夕阳落山了,映红了半边天,也映红了整个矿山,两个人的身体也披上了红彤彤的彩霞。矿山的灯火在他们身子下方又汇集成了一条条颤动的橙红色的线。很久以前也曾经这样看过矿山,那迷人的景色让他们陶醉,于是,老九情绪好了许多,眼眯成了一道缝,微笑地说:“七哥,你看,这景色很漂亮啊!”
七哥没有抬头,阴沉的脸始终松弛不下来,有一种清晰而纯粹的凄凉感似乎夺去了他的灵魂,他愤愤地说:“有什么好看的。”
老九似乎理解了他的话语,叹了一口气,低声说:“是啊,变化太大了。以前,我们常常爬山,呼吸清新空气,追赶野鸡、狍子啥的。自从小煤窑多了,动物们被吓跑了,泉水也没了!唉……青山绿水都被糟蹋了。”
七哥最烦他这一出,不论说什么话题,都能扯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不想听老九唠叨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情,捡起扔在地上那半截旱烟卷儿,吹了吹上面的灰尘,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干咳了一声。嘴里充满了热乎乎、咸滋滋的味道,显然是汗水流到了嘴边。他吐了一口,急忙吞咽了一口新鲜空气,那景色、那矿山、还有那树林、那动物跟自己没有一点儿关系了。他尖刻地说:“以后别再提这个水那个地儿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老九想争辩几句,看到七哥的脸儿拉得很长,又咽了回去,保持了沉默。
回家的路上,俩人闷闷不乐,各自为那块地的旱情而焦虑。老九忧心忡忡地说:“今年,我这玉米苗是长不大了。人和庄家争着吃水,唉……这个破地方……”
“打住!你是真能和我扯啊,哪壶不开提哪壶,能不能换个片子?走,咱们喝酒去!”七哥说。
二
俩人走进了“王二嫂小吃”。他们与老板娘王二嫂很熟悉,交情不一般。王二嫂长得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一副和蔼的样子,和他们格外地亲。红润的脸颊是她喜欢烹饪和待人热情的重要标志,笑起来如山里的迎春花一样美丽。十年前,七哥与她丈夫王军在矿井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处得比亲兄弟还亲。采煤队百十来号人中,曲二驴子年龄最小,什么事儿工友们都让着他。同时,他又是个不守规矩的人,有点儿匪气,常常投机取巧,偷懒耍滑,隔三差五不上班,令工友们生厌。为此,同在一组的王军因为受牵连没少挨罚,感觉很窝囊,俩人时常斗嘴掐架。这天,俩人又分在了一组回柱,曲二驴子违章空顶回柱。顶板突然冒落,王军见势不好,将曲二驴子推到了一边,自己却被一块巨石压在了底下……王军是为了救曲二驴子因公殉职的,工友们都为之惋惜。七哥喜欢打抱不平,为此事找过曲二驴子理论,俩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彼此在心里结下了疙瘩。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王二嫂精神上蒙受了巨大的打击,绝望的情绪闪电般突然袭上心头,一股飘忽不定的气流将她投进深渊,感受到了丈夫的永别将自己美好生活撕得粉碎,自己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的生活也没了着落。王二嫂的眼泪都哭干了,身体瘦了一圈儿。怕她撑不住,工友们心急如焚。还是七哥点子多,组织工友们凑了四万元,在临街买了一个门市。又与几名工友一块儿来到了王二嫂家里,告诉她:“王军活着的时候我们是铁哥们儿,现在家里有难了,都想帮助度过这道坎儿。大家觉得你心眼儿好,人又实诚,而且会做一手好菜,适合开个小吃店,决定把这个门市交给你经营。”随即将钥匙塞给了她。王二嫂手握着钥匙,眼前一片模糊,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心存无限的感激。其他人鼻子也酸酸的,并在不断地劝慰她。
突然,王二嫂停止了哭泣,擦去泪水,瞪着充满血丝的双眼,说:“这门市我不能要,谢谢你们的好意。现在我还能自食其力,不想当可怜虫。”王二嫂的变脸儿出乎人们的预料,大家的心七上八下的。
“二嫂,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都敬重你。可是门市买了,也不能退回去啊!”七哥说。
王二嫂犯了难,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沉思片刻,计上心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你们的好意,我接受!谢谢你们!”
“这就对了嘛!”众人附和。
“不过,我有个条件!”
七哥松弛的脸又紧绷了起来,追问:“什么条件?”
“门市我接,产权归大家,每月我付房租,待赚到钱了再把这个房子盘下来,你们看行不?不行我就不接!”
“二嫂,你这不是钻牛角尖儿嘛!”七哥微笑地看了王二嫂一眼,只见她的脸色又阴了下来,觉得既然拗不过她,就顺着她来,以后再做打算。接着说,“好,好,就依着你的想法!”
“这还差不多!”王二嫂脸儿笑得如花。
她努力振作精神,表现出矿山女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充满自信的品质,消除了一切幻想,全神贯注地筹备着。终于“王二嫂小吃”如期开业了,名字是七哥给起的。开业那天,采煤队的人全去了,王二嫂亲自下厨,什么凉的热的、炖的熘的,调着样儿做。酒管够喝,菜管够吃,撑得这些大老爷们儿咧着嘴儿笑。自从“王二嫂小吃”开业,每天店里都坐满了人,生意出奇地好。七哥自然也没少光顾,隔三差五领着老九等人来到这里大吃一顿 ,矿工们心里很清楚。
不到两年的工夫,“王二嫂小吃”在矿区闯出了牌子。 要不是那天一个矿工兄弟酒后说走了嘴,她还蒙在鼓里。这才知道七哥等人一直在暗中帮她。王二嫂坐不住了,总想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像拉磨的驴一样打转转。心想,七哥等矿工兄弟们都是俺恩人,别看表面上都跑粗,各个心里却很善良和聪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又听说七哥退休了,总想找个机会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否则,心里不踏实。她选了个日子,将七哥、老九等人请到了家里做客。泪眼婆娑地告诉大家:“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没有你们的帮助,二嫂没有今天。你们对我的好,我一辈子忘记不了!”王二嫂擦去已经漫过嘴唇的泪水,几声哽咽之后,又大声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庆贺七哥光荣退休。还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把买门市的钱还给你们!”将装着四万元现金的布袋子放在桌子上之后,她深深地向七哥等人鞠了三个躬。接着笑着说:“现在我生活好了,孩子也读完了大学,有了很好的工作,我也没什么负担了。从此以后,只要哪个工友平安地退休了或者过生日,俺就给他举办免费的‘退休宴‘生日宴,把大家请来一起热闹,也算是俺对大家的心意!”
众人高呼:“ 好!”
七哥等人大碗酒喝着,大块肉吃着,屋内充满了欢笑声。
三
俩人一落座,王二嫂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两位大哥,很久没有来了,想吃什么尽管点。”
俩人不假思索地点了麻辣豆腐、熘肥肠两个下酒菜。王二嫂手脚麻利地做好了,又给端上了两小盘土豆丝、花生豆儿配菜和大茶缸里焖着的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牛眼儿大的酒盅斟满了五十度的高粱烧,俩人开喝。几盅酒下肚,俩人喝得像红脸儿关公。
走出“王二嫂小吃”,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空中。老九打个一个酒嗝,对七哥说: “听说咱们的那块地林业局要收回,说是退耕还林,明天就要上山要求我们自行铲除。”
七哥嚷道:“听兔子叫,还不种黄豆了!”
回到家里,七哥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着老九酒后扔给的那句话。心想,好容易刨出了一片地儿,不让种,那不是白忙活了吗?
清晨,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山上,远望矿山袅袅炊烟升腾白茫茫一片,显得格外空旷。站在西瓜地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西瓜旺盛地生长,什么事情都抛了九霄云外,手握着锄头小心翼翼地铲草。老九在玉米地里弯着腰在间苗,伸了伸腰,回头一望,只见沿着山路走来两个人,喊道:“七哥,他们来了!”
七哥放下手中的锄头沿着老九指的方向看去,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说曹操,曹操真的来了。他狠狠地瞪了老九一眼,说:“ 好事说千遍不灵验,坏事一说一个准儿,我是真服了!”
俩人走出那片地儿,迎上前去。
来的人向他们出示了工作证之后,高个子说:“两位大爷,上面有指示,让我们通知你们,这里的林地属于国家所有,要求你们停止种地,铲除秧苗。”
听说要铲除秧苗,老七心里很不痛快,说:“同志,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小煤矿占地挖煤你们不管,我们开点儿地种庄稼却不让,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
“是啊,我们退休的老头子,开点儿地容易吗?”老九附和着说。
“两位老大爷别动肝火,这样会气坏了身子。实话和你们说,这是上面的最新政策,为了是保护环境。”高个子耐心地说,又指了指周边的山坡说,“你们再看看,咱们这里的山原来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们一比就知道了,这些山再继续荒芜,都对不起我们子孙后代。再说了,你们在这贫瘠的土壤里种植庄稼也不会带来什么收益。国家准备投入一部分资金在这里植树,目的是恢复生态环境,这对改变矿山面貌也算是好事儿。你们二老看我说的是不是在理儿?”
“你说有道理,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希望你们理解并配合我们工作。”
七哥沉默片刻,看了老九一眼,说:“老九啊,看来咱们的‘根据地要保不住了,唉……人不走运,喝凉水也塞牙。”
矮个子中年男子说:“大伯,这不是运气不运气的事情,国家政策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啊!如果你们身体允许的话,可以为我们义务植树护林,既可打发闲余时间,又能在一起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岂不更好?”
“这话中听,顺耳。我们不能像那些开小煤窑的人只知道挖煤,破坏树木,不知道保护这些林子,赚昧心钱。”
矮个子中年男子高兴地说:“还是老同志有觉悟,一说就通。我代表林业局郑重地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聘你们为义务护林员,周围的山地植树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也算是给你们老有所为提供条件,你们看行不?”
“嘿嘿,我同意,这是积德的好事。”七哥脸上露出了笑脸,转身问老九,“你同意不?”
老九撇着嘴,一脸不悦。“不给钱谁干!要干你干去吧。我可没那工夫,有那工夫不如在家抱孙子!”
“你这是啥觉悟?人家是信任咱们,信任比金钱更重要!”
“反正我知道,兜里没有钱,心里就发慌!”
矮个子中年男子微笑着说:“老同志,义务植树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的功德,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不过,我们林业局对你们义务护林员还是有政策的,象征性给你们补贴,你们可别嫌少啊!”
听说还有补贴,老九动了心,憨憨一笑,说:“那我同意!”
“呵呵,老九啊,你是钻钱眼儿里了。”七哥微笑着说,“虽然钱可能给少了点儿,但是,‘瓜子虽瘪暖人心啊!”
四
七哥认准了的事儿,不让干都不行。七哥领着九哥风餐露宿义务植树,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作,就连林业部门给的微薄的补贴都花在了林地上,每一棵树都成了他的命根子。
七哥拿着笔记本,老九配合着拿着小彩旗定位,走遍了这里的荒地和废弃的矿井,画出了只有自己能看明白的图,筹划着如何栽树和测算树苗的株数。林业部门按照七哥的计划,每年运来一捆捆树苗。就这样,俩人一锹一镐地挖坑栽树。七哥告诉老九:“这树苗通人性,你待它好,它就好好地生长,及时地修剪,就会长成大树。所以,咱们不能糊弄,要栽一棵成活一棵。”
他们一干就是十几年,一片片荒山变了模样,与庞大的林区连成了片。每当春夏季节,走进林子里,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有了一眼望不到边的生机。动物又回来了,林子有了灵气,置身其中,七哥心情特别好。日渐增多的鸟儿的鸣叫声、小动物穿行草丛发出的 “沙沙”声成了他心中最美妙的交响曲。
到了秋天,山林一片金黄,有风刮过,刹那间一地斑驳。踏着松软的地,七哥像个顽童撒欢儿地奔跑,累了,就躺在那里,他总觉得躺在山地上比躺在自家的床上还舒服,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成就感。
老伴儿埋怨道:“这一天的只想着栽树,把家当宿舍,把我当空气,也不知道你咋想的,一分钱拿不回来,总拿那些受奖励的红本本忽悠我,图个啥?”
七哥急了眼:“这叫荣誉。既然义务给国家做事,还要什么钱?只要山上不撂荒就行了!” 七哥已经把全部的心思用在了植树护林上,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棵树木。
这天,七哥的小舅子突然登门拜访,知道姐夫喜欢喝酒,买来两瓶名酒。这让七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犯嘀咕,小舅子平时也不来,向来出手不大方,人到中年才娶上媳妇,结婚这么多年不曾端过他家的饭碗。“今天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呢?亏你有心来看你姐夫,还拎来这么好的酒。”七哥边说边仔细打量小舅子,带点儿讽刺意味,“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快说吧,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舍得花钱来看我?”
“姐夫,我,我……”小舅子拘谨地有些语无伦次,“我要建一个房子,需要点儿松木杆,现在手头紧,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在山上砍点儿……”
“那怎么能行呢?这是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情,也不是人干的事儿。千万别打这个主意, 这是犯法,我看你好日子过够了,还想搭上我蹲监狱啊?”
“姐夫,我不是你小舅子嘛!能帮就帮,不能帮就拉倒,何必大动肝火数落我!”
“正因为你是我小舅子,我才这么说,违法的事情咱们不能干,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七哥站起,翻开柜子找出一张存折,递给了小舅子,“这里有两千元钱,拿去买木材吧,密码问你姐姐。”
“谢谢姐夫,这酒……”
“你给我拎走,瓶装酒再好俺也不稀罕,喝惯了小烧酒。等你房子建好了,我去喝喜酒!”
天刚刚放亮,七哥领着老九就起床了,每天巡山两次,每次都要绕着自己的责任区一圈儿,一圈儿十多公里,一趟下来至少四个小时。 七哥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每年穿破三双胶鞋。脱掉胶鞋,他那宽大的脚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
转眼到了数九寒天,山川白皑皑。寒风在雪地上打着旋儿,像吹着大片的流沙,不断地移动细小的雪粒,瞬间刮起了“大烟泡”。这天,七哥和老九在山下巡视,看到通往山上的路有车辙,立即警觉起来。沿着车辙,痕迹渐趋明晰,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深山。
山坳里,伐木声声。不远处倒下了几棵比碗口还粗的树木,四五个人吐着哈气儿,挥舞着斧子劈着树的枝杈。七哥红了眼,奋不顾身地奔跑中吼道:“他妈的,住手,竟敢盗伐树木!”七哥的声音响彻山谷。
七哥步步紧逼,他们居然没有逃,他们手持斧头和电动锯,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七哥他们。随后,重新启动电动锯,又连续伐倒几棵大树。俩人挥动着手臂疾步奔去,上前阻止。七哥更火了,对着盗贼吼叫:“我的树啊,龟孙,谁让你们干的?快说,是谁?”接着上前抱住了一个正在伐树的盗贼,电锯在这个盗贼手里“嗡嗡”地作响,俩人滚在了一起,险些被电动锯扫在大腿上。
其他的盗伐者见到了此景,惊呆了,放下手中的工具,将俩人分开。这时,一个人向这边走来,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这人身材魁梧,方形脸,两腮青青,一脸凶相。他手提一把板斧走到七哥的面前,那张猪肝色的脸上露出狰狞,大声地说:“怎么?七哥,不认识我了?”
七哥一愣,觉得很面熟,却又想不起来。“认识又能怎么样?你们这是违法,跟我去投案自首!”
“吆嗬,老东西,退休了还管起了闲事来了。告诉你,是我领着干的。让开,谁挡我的财路,我就和谁没完!”
七哥伸手捋去了胡须上的霜,眉毛立了起来,怒斥道:“龟孙,你敢!我就不相信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曲二驴子啊,狗改不了吃屎!龟孙,这回我还真管定了!”
曲二驴子的突然出现让老七深感意外。自从王二嫂的丈夫那场事故之后,曲二驴子因多次违章被矿开除了。正逢小煤矿遍地开花的时候,一向品行不端的曲二驴子联络一些地痞流氓,霸占了他人的两个小窑。经营一段时间,小窑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许多人,他弃矿而逃。不到三年的工夫,他用钱平了事儿,逃避了罪责,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煤炭公司的老总。时间不长,又东窗事发,涉嫌行贿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老账新账一起算,弄得倾家荡产,经历了八年的牢狱之灾。刑满释放之后,恶习不改,纠集了以前的狱友,打起了盗伐木材的主意。几经得手,尝到了甜头,未料到在这里遇到了“管事儿”的七哥。
五
曲二驴子见七哥没有退缩的意思,觉得遇到了硬茬儿,立刻变了脸:“七哥啊,咱们曾在一个班工作,一个槽子里吃过饭,虽然我们以前有过节儿,那都是过了八百年的事情了,希望你念过去的情分,抬抬手儿,权当没看见,你们可以安安全全回去。”曲二驴子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五张百元钞票递了过去,“拿着,你们回去买酒喝!”
“龟孙,少来这一套!你把当我什么人了?”七哥手一挡,胳膊一扬,钞票在空中飘散。
见七哥软硬不吃,曲二驴子指着白茫茫的山野,耐着性子说:“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好好地想一想,三分钟过后,我们可就动手了……”
“前些年下井,王二嫂的丈夫让你害死了,难道这回连我们这两个老头子也不放过?”
曲二驴子叫嚣着:“别和我扯犊子,再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曲二驴子劝说让其改变主意别再跟着老七坚持。
寒风中,七哥紧紧地盯着老九,坚定、明亮的眼睛似巍峨的大山那样威严。大声对胆小怕事的老九说:“别怕,他们不敢怎么样!”听了七哥的话,老九赶忙挣脱,回到了老七身边,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平时懦弱的老九,哪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从曲二驴子冷漠的神情中捕捉到了越来越恐惧的东西。他心里没底,挽着七哥胳膊的手始终在颤抖。低声地说:“他们人多,我们要吃亏的!”
七哥镇定自若地对老九说:“老九啊,腰板挺起来,当一回有骨气的男人!”
老九努力地挺了挺腰板儿,脸儿却僵硬,明显感觉到腿软了。
曲二驴子像猎狗在雪地上徘徊,突然走到他们跟前,手拽住了七哥领口,恶狠狠地说:“老不死的,一根筋啊!我看你活腻了!”冲着其他人喊道,“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绑了,让他在山里待一夜,冻成冰棍儿。”
曲二驴子冲着七哥冷笑着说:“不相信是吧?这回让你长长见识!”
一名盗贼手拿着绳子上前协助曲二驴子将七哥绑得结结实实。
站在一旁的老九胆战心惊地苦苦哀求:“论年龄,我们是你们父辈,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儿人性?”
“闭嘴!再嚷嚷,连你也绑了!”曲二驴子厉声道。
老九露出不安的神色,干瞪着眼,凝视着灰茫茫的天空。
“老九,给我挺住!”七哥又冲着曲二驴子等人骂道,“龟孙,你们就不怕当千古的罪人?早晚要有报应,不会有好下场的!”
曲二驴子没有理会,与另一个盗贼推搡着七哥的臂膀向一棵大树走去。
这时,老九眼球恐惧地鼓了出来,呼吸也似乎停止了。他忐忑地观测逃跑路线。就在三个盗贼不断地回望七哥之时,他憋足了劲儿,迈开了脚步发疯地朝着另一个方向的树林里跑去。”
“不好了,人跑了!”三个盗贼边喊边在后面追赶。
“老九,你这个傻狍子,那边危险!”七哥在大声喊。七哥知道,这里有数不清的废弃小窑,被雪和草覆盖后,人是很难躲避的。
只想逃脱的老九像惊弓之鸟,不顾一切地奔跑。忽然,他跌倒了,只好在雪地上往山下滚。当他滚落在一个斜坡时,“啊”的一声,掉进了一座废弃的小窑里,没了踪影。盗贼来到小窑洞口看了看,告诉曲二驴子,老九八成摔死了。
“啊?摔死了?”曲二驴子未料到弄出了人命。惶恐中,撇下盗伐的工具和车四处逃窜。
七哥艰难地走近盗贼遗弃的板斧前,将手腕的绳索割开后,立即向废弃矿井跑去,疾呼老九,却没有听到回音。
“老九啊,你傻呵呵的,如果听我的话……”七哥伤心地坐在废井边,迎着刺骨的寒风,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被泪水浸湿的袖口已经冻得硬邦邦的,腮帮上浓密的胡茬子挂满了冰霜。
他忽然隐约地听到了老九微弱的呼叫声:“快救救我!”
没错,是老九的声音,七哥趴在洞口,“老九,你还活着!”他嘴唇在颤动,内心无比地欣喜和激动。
他不知道这井有多深,也不知道老九什么情况。凭着自己这点儿力气是很难救出的,只能下山找人施救。他告诉老九:“等着我,别急,马上叫人来救你!” 说完,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赶。
老九得救了,曲二驴子等人也被绳之以法,两个老友悲喜交加、欣喜若狂。
俩人来到了“王二嫂小吃”庆祝一番。一杯高粱烧酒下肚,老九打开了话匣子:“那天,幸亏废井垮落了许多土石,洞很浅,你叫醒了我,救了我。来,这杯酒我敬你!”
俩人一饮而尽。七哥调侃道:“老九啊,这回咱们为护这片林子,真是有惊无险啊!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老哥儿俩不醉不归!”俩人回忆山上与曲二驴子斗智斗勇的情节,感慨老兄弟之间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越说越激动,推杯换盏喝得天昏地暗,最后摇摇晃晃各自地回了家。
第二天,林业局的领导从公安机关获悉两位老友的感人事迹之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前去探望,送去了慰问金。令人遗憾的是,老九饮酒回家后,昏睡了过去再没有醒来……
七哥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刚刚醒时,后脑勺像灌了铅似的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才渐渐好了一些。这时,从窗外传来老九的老伴儿的嚎啕大哭声。七哥穿上衣服来到院子中,妻子急匆匆回来,责怪他:“死老头子,你把老九喝死了,这回你该消停了!”
“这是真的?”七哥有些疑问。
“我还能开这个玩笑嘛?”
七哥的胸口顿时觉得重重地挨了一拳,心里一阵酸痛,他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身体随着哭泣而颤动,歇斯底里地喊着:“老九,我的好兄弟,这么多年我们出生入死在一起没有大碍,却在阴沟里翻船……”
七哥悲伤至极,一遍一遍地重复:“老九,哥对不住你啊!”他两眼发直,费劲地站起来,向老九家走去。
李载丰:笔名心梦润笔、寒山卧雪、老黑。男,汉族,1964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党办主任。黑龙江省煤矿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鸡西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鸡西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网络签约作家。曾在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小说和长篇小说百余篇,12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雪山英雄传奇》《想爱》《炼欲》《煤矿安全小故事100则》,纪实文学《蹚水过河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