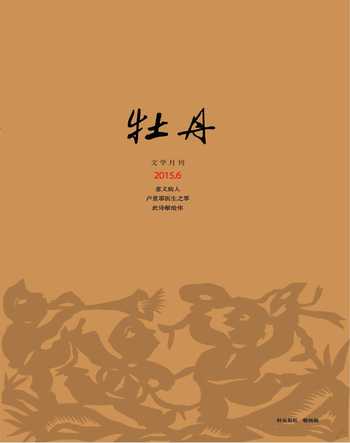绯闻落幕
卢浩林,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有散文《烟花三月下扬州》《泰山挑夫》《石榴花开》等和中篇小说《几日行云何处去》《残局》《机会》《落月》等。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接到S的电话,说约了几个老朋友想到老四川餐馆小聚,问我能不能参加。
“不时不节的,这时候聚什么会呀?”
“没听说吗,你住过的那条老街马上就要整体拆除了,改建仿古一条街。我想,那里毕竟有过我们的青春过往,不如提前去凭吊一下。再说了,也真的想老四川了,这会儿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估计,这也就是我们在老四川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听S的话,我蓦然意识到,不觉中搬离老街已近二十年了。此刻想起,脚下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熟悉的青石板路,光滑、坚韧,还有丝丝绵绵的亲切。
“都约到谁了?”
S说了,几个人的音容笑貌在时隔近二十年后于顷刻间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现在再见,不知道还能认出来几个。”
S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起来:“你把大家都忘了,他们可是时常提到你。这顿饭你请得了,弥补一下在情感上对我们的亏欠吧。”
“放心,我一定带足银子。”
放下电话,我在原地呆立半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频繁地搬迁,现在居住的新城区离老城区,前后也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或许因为知道老街始终在那里,从来不用担心哪一天想起来去找它时它会不在,所以,自打搬离那里始终不曾再回去过,而突然间,它真的就要不在了,连同它所承载的一切就要从我所熟悉的那个空间彻底消失。还有S说的那个“老四川”,曾经是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餐馆,就在老街尽头的拐角处,门面不大,是个小二层,环境很干净,饭菜口味儿特别好,无论大小聚会,我们都喜欢首选川菜馆。人多的时候就把几张小桌子对在一起,点上几个特色川菜,一个个吃得伸舌头冒汗的。如果是一两个朋友相约,就要了排骨面或是担担面,再加一瓶用色料染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小瓶汽水儿,吃得不亦乐乎。由于经常去,和这家老板熟悉得彼此都做起了朋友。还记得那是个矮个子女人,戴深度近视镜,黑镜框大得出奇,也许是镜片放大的缘故,她的眼睛也显得格外的大,加上天生的一张阔嘴,脸型就显得短宽,像是四川妹子,张口却是满嘴的本地话,而且招待人时的热情和活泛又远远强过了本地生意人那副无端傲慢的做派。她还有个绝活儿,记人,只要是第二次进入这家菜馆,她一定能记得你:“来了。还是一碗抄手,不要香葱花?”
一点一滴地想起,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而这尘封的过往,在不久的将来,将永远失去它的载体,那段历史将无从翻起,蓦然间,感觉生命中的一段儿似乎也将要被拿去,竟有些怅然若失。
聚会约在晚上六点半,但我已是心猿意马,最终,索性丢下手头的活儿,拿了件风衣动身了。不远处,那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连同发生在其中的青春故事,连同这些故事中一个个人物,开始拼命地撕扯起那段近乎已荒芜了的记忆。
那时,我初涉文坛,刚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小散文,刚认识了文艺圈里的几个文友,正满怀憧憬地陶醉在五彩缤纷的文学梦中。那时,各种文艺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唱得正热闹,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市,也沐浴进了文艺的春天,文学青年和文学老年都显得兴奋异常,经常用类沙龙非沙龙、类Party非Party的形式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我初来乍到,自然不是大家呼朋引伴的主要对象。一次偶然的机会,S知道我住在老街:“你和龙吟之住在一条街上呀,太好了,我们本来女生就少,以后再有活动就叫着你。”
S是写小说的,当时已是市作协会员,这一身份让我高山仰止。我迫不及待、情绪高涨地加入了她所说的活动——比较投缘的几个人隔三岔五地小聚,饮酒神侃。而活动的地点多选在小四川餐馆。很快,我就认识并熟悉了S说的龙吟之。
“你在这条街上住?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开场的。
龙吟之个子挺拔,眼睛非常大,而且明亮,炯炯有神。最招人眼的还是他的头发,卷曲及肩。S说他写诗歌,我说能看得出来。S嬉笑着说:“看出来了?”我说:“一眼就看出来了。”
“彼此彼此。我就住在这条街上,25号,张老太家的大院儿。”
“哦……那个大杂院儿呀,你家住哪间房?”
“窗户临街的那间。”
龙吟之长长地“哦”了声:“那屋子不大,你们搬来多久了?”
“一年左右吧。你是这里的老住户?听你的口气,你对这街道的房子都很熟悉。”
“没错,我从小到大都在这条街上,生于斯,也将死于斯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龙吟之又问:“你和爱人一起住?”
“不是,和父母、弟弟。”那时我连对象还八字没一撇呢。
“哦,是这样,住得太紧张了。这样吧,你们搬到我那儿,我还有空房。”
毕竟是初相识,交浅不便言深,适方才我还在腹诽这个刚认识的卷发男人的唐突,但此刻这实实在在的关心让我尽释前嫌,不禁心头一热,对他的好感油然而生:“谢谢你的好意,我们现在也是过渡,再有一年左右我们的回迁楼就交工了,很快就搬走了。”
“哦,你们是搬迁户。可也真是,你都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竟从来没在街上碰到过。现在知道我们是街坊邻居了,以后有需要帮忙的言语声。”他边说边用手拨拉一下我的头发。是因为我的年轻还是因为我留的头发太短、偏男性化,这种亲昵彻底让我认可了这个街坊大哥。
“你多长时间烫一次头发?”这话竟脱口而出,完全没有了初相识的拘谨。
“嗨,哥们儿,仔细看清楚啰,我这可是自来卷儿。看这英俊的脸,两鬓络腮胡,如果留起来也是卷的。来、来、来,感受一下。”龙吟之还真就拉我的手摸他的卷发。手下的发很柔软,我不无艳羡地说:“要是长在我头上该有多好。”
“想要卷发呀,好办,哥哥明天带你到理发店去。”
圈里的人都喜欢龙吟之的豪放,他奔放着自己,感染着别人,在他身上,星星点点感觉到的都是一个真。而龙吟之豪放之气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喝酒的时候有力拔山兮的气概。他酒量很大,但他醉酒的次数最多,这是大家有意为之的,几乎每次都以龙吟之微醉或大醉收场,连那个戴高度近视镜的女老板都会一次次护着龙吟之说话:“你们就让他少喝两杯吧,都知道他不吃劝的。再这样哄他喝不卖酒给你们了。”
有几次,我也试图阻止,却被S不易察觉地拦下。本以为S是为我好,不想让我陷入喝酒男人们的胡闹中,直到有一次送酒醉后的龙吟之回家,才知道事情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那天依旧是他醉了,醉得不能自己,被几个男人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我本打算回家,却被S拉住:“走吧,一块儿去送吧。”
我知道S是要等那几个男的一起走的,碍于情面,我陪着S跟在后面。
这是我第一次到龙吟之家。进大门,过一个窄窄长长的门洞,置身一个院落。院落左边有宽约一米的走廊,走廊两边连接的是五六根木柱和一排临街房。院落右边是进后院的二道门,门槛很高,门后有影壁墙,绕过影壁墙,闪出又一个院落,一排正房和两排厢房,有两个窗在亮着灯。
“这院子里全是他家的房子?”我悄悄问S。
“听说以前是。后面还有一个套院呢。现在前后院都让收了,只给他家留了这中间的一块儿。”
“嘿嘿,要是不解放,龙吟之现在还是少爷呢。”
“回来了。”一个脆生生的女人的声音,随着声音,从一个亮灯的房间走出人来,是个身材窈窕的女人,因为在人群后,看不太清容颜,只见她盘着大发髻,衬托得额头光洁异常。那晚,月光如水,场景亦真亦幻,这个女人恍若从古时走来。
“媳妇儿,我回来了。”龙吟之傻笑着喊道。
透过人群缝隙,只见她把龙吟之从男人们手中接过去,然后把龙吟之的一条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连扛带拉地拖着醉酒的人往屋里拖,边走边困难地回头道:“谢谢哦谢谢了,麻烦你们了,不好意思哦。”一口南方口音。这个女人就是龙吟之的妻子玉玉。
“谁帮忙把人扶到屋里呀。”我看着不忍,在后面小声提醒前面的同伙。
“玉玉有办法,我们不用管,走吧。”S拉起我调头往回走。
重新来到大街上,S叹道:“龙吟之真是好福气,摊上好脾气媳妇儿,放在别人身上早发作了。”
“就是的!你说偶尔一次喝多了还说得过去,可他三天两头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我深有同感,随声附和。
“她有什么受不了的,龙吟之能继续和她过不和她离婚已经是不错了。这种女人!”有男人说。
“嘘,小声点儿,夜深人静的,让人听去了多不好。”S急忙制止。
“这有什么,我就是说了,不是看着龙吟之的面子,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唾弃她。呸!”
“得了吧,几口猫尿就这样,别狗拿耗子了。”
“什么狗拿耗子,我这叫路见不平,懂吗?”
那晚,我知道了,玉玉有男女作风问题。当时我震惊到了极点,邻家大哥的女人,那个盘着大发髻的端庄的女人,我感到难以置信:“啊?真的呀?”
“什么叫真的呀,圈子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什么叫无风不起浪吗?即便是捕风捉影,那也得有风、有影儿不是?当然,我们宁信其无。”
“那一定是有了。”听S言之凿凿,而且大家都知道,是已经被坐实了的事情,我没有不信的道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滋味儿。
“龙吟之他知道吗?”
“我们都猜测,八成他是知道的。你也知道,咱们这些活动,他张罗的次数最多,你说,如果不是心里不痛快,他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他天天这样醉醺醺的,十天有九天都不清醒,十有八九是在麻醉自己。所以,有时候也知道你是好心想劝他少喝,我总拦住你,龙吟之他这也是借酒消愁,不喝他难受,所以,干脆别劝,让他一醉解千愁,权当是作为朋友成全他呗。”
“既然如此,离了得了,这不是活受罪吗?”
“离?说得轻巧。且不说都是死要面子的人,龙吟之现在下岗在家,尽管在我们这里他是有些名气的诗人,可靠这点儿知名度,发表两首诗歌,赚的稿费不够他打牙祭的。他老婆是国企高管,工资高,生活还不全靠老婆撑着?离了,他今后靠什么过日子?”
“他家不是有空房吗?可以租出去呀。”
“现在是有,可如果真闹离婚,财产分割,他就不一定有了。龙吟之为人不错,单纯,讲义气,我们也不想看到他潦倒,所以,大家都很小心不去捅破这张窗户纸。”
原来有这样一个同盟,而我在得知这样一个同盟存在之后义无反顾地成了同盟中的一员,很轻易地就把我的街坊大哥放在了同盟的对立面,既然大家都这样做了,我深信,这是对他好的。
这是一种非光明磊落的默契,大家心照不宣地怂恿着龙吟之放浪形骸。只要是龙吟之安排的饭局,有事儿的人也会把天大的事儿给推了,义无反顾地应约。在大家的潜意识中,其他人请客,可以去应酬,也可以不去,而赴龙吟之的酒宴,便是使命在身,这使命就是让龙吟之酩酊大醉,帮他摆脱苦恼,帮他天天以半醉半醒的混沌状态惩罚他妻子的不轨,因为是使命,所以,责无旁贷。如此以来,更加助长了龙吟之请客的热情,他自我感觉太有面子了。不觉中,龙吟之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他最终也被这个怪圈漩进了无底的深渊。
杨潇是带着光环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从省城回来的年轻女诗人,出过两本诗集。在当时,出书对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是件多么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所以,认识杨潇自然成了我心向往之的事情。而在众人口中的杨潇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两年前在文坛崭露头角,没几天便不辞而别,说是到省城发展去了。这让一心一意想要栽培她的市作协很没面子。有人冷嘲热讽,小池养不住大金鱼;有人更加赤裸裸了:见了两次省诗刊主编就奔了人家去了,是准备走发展的捷径呢……但这些怎么可以影响到杨潇的再次出现?
和杨潇见面那天,是深冬的一个晚上,她穿着几乎拖地的长裙登场了。
“杨潇,著名的女诗人。”有人介绍,情绪的高亢有些夸张:“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更另类了呀。”S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巴掌,无可无不可地说。
“你也认识她?”
“谈不上认识,见过一两次面,那时爱穿喇叭裤,大红大绿的。现在改成夏装冬穿了。”
杨潇的着装即使在当下看起来也有些戏剧化,裙摆怎么可以那么长?不走路连脚都看不到。
“有很多老朋友呀。”只见杨潇把目光从我们脸上一一扫过,对尤其熟悉的人,还会特意走上前做些拍肩膀搂膀子之类的动作。
“真放得开。还真没拿自己当外人。”我从不觉得S是爱嫉妒的人,但对杨潇她的非议好像就多了些。再看大家五花八门的表情,我有些担心这饭局的场面会尴尬起来。但很快发现,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看着大家真真假假的面孔,听着大家虚虚实实的逢迎,杨潇泰然自若,完全的无所谓状。而所有的对立情绪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后,便不分你我地称兄道弟起来。正所谓,敌人或是朋友都不敢妄言做到永远,永远的只有利益,更何况,我们只是一群不太正宗的文人,还有人要向杨潇讨教出书的相关环节呢。
龙吟之也是认识杨潇的,一如当初我和他初相识时他的唐突,席间就说杨潇:“不辞而别!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必须罚酒!”
杨潇来者不拒,一杯又一杯,女性中少有的海量。借酒助兴,她的谈兴正浓,用手指点在座的人:“你们哪里知道我的难言之隐?我是逃婚的,知道吗?躲到我姐姐家去了。”
“谁信!编!”
“谁编谁这么大点儿。”杨潇用大拇指掐住小拇指第一节的中间,露出上面少半段儿。
“真有这事儿?”人们兴奋地起哄。
“真的,骗你们我是孙子。”
“怎么个情况,说说看。”
“你们知道,我那时在企业,一个技术工人看上了我,天天缠着我,早晨上班,一下楼看到他在楼下站着;下班刚出厂门,又看到他在路边戳着,好像他的工作就是跟踪我似的,实在让人受不了,只好远走他乡。”
“竟有这样的事儿?你早说呀,你哥哥我打黑社会不行,可撂翻个技术员还是绰绰有余的吧。我打得他让他满地找牙,顾不上找你。”龙吟之豪气冲天地撸了撸衣袖。
众人哄笑。又有人问:“他怎么盯上你的?”
“那时候刚兴起跳舞,晚上职工食堂就改成舞厅了,一姐妹拉我去跳舞,那时我还不会,在舞厅站着看热闹。这时一个小个子男人来了,请我跳舞。我说不会,他说没关系,他带我。还别说,他带得真好,三下五除二我就学会了。”
“嗬,人家都教会你跳舞了,你就从了不得了。”
杨潇卖乖道:“他要是像我龙哥哥一样英俊,我还是可以考虑的。”继而端起酒冲龙吟之道:“哥,我敬你一杯,以后妹子再有事儿就指望你了。”
“这就对了。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对,杨潇的事儿就是龙吟之的事儿,龙吟之把杨潇包了。”
就这样,大家渐渐地把杨潇定位为龙吟之的女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开玩笑,又都在这玩笑中逼真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撮合着这两个人,推波助澜地营造着一个温床,迎合着这个玩笑,又都在其中寻找着各自的乐子和刺激。
龙吟之开始是卖醉时说杨潇是他的女人,他要保护自己的女人。后来习以为常了,醉或不醉都会叫杨潇“媳妇儿”,而杨潇更是天衣无缝地配合着,每次饭局必坐在龙吟之身边。原本以为生活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原本以为生活是不会和一群生活态度不很严肃的人十分斤斤计较的,而杨潇怀孕了,是龙吟之的孩子。
没有人在乎杨潇一天天凸显出来的肚子,毕竟这是龙吟之的事儿。我们所在意的是为这两个成年人的荒唐找到的言之凿凿的理由:“他老婆在外面不是也有人吗?兴她就不兴他呀!嘿嘿,这样也好,各忙各的,都不闲着。”我们是替龙吟之以暴制暴吗?俨然是在替天行道,我们把所发生的这一切都做成了情理之中的局,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局中作壁上观。
已位列父班的龙吟之却没有丁点儿的高兴,甚至没了往日的洒脱和豪放,连精气神儿也大不如从前,颇有颓废之态,几乎是沾酒便醉,又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沾酒。过去醉酒了,他会傻笑;如今醉或不醉,他却会哭,鼻涕一把泪一把,常搞得大家不知所措,想作些冠冕堂皇的劝说,也是无用的,谁劝他骂谁。
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好玩儿了,大家聚会本是为了寻乐子,结果老是弄得灰头土脸的不欢而散,这事儿就太不合乎常态了,开始有了另外的声音:“玩玩儿就可以了,怎么还当真弄出个孩子来了。”
“说的是,杨潇是什么样的女人,那敢碰吗?当年她要不上某诗刊主编的床,就她写的那几首诗能出诗集?还逃婚,骗谁呢?”
“她为什么又回来?还不是在那边儿混臭了。到我们这儿反倒成了香饽饽了。”
“龙吟之也是昏了头,搞婚外恋也找个靠谱的呀,你看像人家S这样儿的,这才是正经主呢。”
“去,少拿我说事儿啊,再说我和你们急。龙吟之走到这一步不都是你们撺掇的。”
“哎哎哎,这责我们可是担不起啊。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就是,还不是因为他家里的红杏出了墙。你们说,龙吟之是不是就是这命,摊不上好女人?”
世事无常,龙吟之也真就经历了祸不单行,在他还在婚外恋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时候,又被查出肝癌,晚期。
我们最后看到的龙吟之,整个脸色黄中透着惨白,眼睛更大了,仿佛只剩下了骷髅般的眼眶,里面的神韵散尽了,而腹围显得格外粗。据说,这是因为排尿困难的缘故。他少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玉玉说,已经吃不下东西了。
看到我们,他勉强地凄然一笑:“疯够了,该走了。”接着,是细细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玉玉从床头小案几上抽出面巾纸给龙吟之擦去泪,泪却再次从他眼中流出。此时,龙吟之不再看我们,而是吃力地抬手抓住玉玉:“我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原谅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我报答你!”
“胡说什么呀!这辈子我们还没过够呢。”玉玉给龙吟之擦泪,自己的泪也流了出来:“朋友们来看你,高兴点儿,啊!”
龙吟之再次看我们:“我荒唐了一辈子,后悔莫及。”龙吟之在请求玉玉的原谅?和当初我们对他们夫妻关系的判断大相径庭,我们理所当然地理解这是人之将死的慈悲。
送我们走时,玉玉的眼圈红红的,按照惯例,我们本也要安慰对方两句,却见玉玉头也不抬,看也不看我们,一改方才的态度,不冷不热地说:“你们都是忙人,以后就不要再来看他了。”
一时,我们有些讪讪的,觉得玉玉的话里有话,但毕竟龙吟之是我们的朋友,觉得还是应该说些什么。当有人刚开口发声,却被玉玉毫无悬念地打断:“不仅你们不用来看了,请转告你们那个酒肉圈儿里的朋友,都不要来看了。你们不是龙吟之的朋友,龙吟之没有你们这样的朋友。从今往后,我不想在任何场合看到你们!”玉玉说完也不等我们反应,转身进了病房,用一种尽可能显示出她的不满和愤怒的力度把门关上,把我们关在走廊上好半晌回不过神儿来。
这等于替龙吟之宣布了和我们之间的义断情绝,而且,竟把我们的文学聚会贬低为酒肉圈儿。
“走吧,都别愣着了,她一定是知道了龙吟之和杨潇的事儿,而且,认定是我们撺掇了,还不恨死我们了。”
“她不看管好自己的男人,能怪了谁去?”
“哼,她得能看得住!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她怎么去管?怎么说得出口!”
众人边说边往外走,七嘴八舌地表示着自己的愤愤不平。离开医院,不知谁提出去看杨潇,竟是一呼百应。没有人问为什么要去见杨潇,好像就是一个英雄所见略同的认定,必须去见一下杨潇,谁让玉玉冷落了这些人,并且是无礼相待呢。
联系了杨潇,一行人来到了杨潇的住处,在五楼。拾级而上,楼道有些破败,一梯四户,两家和两家门对门,中间隔着一扇门的宽度。空间非常闭塞。
打开房门,是杨潇,欲语泪先流。把我们往屋里让,是两室一厅,而那间所谓的厅仅是个容三四个人吃饭的小空间,我们几个塞在了客厅。一个中年妇女出了厨房从我们身边挤过,侧身进了一间卧室,应该是杨潇的母亲,见了来人也不招呼,仿佛不曾看见。杨潇把我们让进另一间卧室,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刚从医院来,情形不是太好。”有人说,口气有些伤感。
“你打算怎么办?”又有人问,口气十分关切。被探访者的泪一下开始奔涌,众人沉默。
“我不知道。”杨潇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无奈地说:“我一直不知道。龙吟之也一直没说我们该怎么办。我本想把孩子生下来他总会有个说法吧,可现在……”
众人面面相觑,并感到几分尴尬,杨潇在赌,而我们在场的人,对所发生的这一切,谁又能脱得了始作俑者的指责呢?
我们只能讪讪地说些不关痛痒、于事无补的一箩筐废话,只是,这次没有被听者无情地打断罢了。
最终,我们没再见到龙吟之,甚至没能和他的遗体告别,仅在报纸看到了关于他的讣告,追悼会后发的,告知,龙吟之因病已于某年某月去世,感谢大家生前对他的关心及生病期间的探望。自此,杨潇也再没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中。而我们那所谓的文学聚会不久也无疾而终。
“嗨,早来了?发什么呆呢?看你老半天了。”是S,她摇下车窗探出脑袋,“上车。”有些日子没见,她看起来更加青春了,时尚的沙宣发型让她显得既成熟又干练。
我抬腕看表,还有些时间:“你找地儿停车去,我先慢慢走着。”
“好,你先晃着。”说完一踩油门儿从我身边疾驶而过。这就是S的性格,从来不啰嗦。
在岁月长河中,对那些共拥文学梦想的、曾以为志同道合者一个个丢手了,最终,依然还维系着的只有S了。现如今,她在本市晚报做编辑,前些年偶尔还能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散文,现在她的名字仍可见诸报端,XX版编辑,而她的文字却销声匿迹了。聚了散,散了聚,缘起缘灭,无非如此,甚至有的根本无从追忆。
渐渐地,天黑下来了,街两边的老房子毫不费力地就把人带进一种遥远的苍茫中,和林立的大楼与喧哗的闹市形成了绝对的反差。境随心生、物为心役,一时间,竟对老街充满了无限的留恋。
暮色中,S已停好车向我走来,她身穿烟灰色的保暖打底裤,卡其色的外套,头上又多了顶米白色的绒帽,远远看去就像个妙龄女子从古巷中款款走来。接近了,是淡淡的香。
“刚才看你在龙吟之家门口站了半天,又想起他来了?”
“刚认识龙吟之的时候,他说自己要生于斯,死于斯,如果他活着,这个愿望怕是实现不了了。”
“世事变迁,都是昙花一现呀,觉得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昨天。”
“一晃十几年了,龙吟之的妻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应该不住在这儿了吧。你想,她现在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会主席,也是领导了。都知道自来水效益好,听说职工们都不止一套房子,她一定也搬走了。再说,睹物思情,如果换作我,一定会搬走的。”
人到中年的玉玉不光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会主席,还是市人大代表,我在人代会分组名单中见到过她,但几天会议下来竟然无缘遇见,其实,即便相见又能说些什么呢?
“那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听说现在国外读书。也就是玉玉了,倒比孩子的亲生母亲还要好些。”
当年,年轻的杨潇最终还是生下了龙吟之的孩子,是个女婴。当时,我们都感叹爱情力量的伟大,感叹杨潇的坚韧和勇气,而杨潇却出其不意地做出了令大家瞠目结舌的事情,她把孩子留给了玉玉一走了之,至今杳如黄鹤。
“你说哪有这样不靠谱的,说好就好了,说有就有了,说生就生了,说扔下就扔下了。只是玉玉怎么就肯答应杨潇,如果是我,恨也恨死了。”每提此事S都忿忿的,尤其是在我们相继做了母亲。
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替杨潇想过,这个闯祸的女孩子,避祸远走时心中是否坦然,是不是能在春夏秋冬的每个夜晚都能安然入眠,我深信,当婴儿出生时那种撕裂的痛一定会在,而且将伴她终生,而当年铸就的错也会像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沉重,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来消融它,哪里还会有她改正的机会,会不会还有人愿意给她改正错误的机会,谁让这错是不可逆转的呢。
倒是玉玉,从男人们口中不齿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可歌可泣的伟大女性,或许,这也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梦想,无论自己在外面如何游荡,家总能成为他休憩的港湾,而且,这个港湾中总有一个女人始终在为他摇动着黄手帕,并张开了温热的胸等他归来。
“想想玉玉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龙吟之在的时候,天天守个醉醺醺的男人。男人不在了,独自一人还得替偷了自己男人的女人拉扯大一个孩子。她即便年轻时闹出些什么绯闻,能做到这一步也真算可以了。”S感慨道。
“是啊,现在看来,她那点儿事儿又算什么,至少和龙吟之的荒唐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
“玉玉的事儿到底是怎么传开的?”
“谁知道!我也是听圈儿里的人传的。”
“她到底是和他们单位的谁好了?”
“谁知道!”
竟然如此!
“走吧,时间差不多了,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也好非也好,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看来,在S心中,有和我一样的结。是啊,当初我们都做过些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曾经年轻过吗?
回头再看走过来的路,已淹没在黑夜中,要不了多久,这里将会被夷为平地,再现世人眼前的将是仿古一条街,而过往是再也不能重现了,我们无论背负的是什么,都只能往前走。
责任编辑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