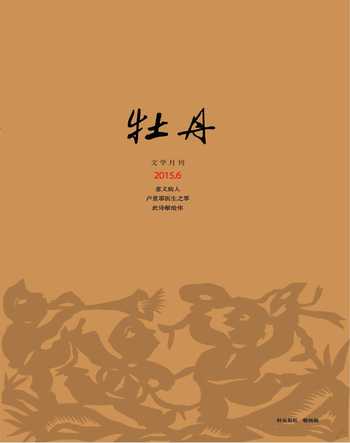红色玫瑰
刘玉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哲学讲师。后在欧洲游学,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游记。回国后曾任广告公司总经理,并曾为中央电视台创作公益广告脚本。近年来在《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杂文多篇,也创作有电影、微电影剧本等。
我觉得夏小玲的父母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太不恰当,这个名字适合一个白净瘦弱的小姑娘,说话声音细细的,像叮叮当当的小风铃;而她不白,反倒是有点黑,鼻子倒是很挺拔,眼睛像电影里的吉普赛人,不光是说外形,还有目光,相当野性,高兴的时候很美,生气的时候很冷艳。我怀疑她父母有点外族的血统,比如大唐时来中原的什么外族人。所以她的名字应该是诸如夏殷红、夏紫燕什么的,才配得上她长相的浓重。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本名都快被人遗忘了,我们大院的人都叫她“假小子”,尤其是大人们,提到她时连连摇头:“那假小子,哪像是知识分子家的女孩子!”
跟她的长相相比,大家一般最先记住她的嗓音,上小学的时候就粗粗的,声还特大,经常是老远就听见她跟男孩子在吵架,或者是在打架,货真价实地跟他们在土里滚着打,赢了就小公鸡一样地叉腰昂头大笑,输了就一边哭一边还骂着,鼻涕眼泪抹一脸。但过一天之后她就又跟他们混在一起玩了,弹球、烟盒什么的。
那天我从大院里的一小片桃林经过,看着那光滑的树皮,像是闪着暗暗光泽的淡枣红色的缎子。正欣赏着,突然从树上跳下一个人,吓得我拔腿就跑,心里想:这回是真的碰到传说中的流氓了!跑了两步,听背后的“流氓”大喊:“别跑,是我,夏小玲!”我恼怒她害我失了面子,差点揍她一顿,琢磨一下还真可能打不过这野丫头,就虎着脸问她想干吗?她竟有点扭扭捏捏地说想跟我们一起玩儿,我想了想就勉强同意了。
虽然有我做主加她玩儿,但没玩几次她就被人轰出了局。她不会跟别人相处,自我、霸道、不知进退,一会儿有人被她弄哭,一会儿有人跟她吵起来,最后闹得大家集体整她。有一次玩捉迷藏的时候,轮到她找,大家事先商量好了,在她蒙着眼睛没数到一百前都偷偷跑回家去了,把她一人晾在那里。我那次正好去晚了,看见她呆呆地站在那儿,没了平时凶巴巴的样子,眼里含着泪没掉下来,看见我也没说话,转身走了。
第一次去她家就让我惊着了。正要敲门的时候,听见里面哇啦哇啦一片喊,像是在争吵,就侧耳听了一会儿,只听一个男人,应该是夏小玲的爸爸,正在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想气死老子啊!在自己家当起小偷来了,想让我把你抽死啊?”接着是响亮的一声,我跟着哆嗦了一下。夏小玲的哭声出来了:“我不是偷,我跟你说了你偏不同意!”她爸爸大吼:“废话!不同意就是不许你买!”我不小心碰了门,门忽地开了,一个横眉立目的大男人站在我面前,以前远远地见过他,印象还挺好,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普通讲师,成了一个犄角旮旯学问的教授是很久以后的事,长得帅,穿得也挺讲究,见了人一概很热情。他看了我几秒后竟变成了笑脸:“你是小玲的同学吧,进来进来。”我正不知应如何是好,夏小玲从屋里蹦出来,脸上还挂着泪呢,却笑成一朵花,把我拉进屋里。
以前听院里的大人和小伙伴们说起过,夏小玲的妈妈大概五、六年前去世了,她爸爸又结了婚,生了一个弟弟,她爸爸、妈妈只宠着弟弟,不喜欢她。这些话我原本并没太信,但到了她家一次就都信了。她继母是个娇滴滴的南方美人,我进去的时候正在心闲气定地给儿子剪指甲,只冷淡地对我点点头,刚才父女间的狂风暴雨好像也根本没听见;她弟弟那么干净秀气、安静害羞,像个扮成男孩的小姑娘。夏小玲的书桌上摆着一个相框,是她故去的妈妈和幼小的她,好家伙,她的容貌可真是从她妈那儿刻出来的 。
后来我去过她家好多次,在她那又脏又乱的八平米小屋里议论一些大院里的事儿。她爸爸在我去多了之后不再绷着了,当着我的面也凶狠地骂女儿,她继母好像就没说过话,老迈的奶奶总是小声唠唠叨叨地抱怨什么。我一去夏小玲就特高兴,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一会儿像猴子一样蹲在地上,一会儿从抽屉里翻出几个干巴巴的话梅让我吃,我说:“你安静点行吗?”她就安静那么一会儿。我经常说她:“看你那样儿,那么好的头发也不好好梳一下,乱糟糟的,衣服上沾着饭嘎嘣儿,裤子短得吊起来了,你家大人也不管你?”她一般都是把指甲放在嘴里啃,不回答我,有时就说:“要是我有你这么个姐姐就好了。”
上初一的时候,学校来了个姓杨的年轻女音乐老师,不是特别漂亮,却像她的姓一样特别洋气,也特别活泼,唱歌跳舞弹琴都好,也没有老师的臭架子,课间还跟我们说笑,男生、女生立刻都崇拜她了。她组织一个合唱队,大家一窝蜂报名,会唱不会唱的都去了。没想到,刚练了两次,一个女生就因为得了肝炎休学了。杨老师说还得补一个,我就推荐了夏小玲,大家一听都说不行,没听过她唱歌,而且人脏了吧唧、野了吧唧的,我说我听过她瞎唱,嗓子挺不错的,脏、野什么的能改吧?
合唱队再次活动的时候我带夏小玲来了,她特意穿得比较干净整齐,头发也洗了。她看着有点紧张,我说:“你就照平常那样唱就行。”她问:“那唱什么呀?”我说:“随便,老师就是听听你嗓子怎么样。”她站在杨老师的钢琴前局促得直卷衣角,几个合唱队的女生带着点优越感看着她,但等她一开始唱,我们立刻都傻了眼。她唱了一首《快乐的小箩筐》,是我们最怕的歌,速度快、音域宽、最后的音相当高,她却唱得轻松自如。唱完后杨老师把她拉到身边,看着她,起码有一分钟没说话,把她都看毛了,又局促起来,直到听见老师说让她参加合唱队才笑了。我这才又想起一个关于她妈妈的传言,说是她妈妈有夜莺般的歌喉,一场大病之后倒了嗓,不久以后就去世了。
这之后夏小玲每周一次跟我一起参加合唱队的练习,她一下子就成了我们里面最出色的,练声的时候她不但一个人的音量把我们都压住了,而且从低到高都相当顺滑,不像我们经常磕磕巴巴的。练歌的时候杨老师常让我们单独唱一下,我们都推三挡四尽量往后撤,唱之前又咳嗽又清嗓子,好像总也不是最佳状态;夏小玲就不这样,一要单唱就显出兴奋不已的样子,两眼放光,脚下一蹿一蹿的像是要出栏的赛马,若是老师问谁愿意第一个唱她立刻举手,然后站一个自以为好看的丁字步,琴声一起张嘴就唱,没经过训练不知克制的大音量在教室里嗡嗡回响。
虽然夏小玲很快就当了领唱,但若是没有我罩着她,她早就被孤立了。她显得很没有教养,不懂得谦虚、低调,也不知道照顾别人的情绪,自己唱得好就洋洋得意,别人唱得差就嘲笑挖苦,演出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拿衣服、提包什么的也没她的事儿,那自私劲儿经常让我大动肝火,也没少训她。
全区汇演的时候,上台后大家有点紧张,先是起音的时候不太齐,中间又有一个同学抢了拍,这么一来本应该与奖项无缘了,但夏小玲领唱得实在是好,下面的观众频频鼓掌,最后合唱队得了个三等奖。我们之前练得挺好的,杨老师指望我们得起码二等奖,所以她对最后的结果不太满意,只对领唱的夏小玲大加赞扬,弄得我们女生集体嫉妒起来,小声议论:又不是独唱,再怎么说也不能就是她一人的功劳吧?我那天回家的时候也没等她,跟大家一起一窝蜂似的跑了,中间回头看了一眼,她一个人在后面慢慢走,可怜巴巴的。
放暑假前,有一天夏小玲在放学的路上堵住我,脸色绯红,一副兴奋得不得了的样子,把我拉到小桃树林里,扔下书包,蹿上一棵她常呆的树,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你自己在这儿发疯吧!”转身要走,她连忙跳下树来拉住我:“今天我们班上音乐课的时候,杨老师问我家住哪里,说过几天文工团的人要去我家,他们看了咱们区里的演出,挑中我了。”我听了有点发愣,问她:“那你去吗?”她单脚着地转了一圈:“当然啦!”我问:“那不上学了?”她说:“团里有一批我这么大的,每天上午文化课,下午练唱。”
过了几天,合唱队活动的时候,夏小玲来晚了,神情沮丧、额头上有一处擦伤,也没抹药,结了很薄的痂。大家都围过来,杨老师问她怎么了?她就哇地哭起来:“我爸不让我去!”除了我和老师,其他人都不知道她被文工团挑上的事,在老师把她拉到一边去安慰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们,引得一片羡慕加嫉妒。
那个暑假是夏小玲跟我做同学的最后一个多月,也是我们相处最多的一段。文工团的人踏破门槛地上门求,她爸就是不同意,说出了无数的理由,就是有一条理由没说出口:“我女儿不能去当戏子!”夏小玲撒泼打滚地跟她爸闹,好几次都是当着我的面,又哭又喊,躺在地上,鼻涕眼泪流一身,她爸指着她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去了就成女流氓了,我可不能让你给老子去丢那个人!”有时候我在她啃着指甲不说话,乌黑的眼睛望向虚无的某处时劝她:“要不然你就别去了,不去能死呀?”她每次都是那句话:“我要去唱歌!”我觉得那时候她并没那么热爱唱歌,想离开家才是主要原因。后来有一天她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爸同意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他爸的,当时也没问出她来,这丫头从来藏不住话的,这次却鬼得很。
再见到夏小玲是差不多两年以后了,我刚上高中,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听见有人叫我,四顾一下,只有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孩站在前面,天呐,是夏小玲。她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穿一件合体的红色上衣,半高跟皮鞋,头发梢儿有点卷,眉眼的轮廓出来了,窄窄的鼻子耸起来,胸也开始紧绷绷起来,要不是那双标志性的大黑眼睛仍然没变,我真有点不敢认她。我本来想请她去家里坐,她摇摇头,把我拉到小桃林里,不过这回没像猴子一样蹿上树,而是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石头上,坐前还看看是不是太脏,我看着她笑,她有点不好意思。拘谨了几分钟后,我们又都放开了,我说了几句学校同学的事后就问她文工团的生活,她眉飞色舞地讲,从练声、演出讲到生活、女伴,说到高兴处还站起来唱了几嗓子,女高音,果然比以前强多了,已经是经过一些训练的嗓音。这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我问她是不是后悔初一时离开中学,要不然可以考大学。她说:“我才不后悔呢,能离开家去唱歌,我美死了!”
夏小玲去文工团之后,在差不多我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挺帅的小伙子在一起,引起了点轰动,我的“兵”们立刻前来禀报:夏小玲有男朋友了。那时候就是上大学的人也很少有公开谈恋爱的,她这样的算挺出格,而且在之后的几年里还换了好几个,更是成了大院里大人、孩子的谈资,她爸爸那几年有点抬不起头,但女儿已经大了,估计他也没什么办法,更何况夏小玲那些高头大马的男朋友们可不是好对付的。那一阵我跟她特别疏远,觉得她已经是另一种人。
我上大学的第三年,周末经常看见夏小玲回家,她看见我总是把我叫住聊一会儿,我们又重新亲近起来。她那几年有点背,在文工团里不太受重视,没有独唱的机会,本来以她的天赋和刻苦是应该有这机会的。她一赌气,干脆要求去音乐学院进修。这要在以前不会实现,她不拍团长马屁,怎会轮上她?但这时候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歌星走穴,她们团的一些人都整天琢磨着赚钱,顾不上别的,她就如愿以偿,去音乐学院进修了一年。
时隔多年以后我又去了她家,这时她爸爸升成了教授,换了一套大些的房子,夏小玲的屋子已不再是八平米的小脏屋,而是干净漂亮的香闺。我奇怪她怎么变成个能干的人了,她笑笑说:“嗨,被逼的,团里把我们当女兵,军事化管理,练出来了。”在她张罗倒茶、拿零食的过程中,我仔细地打量周围,见书架上有不少书,文学的、音乐的居多,还有一个那时候很稀罕的日本双卡录音机,一大堆磁带,一个电唱机,一大摞唱片。桌上还放着她和她妈妈的旧合影。这时的她已经和母亲几乎一模一样了,当然,更时髦一些。和以前不同,她不再跟我议论院里的八卦,也没聊衣服和电影明星之类的话题,而是一直眉飞色舞地说她在音乐学院进修的事。在几个小时里,我几乎都没说话,一直是她在滔滔不绝,其间还给我放了几张外国歌唱家的唱片,是歌剧咏叹调。之前我没怎么听过这些,不太懂得欣赏,她一边兴奋地给我讲解,一边跟着一起哼。最后,她说得累了,一下坐倒在沙发上,脸色绯红,微微出了汗,一下子灌下去一杯茶,然后把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乌黑的眼睛里有点阴云:“唉,什么时候我也能站在舞台上唱这些咏叹调就好了。”临走时,我忍了一晚上的问题终于说出了口:“你有男朋友了吧?”她摇摇头,轻飘飘地笑笑:“没有。”这么断然的否定把我下面的话噎住了,她看看我,露出我熟悉的坏笑:“有过,行了吧?但现在没有。”下楼的时候,我停下来对送我的夏小玲说:“等你出了名,我可能就见不着你了。”
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报社当编辑,觉得没什么劲,但也不知道能怎么改变,我资质平平,并且也不是勤奋的人,名利方面的要求也不高,所以出国和考研都没考虑,平平淡淡地过,少年时代的爱好就剩下听歌,包括有时听听外国歌剧咏叹调,听的时候常常想起夏小玲。
这时的夏小玲却好像被我的吉言说中了,突然走了红。她在熬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独唱的机会,在一个晚会上,她唱的一首西北风格的情歌被大家喜欢得不行,一夜成名,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晚会上频繁出现她的身影,而且每次都要唱那首成名的歌。她的磁带也畅销,连着出了好几盘。那时候真是娱乐饥渴的时代,夏小玲的嗓音其实属美声范围,却来唱通俗歌曲,根儿并不正,但因为歌好听,她的演绎也比较灌注情感,就成名了。那两年我是真的见不到她了,她也几乎不怎么回家,不是去那儿演,就是去这儿录,整日滚在名利窝里。她爸爸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他女儿夸成了天才少女,把他自己说成是善识千里马的伯乐,经常可以看见他站在院里的马路上,跟打听他女儿的人高声大侃,伴着爽朗的大笑。
我们大院挨着一座影剧院,一般都是放电影,偶尔有晚会,那天有个难得的音乐会,我去了,是几个在国外音乐比赛中得奖歌手的演出。我的位置相当靠前,坐下之后听见邻座两个女孩小声议论:“是她吗?”“好像是,真是!”“咱找她签个名?”“我不敢。”我顺着她们的视线看过去,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背影,正是夏小玲。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这么站起来又坐下的一磨蹭,就有好几个人围到了她身边,还真不是粉丝,应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她见了他们,赶忙站起来,很谦恭,满脸堆着笑,但又落落大方,以前那个野姑娘的影子一丁点都没了。而且她这么一说话就把脸转过来了,即使没有精致的妆容,她也已经出落成了一个真正的美女,衣服也很时髦,首饰在灯光下闪烁,是个真正的明星样子了。
音乐会的水平很高,那几个得了国际奖项的歌手很有实力,歌剧咏叹调一首一首地唱。尤其那个女高音更是唱得好,不但音色、音准、气息都不错,还颇有些感染力,不像另几个,偏重技巧忽视情感。压轴是那女高音唱歌剧《托斯卡》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真是唱得相当不错。
音乐会散场后还不太晚,我正想着要不要去大门那边再溜达一会儿,听见后边有人叫我,一回头,是夏小玲。她紧走几步赶上来,要在以前我们肯定是拉住手大呼小叫,现在却互相有点拘谨,尤其是我,不知该怎么对她,客气也不是,随便也不是。别扭了一会儿,她说:“我刚才看见你了,太乱,没叫你。”我问:“你是要回家看你爸妈?”她迟疑着:“也不是,我们家人最近不在北京,我是一个人走走,想想事儿,不知不觉就进了院儿,老马识途,老窝就是老窝呀。”我说:“你觉得音乐会怎么样?”她沉默了一会儿,才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好,真好,尤其是那个女高音。”我附和:“我也觉得是,她比那几个都强。”这时候正走到一处路边长椅,她建议坐一下,等我们都坐下后她掏出烟来抽,细长的女烟,打火机小巧精致,打火时带着好听的颤音。我有点惊讶:“你抽烟?不怕毁嗓子。”她心不在焉地说:“偶尔的,不上瘾。”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名利地位的差异隔开了我们,要想再回到少年时的无拘无束不那么容易。她倒是一点都不窘,而且简直好像把我忘了,一口一口地抽烟,不说话,也不看我。我刚打算找个理由告别,她突然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踩灭,转身一把抓住我的两条胳膊,一双大眼睛离我很近:“我得走!”我吓了一跳:“去哪儿?离家出走?”她笑起来:“你糊涂了吧?我已经不是怕我爸的小姑娘啦。”她放开手,靠着椅背坐正,又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幽幽地说:“刚才那个女高音唱的时候,我在心里跟着从头唱到尾。”说完又不吭声了。实在被这种沉默压得难受,我起身告辞,她坐着没动,也没跟我说再见,只是挥了挥手。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在院里的书店撞见夏小玲的爸爸,问起她,他说她已经出国了,跟她男朋友一起走的,去了法国,那小伙子在法国有亲戚。
这之后又过了八年我才又见到夏小玲,是春节的时候,在父母家看完春节晚会,外面开始密集地放炮,本想带着女儿下楼,她胆子奇小,只好让她爸爸带着她站在阳台上看,我则像小时候一样下楼跑出去看,捂着耳朵,仰头看着像花朵一样盛开在天空中的烟花,忘乎所以地高兴。想着大门口那边烟花更漂亮,就往那边走,刚走过花池就看见夏小玲了。她穿着漂亮的皮衣,发型也洋气,臂上挽着一个挺帅的洋人,因鞭炮声大,只能看见她笑却听不见声。我站在离夏小玲不远的地方,犹豫着要不要过去,这么磨叽的当儿,她就看见我了,甩开帅男,笔直地走过来,夸张地叫着我的名字,一下子把我两条胳膊抓住了。我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里喊着问她这些年怎样了?她也喊着说在法国先是学语言,然后在音乐学院学声乐,现在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这次是回国探亲。她说这些的时候神采飞扬,像个二十出头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三十三岁的人了。我看着站在远处的洋小伙问:“你结婚了?”她摇摇头:“男朋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我慌不迭地说:“不用了,我也不会说外语。”我们匆匆告别,约好改天再聊,其实心里都明白不会再见。
虽然知道短时间不会见到了夏小玲,却没料到从那之后到现在就再也没见到,有十六年了,父母年事已高,我女儿也都已经快大学毕业了。我已经当了某个杂志的主编,头发白了,腰身粗了,每天的日子过得挺丰富,渐渐把少年时的一些伙伴也淡忘了,其中也包括夏小玲。
其实这些年也断断续续听说过一点她的情况,一个消息说她在某歌剧院唱歌剧,另一个消息又说其实就是在一个慈善活动上唱了两首歌而已。又一个消息说她嫁了洋人,生了孩子,隔了几年又说已经离了,自己带着孩子过。消息经常是二三手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有一次下大雪,我在院里正走着,看见远处一个穿红斗篷人的背影,像极了夏小玲,我在雪路上笨拙地拼命跑过去,喘得叫不出声,只得直接去拍她,她回过头来,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恼怒地瞪着我。我连忙道歉,说认错了人,她小声嘟囔一句什么转身走了。天呐!我以为的夏小玲,其实是三十年前的她,在这样的下雪天,也是穿一袭红衣,在我前面走着,我叫她,她停下来回头看着我笑,用她高亢的声音喊:“小心别摔着啊!”声音被雪吸走了一大半,我其实听不清楚,只是一边笑着一边朝她奔过去。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