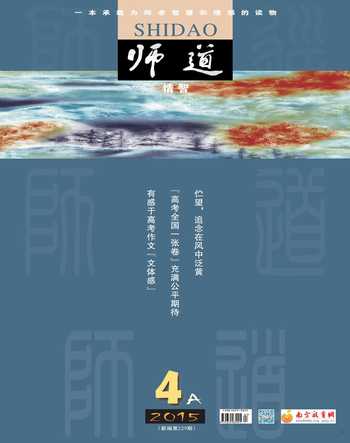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
梁昌辉
中年顾盼,别有一番兴味。回首走过的路,因为经历,因为看过的,听过的,亲身体验过的多了,自然多了一份从容与平和的心灵资本;瞩望前行的路,因为思考,因为阅读的,观察的,比较过的多了,自然多了一份温情与深刻的目光视野。
其实,就是在时间的流里精神与灵魂的磨洗。
時间,如静水深流,却也有湍急的匆匆;时间,似箭矢疾飞,竟也有漫步的闲闲。
是急还是缓?是动还是静?说得清吗?不然,怎么既有人感觉度日如年,时间好漫长;又有人说日月如梭,时间过得太快呢?连天纵英才的李白也要浩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大诗人是在感叹万物易逝,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吗?
是的,我也是只见得镜子里日渐稀疏的头发,却不知道那一根一根的白头发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更难以说清自己的时间都去了哪里。刚才还在墙角的阳光,一会儿爬到了墙上的镜子上,晃得人眼前光艳金闪的,迷离难分。
一、光阴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台湾歌手这首《光阴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致青春”,我特别喜欢它的歌名——“光阴的故事”,时间在故事里,故事在时间里。有作家这样提醒读者,我的意思不在别处,就在我的词句里。我想,我的光阴,我的时间,不在别处,它应该也在我的故事里吧。
少年时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就是作家江南雪儿散文里的瓦西河中学,我们则喜欢称之为青峰岭中学,虽然它在红印章里从来却是另外一个名字。为了节省下从家到学校八华里步行上下学的时间,从初二起我就住校了。这所冈峦之上小河之滨的中学,因为没有围墙,没有像现如今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学习安排,我们反而格外用功地读书。每日晚饭后,我们三三两两的,携着书,边走边说笑着打闹着,走到田野里,就分散开来,或站或坐,温习起功课来。
除了严寒的冬季,我们有三季都是这样的,晚饭后有一段自在地在田野里读书的时间,“走,‘野读去!”我们相互招呼着。夕阳在远天移动,深边的一棵两棵齐膝高的野草不断拉长着阴影,“苦哇”鸟(一种叫声像喊“苦哇”的水鸟,学名至今不得而知)在碧绿的秧田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我们直接感知着光阴的意义,珍惜这大自然赐予的明亮,有的默然识之,有的口中念念有词,有的干脆放声朗诵起来。
学校里是没有热水供应的,住校的学生就用刚吃完饭的搪瓷缸,向食堂的师傅从学校硕大的铁锅里讨一点热水喝。于是,“野读”时,我们便坐在田埂上,脱去鞋袜,两只脚惬意地在水里摆来荡去的,书念了,脚也洗了,那是我至今都留恋的天然足浴。
后来读了师范,到了州府,洗脚有了热水,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图书馆。学校拥有当时号称我们地区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一学期下来,图书管理员就给了我一项特权——每次可以借五本书(学生一次一般只能借两本书),这愈加怂恿了我的读书,是不用为了考试的纯粹的读书。哲学,小说,诗歌,散文,甚至建筑、绘画等,每一本书对一个缺书的乡村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九点学校熄灯,点上一盏油灯继续读;夏天的晚上,到厕所旁彻夜亮着的路灯下读;西南角生化实验室的拐角,高大的法国梧桐,喧闹的蝉嚷,于我,却是清净的读书佳处,因为无人搅扰;为了实验,也曾试过月下读书。
最浪漫的还是“郊读”。学校西边两三里外是淠河,河滩上有一个杨树林,我常去那儿读书。家祥、光鸿也是那儿的常客,我们结伴而行,到了树林则静静读书,暮色四起,再一同步行回校。有时也会朗声对诗,诵文,惹得暂居树林的船民家的看家狗一阵狂吠,我们却在它紧张又警惕的目光里大笑而去。晚霞,暮霭,星辰,月钩,也伴着这少年的笑声走进了我们创办的文学社的刊物上。
后来,我离开安徽老家到了苏南。在华士实验小学这所百年的江南乡村小学,朋友们总说起我的“走读”。其实就是边走边读,我喜欢这样悠闲地读书。走走,读读,看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还有冬天的暖阳”,和书一起走进了我的心灵里,走进了我的文字里:
长空寥廓散云纤,
满院清辉水银天。
月里流霜觉梦冷,
明灯一盏古今言。
友人“江南雪”在我的QQ空间里评论这首小诗:“有一种唯有中年过后的心绪和怀想,如一杯香醇的老酒,飘逸中有沉郁,况物中有心声,虚实相济,动静有法,有天地宇际的遥想,更有跨越时空的沧桑……”
呵呵,谬承称赞也!南朝文学家江淹在《别赋》中写到:“明月白露,光阴往来。”大约可以作为此诗的注脚。“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光阴增加的不应仅是阅历,经验,还应有心灵的舒展,内心的澄明吧。
二、时·分·秒
想你就紧张,
有你就疯狂,
你也像闹钟在我身边滴滴答答。
——于冠华,《闹钟》
和孩子一起,让我对时间与时间的流逝的认识多了一种视角,也从多年的教育与自励中累积而成的珍惜时间的观念与习惯中脱身出来,深切体悟到,对于时间,珍惜与否并不能增减它的数量,也不能改变它的价值;倒是教育家卢梭提出的“儿童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浪费时间”,让我警醒,也给我启发。
玩伴少,儿子常常喊:“爸爸,我们一起玩游戏吧。”于是,我将业余的大部分时间拿来与他一起厮磨:打弹珠,画画,打球,骑车,溜滑板,逛公园,在老家过年一起放鞭炮,长江边一起打水漂……最让妻愤怒的是我们一老一小捉迷藏了,90平方的斗室,只能爬床底,钻衣柜,一通尖叫、哄笑的结果可想而知,难怪妻明令禁止了。
最高兴的是儿子:“爸爸,你快要靠近我藏的地方时,我的心怦怦,怦怦,直跳,好紧张!”他说的“怦怦,怦怦”,让我想起了静心读书时,钟摆的伴奏。儿子比较顺利地能看钟知道时间了,但是纸上的“时间题”也难免搞不清,“一分钟大约可以走 米。”给了三个选项:A.10米,B.80米,C.300米。他选了A,因为他没有掐过秒表,感受不到1分钟到底是多长时间,一个人走起路来可以走多远。不用讲“道理”,我们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实际走了一下,他在心里感受到了1分钟的长度,不是那种“1分钟=60秒”的进率口诀记忆。
我们家有个习惯:尊重发呆!儿子四年级了,懂事了,他会告诉妻:“喏,妈妈,爸爸在发呆呢,他累了,别打扰他!”是的,发一会呆让经常快节奏工作的我很惬意,不过,儿子的话更让我心里暖暖的。儿子也会要求让他自已一个人瞎闹闹,乱想想。阳台上一大盆水,他聚精会神地策划、指挥着一场“恐龙战潜艇”的战斗。尺水兴波,光影在墙上、玻璃上,还有他红润的小脸上闪动跳跃。只有闹钟发出的“滴答,滴答”的走动声,提醒着时间的静好。
来不及,一秒钟还是一秒钟;赶紧,一分钟也不会变成61秒。“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没有游戏,还能称为童年吗?真正的成长是心灵的成长,而做梦,犯傻,幻想,游戏与亲情,都是心灵成长的良伴。长大需要慢慢的,生活也不要总是赶,毕竟我们不是去参加一场计時的跑步比赛。
三、岁月
是谁真的浪迹到天边,
是谁一直守在门前。
——沈庆,《岁月如今》
一次,十几里外的堂叔家办事,父亲同我一起去。那时我17岁,刚进师范学校。望着一贯瘦弱的父亲,自认为自己骑自行车带人已经熟练了,便对父亲说:“爸,我带你吧。”父亲笑着说“好呀”,就坐在后座上。还好,车子控制得比较平稳,我生平第一次载着父亲骑行在乡间公路上,两边是水稻收割毕的田野,黑黝黝的稻田里间或一群两群寻食的雪白的鹅。
“爸,就是这条路,我九岁那年你还用自行车拖着我去堂叔家吃喜面(六安习俗,孩子出生三天亲朋好友来祝贺,叫“吃喜面”)呢。”
“是吗?是小满子出生吧?记不大请了。”
“爸,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最盼着你能带我走亲戚。”
“哦?为什么?”
“因为可以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很带劲,小伙伴们都馋死了!”上世纪70年代,一个公社也才几辆自行车,父亲的自行车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辆。
“30年前子以父荣,30年后父以子荣啦。”念过私塾的父亲一生朴素,他不是叫我们出人头地,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自立自强。
漂泊在外的我现在很少骑自行车了,总是在大巴车碾过柏油路面的“滋滋”声中一次次回老家过年,眼看着一米七八的父亲一年比一年佝偻了,却无能为力,不能做上一点点事。晚上,我坐在父亲的被筒里,与父亲抵足聊天,汇报与问询一年的时光。伸过手去,摸摸了父亲的脚和腿,皮贴着骨头,心中酸酸的:
“爸,你太瘦了!”
“老了,都这样的,没事的。”
冬阳好时,我们会把茶水、糖果搬到院子里,大家闲叙喝茶。我喜欢搬了小凳子偎坐在父母身边,就像儿时那样。年幼的儿子跑来跑去;阳光洒在父亲母亲枯瘦的手上,灰白的头发上;他们微笑着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小孙子。陶渊明描述“桃花源”时说:“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约就是这样的天伦有乐吧。我却忽然想到了南朝诗人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的一个词:“岁月如流。”无尽的感触都在这“流”里,无形,却深入骨髓与心肺。
人与时间,我觉得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是妥帖的比喻。虽然人制造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计时工具,但是,时间依旧无形,无绳索可以将它羁留,也无箱柜可以将它保管。也许,这种思量本身即透着傻气。跟随心灵的步伐,追求精神的丰富,与亲人、身边的人一起经历故事,创造每一刻的温慰,才是时间所能让我们去做的吧。因为,我们就是时间,我们在哪儿,时间就在哪儿;因为,我们所能拥有的时间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