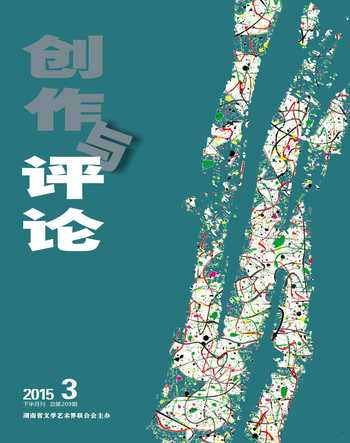文体多样和技术多元的新诗实验者
苏绍连 王觅
时间:2015年1月24日
地点:台中市苏绍连家中
苏绍连简历:
1949年12月生。台中师院毕业,曾任国小教师,现已退休。1965年开始写诗,参与创立过三个诗社:《后浪诗社》(后改名为《诗人季刊社》《龙族诗社》《台湾诗学季刊社》。网络笔名米罗·卡索,曾设“现代诗的岛屿”及“Flash超文学”网站,从事现代诗与超文本网络诗创作。现负责“吹鼓吹诗论坛”网站,并主编《台湾诗学论坛》刊物。其新浪博客“意象轰趴密室”( http://blog.sina.com.cn/u/1745607013)曾获台湾第一届文学部落格奖。著有《茫茫集》《惊心散文诗》《隐形或者变形》《台湾乡镇小孩》《童话游行》《河悲》《我牵着一匹白马》《草木有情》《大雾》《散文诗自白书》《私立小诗院》《孪生小丑的呐喊》《时间的影像》《时间的背景》等诗集。曾获《创世纪》二十周年诗创作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诗奖、联合报文学奖诗奖、国军新文艺新诗及年度诗人奖等。
王觅:苏绍连先生,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先请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有哪些重要事件影响了您的创作?
苏绍连:我的生活是比较平淡,没有什么波折。父亲和母亲开设零售米店,定居而无搬迁,生活稳定,求学过程顺利,均在台中。毕业后亦在家乡沙鹿任小学教职,直至退休,没有经历任何重要事件。我个人的人生变化是比较稳定,没有遇到什么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或者家庭变故都没有。所以创作稳定持续,乃因我生活的稳定,而非受到事件的影响。
王觅: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写新诗的?
苏绍连:最早应该是从14岁,初中时候开始练习投稿。那时候学校有一个小的刊物。进到师专,大概17、18岁,就整个投入新诗的创作,在校园的校刊发表。我的创作经历跟一般的学生一样,就是在校园先写,在校园发展。
王觅:请谈谈您接受的诗歌教育的经历?主要受到了哪些诗人和诗论家的影响?
苏绍连:我的诗歌教育就是学校的常规教育。我受正规的诗歌教育不多,没有受到现代诗的教导,接受的是传统的教学。感觉上,我的诗不是受教育体制而产生。我会写诗,或说我的写诗能力的养成,其实依靠的就是“自学”,就是多阅读,从课外读物中去读,去学习,去写。在不断的“读”与“写”两个方式中成长。我受到哪些诗人的影响?我自己不能断定或确切指出,但我可以告知我年少时期读过而较喜欢的诗人,从初中开始最早喜欢徐志摩,后来是杨焕。读师范学校时开始看到洛夫、罗门、痖弦的诗,我很喜欢,就从他们的诗里学习如何写诗。我会去研究、去分析他们的诗,找出他们的诗的特点,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会受到商禽的影响。至于诗论家的影响,我没有特定受到谁的影响,有关诗论的文章,我读得很杂。我喜欢东看西看,图书馆里有诗论就借出来读,但往往读过就遗忘,或者说是抛弃,西洋翻译的理论或中国传统诗学都一样,不会牢记。
王觅:在大陆的中小学校教学中,学生也只能学习到几首新诗,诗人的成长主要也是依靠自学。请您谈谈你自学新诗的宝贵经验,这对诗坛晚辈会有帮助。
苏绍连:其实所有自学都是通过阅读,阅读会去找自己喜欢的。当时喜欢杨焕,是因为他的诗比较有音乐性。也许所谓自学的过程一定是有模仿,模仿是从他的语言上去模仿,比如说他的语气上的,如语言的节奏,还有他的意象是怎么产生的,慢慢地去学他的意象呈现的方式。
王觅:谈到风格,我读您的诗明显觉得前后时期的风格不一样,你是如何将原先的风格变成了现在的风格?
苏绍连:我的风格确实很有变化,很明显的是我对意象没有那么重视,以前是很重视意象的词语。意象就是让你有一个画面感觉,这首诗里面所写的东西是具体的,是可以产生一个画面的。这个画面是经由你心里的那个想法,把它组织出来,把它绘出来的。现在我的转变是把意象尽量减少,减少到这首诗的意象会很少,甚至没有意象。近几年来我就是在尽量做这方面的尝试——怎么把意象减到最少。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王觅:这个很宝贵,因为现在大陆诗坛也有人在提倡“拒绝意象”,大陆拒绝意象后是在向口语诗方向走,艺术层次却降低了。
苏绍连:那不好,你把艺术层次降低了,那是非常不好的。我跟大陆的诗人不太一样,我的转变是把意象减少,是不要让一首诗里面有太多互相干扰的意象。因为一首诗里面意象包含太多,那会互相干扰。我把意象减少以后,甚至这首诗没有意象,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要用其他方法来补充,让它维持诗的本质,如它的语言的旋律或语言的变化,必须通过语言的微妙变化来加强诗性,实质上是提高了艺术质量。
王觅:您1949年12月8日生于台中县沙鹿镇,在台中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您在青少年时代不是在台北那样的大都市生活。这种平静甚至封闭的生存环境是否是您后来在诗歌道路上比台北大都市成长的诗人更富有创新性,更喜欢“标新立异”?
苏绍连:大家认为很多创新的东西,一定是在城市里产生,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才能产生。在台湾虽然我在中部,可是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得到的。我也经常到台北去,参加各种活动,但是过的主要是封闭的生活,只是封闭的生活也需要心灵开放。封闭的生存环境对人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因为被封闭,所以更想突破,突破就是创作的精神之一。但是若说比台北大都市成长的诗人更富有创新性,那可不一定。创作的“标新立异”跟现实生活的“标新立异”不尽一致。创作的“标新立异”是属于创作理念呈现上的需要、手段,但不是目的,而且是非常前卫化的创作实验行动。
王觅:您于1969年获“教育厅学生文艺创作奖”大专组小说奖。为何后来却成了诗人?您在1980年还以《线索》作品获联合报小说奖极短篇奖。在年轻的时候,您的小说创作那么优秀,后来是怎么完全转移了新诗创作上来的?小说创作对您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写小说采用叙述是否影响了您后来的散文诗的创作和长诗及叙事诗的创作?
苏绍连:文类的创作方式或有不同,但文学的原则大致是相同的。一个作者,要从内心受到什么感动才去写,不管是小说或是诗,都是一样的。我会写小说,是因为我开始接触文学,小说、诗和散文都会接触,都会尝试创作。自己后来会发现写诗比较适合自己。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语言上的精减,还有意象上的处理。还有诗的写作时间比较短,很快就可以完成一个作品。小说需要写一两千字,需要较大块的时间。写诗,可以将快乐或忧郁的心情,通过写作马上来满足。一个写作者,最好都有每种文类的创作经验,而且要从不同的文类中汲取养分,拓展自己所要创作的类别,甚至要跨越文学,到绘画、音乐等领域去。有小说创作经验,当然在写叙事诗时更能懂得怎样布局、铺陈情节,怎样运用叙述角度塑造人物的形像、说话的语境。
王觅:您的小说创作是否影响了您的散文诗创作?写小说的叙述是否影响了你的散文诗的叙述?
苏绍连:因为小说需要布局,需要结节安排,比诗更需要线索。我的散文诗有情景和情节存在,这些情节与情景与小说相近。所以会写小说,尤其是写短篇小说,有时候会写成散文诗。小说的叙述更具体一点,散文诗可能会多一些想象的空间;小说要很鲜明地、具体地表现出来,散文诗就比较模糊一点。
王觅:现在您如何看待台湾众多的诗歌奖?对台湾新诗的发展有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苏绍连:正面的影响是,写诗的人多了,教诗的人多了,谋略的诗人多了。评奖会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创作。一些老师在教学中也会将给学生分析获奖作品,会扩大诗的影响力。为了获奖,诗人就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写得更好,如何得奖,会提高诗人的创作能力。负面的影响是,有的人专门为获奖而去写诗,没有真诚的心,目的性太强,一旦没有评奖,就不写作了。评奖还会导致大家一窝蜂地模仿某种风格,可能对诗坛产生误导。
王觅:您有一首诗的题目是《异乡人》,全诗如下:“一个人,也许是姿势难看,才成为一支拐杖/行走时,两边的手流着眼泪,也许是一种疲惫/也许那人是一条漫长的路/看看天空/总在翻起破旧的鸟声/总在一架飞机下/听到婴儿的脸/向自己的眼睛里掉落//路上连绵的鞋印/也许是那人的姿势的/繁殖/开满/沉重的嘴唇,垂倒下来,吻着衰退的泥土/垂倒下来,深深埋入故乡里。”请您谈谈这首诗的创作情况?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的家园没有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成了“异乡人”?
苏绍连:对我来说,这并不是说我是“异乡人”,“异乡人”的意象或意义是精神上的。我是从很多异乡人的形象中借来的,我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并非异乡人。我的异乡人概念是从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得到的,如西方卡夫卡的小说。当然,文明发展,会使原来的乡景改变,失去原貌,人若是怀念过去,对新的家园生活便会有陌生的感觉,精神上的自己便会变成“异乡人”,这也算是一种“异乡”的性质。异乡是时间上的,而不是空间上的。如现在我呆在自己的家乡,却没有办法回去。因为今天的家乡与过去的完全不一样。
王觅:您著作众多,在儿童诗、散文诗、现代诗、图象诗、网络诗、长诗、叙事诗等多方面都有成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誉为“台湾省青年诗人最杰出的一位”,台湾诗评家萧萧指出苏绍连“所表现的生命主轴与台湾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艺术工程之多元化与多彩是台湾诗坛的珍宝”。人的精力有限,您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此高产的?尤其是您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的?
苏绍连:最重要的是你对诗有没有兴趣。当诗的创作成为兴趣,你就会坚持下去。诗成为我文学唯一表现的类型,最终再成为我个人生命存在的方式,没有退路时,这样便须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长期这么写下来,也就无令人意外了。很多创作者,都是这样的在累积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算是不少,这么多年了,创作了好几十年,也该有这些数量。
王觅:您参加和组织过多种诗社,1968年,与洪醒夫、萧文煌筹组“后浪诗社”于台中市。1971年,与林焕彰、辛牧、乔林、施善继、萧萧、景翔等人共组“龙族诗社”。1992年,与向明、白灵、李瑞腾、萧萧、渡也、游唤、尹玲等人筹办“台湾诗学季刊”社。请您谈谈诗社对您的成长和创作有何帮助?
苏绍连:参加诗社是有必要的,虽然创作是很个人的事,但有时候太过于个人,不参与活动,是不好的,应该多与诗友交流。诗社是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多少也会受到影响,有些讨论活动对创作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团体结社也只不过是对诗坛的一种关心和奉献,有些人的创作会跟着诗社推展的议题而前进,但也有些人仍是自己走自己的。我大致是折中的取舍,该怎么创作仍是很个人的事,还是要走个人的路。
王觅:请您谈谈“台湾诗学季刊”社的历史,它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诗学研究刊物,在海内外,尤其是在大陆有巨大的影响。我父亲王珂自从1997年在福建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认识白灵、萧萧后,一直收到赠刊。对他的新诗研究很有帮助。“台湾诗学季刊”社集结了台湾最优秀的诗论家、诗评家及新诗教授,您的主要身份是诗人,与这些理论家接触,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苏绍连:对,没有错,现在“台湾诗学季刊”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学者,其他基本上都是教授。我觉得创作应该在理论之前,我会去读理论家的理论,但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理论与我创作不见得是一回事,所以创作不一定会跟着理论走。“台湾诗学季刊”社的历史纪录,在诗刊很容易查到。《台湾诗学季刊》后来改为《台湾诗学学刊》和《吹鼓吹诗论坛》,都很自然,大家都没有异议。但“台湾诗学季刊”社开始结社也并非标榜学院,可是后来发展增加的同仁都是学院学者,所以十周年后改为“学刊”论文定位。至于在学院强大的理论家之间,只有我和向明师非学院,创作是否会受理论家影响,问问向明师或许和我答案会一致:创作先于理论,创作怎能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如果诗人想用他的作品来证明某种理论,自然会受到理论的影响。
王觅:您是否认为诗人知道理论多了,会妨碍诗的创作?
苏绍连:会出问题的,不在于理论,而在于诗人本身的能力,动与不动,碍与不碍,都是诗人自己产生的。
王觅:台湾诗社众多,您如何评价台湾诗社对台湾新诗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苏绍连:诗社众多,但能对台湾新诗的走向有所影响的,并不多。小众影响的仍是小众,大多的诗社壁垒分明,各自攻城略地,各自发展自己的园地,发展自己的读者。不少是昙花一现的诗社,能领山头的都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证明,只有能够长期存在下来的诗社才能有较大的价值。台湾的诗社能影响新诗的,首要诗社的社员出现杰出的诗人,要有好诗人来代表他的诗社,才能对诗坛才生影响。其次是诗社办的活动,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能创造好议题,鼓动诗潮,才能产生影响。诗社多,若无上述两项,则诗社多并不会对诗坛有影响。
王觅:您写过的诗的文体多种多样,新诗文体及诗体主要有三大资源:古代汉诗、外国诗歌和中国民间诗歌,哪一种对您的影响最大?
苏绍连:都有影响,是综合性的影响,一个诗人的吸收和阅读都是多方面的,三方面都会看。但仅是某个创作时期的影响。比较起来,没有什么是最大的影响。
王觅:您用古代汉诗的四诗体写过诗,如《衰老记》,全诗如下:“落了头发/再落牙齿/忽无落泪/只见日落//忽无路径/用拐杖踩/踩入坞坑/收回拐杖/竟是,竟是/一把白骨/竟是,竟是/一条额纹/在花瓣中//竟是,竟是/一轴山水/挂在火中//忽无日落/只见泪落/月渐渐落/霜渐渐落。”您为何要用四言体?用四言体写新诗有何好处和坏处?
苏绍连:用四言体,除了是题材的需要外,也是语言的实验。因为这个题材是比较古老的题材,表现在河岸生活的情形,人类沿河而居是比较古老的。四言体也是比较古老的题材,所以我想用古老的体裁来表现比较古老的题材。没有形容词的枯瘦语句才能见骨,所以选用和诗经相同的四言体,是我唯一的考虑。这样的写法,好处是悲凉枯瘦的味道做出来了,坏处是陷入了一个语言框里,多了成为制式化。
王觅:您写诗分行排列和分诗节排列有标准吗?尤其是分诗节时是否有“固定行数”,如三行分节、四行分节和五行分节。您的《风沙》第一个诗章分别是三行、五行和二行分节,第二个诗章二行分节,第三个诗章四行分节。您是否有刻意分节的倾向?
苏绍连:没有标准。创作上不需要刻意,但是有时候为了节奏、旋律的需要,就会重视诗的分行或分节。
王觅:您的诗非常重视诗的形体,重视语言排列产生的视觉感, 您觉得诗的形体在新诗中很重要吗?为何您格外重视诗的排列?
苏绍连:如果要把诗当作图象诗,就需要格外重视排列,要看诗的题材是否需要这样做,要看表现上是否需要。因为需要,才会重要。
王觅:《台湾诗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的封底上刊发了您的两首“图象诗”,一首题为《〈金谷园〉变奏曲》,全诗如下:
楼 坠 楼 鸟 啼 怨 风 东 暮 日 楼 落 楼
楼 楼 楼 楼
楼 楼 乳 手 自 溶 西 像 楼 楼 楼
楼 楼 房 臂 颈 于 斜 脸 房 楼 楼
楼 楼 是 为 以 夜 以 的 楼 楼
楼 楼 尘 翅 下 后 像 倒 楼 楼
楼 楼 土 发 影 楼 楼
楼 楼 楼 楼
楼 人 楼 春 自 草 情 无 水 流 楼 花 楼
2000年,大陆诗评家王珂在他的著作《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中评价说:“这首诗产生了具象的楼的建筑感,人生活在楼群之中,在高耸的楼群之间,有楼的倒影,还有落花和坠人。落花和坠人两组字分别上下排列,中间留出空白,物体自上而下作自由落体运动的视觉效果极佳。如果把这首诗放在计算机上,通过自动翻页更能显示出人和花自楼顶而降的动感。最重要的是,这首诗通过形体的特殊处理,较好地呈现出现代人生活在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中的生存境况,特别是都市诗人的生存境遇。不仅在楼群间存在着坠人和落花,在楼与楼之间还存在着诗:‘楼房的倒影/像脸 像发/西斜以后/溶于夜/自颈之下/手臂为翅/乳房是尘土。”
还有一首诗是您的《〈逢入京使〉变奏曲》,全诗如下:
王珂评价说:“这首诗充分利用了自然形式的最基本规则:对称,均衡和方向性,把古典汉诗与现代汉诗巧妙地融为一体:题目是唐诗常见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和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古代汉诗;现代汉诗是:故事说完天已亮/东方太阳出来了/路上走着一匹马/马的上面似乎坐着一个人/那一个人离开了故事的结尾/继续发展成一个新的故事/没有纸笔可以写下这故事/凭着一匹马走回故园/传说那个人离奇失踪/报上登载寻人启事。全诗中所含的现代汉诗还可以从中向两边读,从左向中再向右读,可以构成多首诗,但是每首诗都有相同的主题:思乡思亲想回故园。还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机地结合:‘故园东望路漫漫,凭君传语报平安两句是古代汉语,其它诗句都是现代汉语。甚至还将传统传递信息的方式与现代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方式是凭君传语报平安,现代方式是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这种新旧的结合充分地呈现出诗人想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故园是旧的,思乡的人是新的,当代人想寻根,却处在新与旧的对抗之中,甚至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凭着一匹马走回故园,却‘传说那个人离奇失踪,这正说明‘故园东望路漫漫。全诗的图案清晰地表达出有很多条道路归故园,横的竖的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象征一条回乡的路,结局却不是‘条条道路通故园,回故园的人却失踪了,故园始终是‘路漫漫的。因为排列的奇特,这首诗在众多的台湾诗人的思乡诗中,显得更抒情、更深刻、更有艺术性。”
您为何要创作这两首诗,您同意王珂的结论吗?
苏绍连:这是我做过一系列古诗变奏的作品,将古代汉语接生到现代汉语里,在形式上去求变化,以求现代汉语诗的新貌。我同意王珂先生的论述,睿智的评论家总能见出作品的内蕴,给予作品更多展延的可观性。感谢王珂先生。
王觅:你对大陆诗歌研究者,尤其是研究您的那些研究者有何建议?
苏绍连:应该从作品本身来研究。我觉得大陆研究者会采用他们的学养来看台湾作者,也许会看到台湾作者不同的东西。台湾作者成长的语言与大陆是不一样的,应该尽量从语言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台湾作者的成长是较快的,比如说我的作品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大陆学者研究的更多是旧的作品。很多台湾诗人都有同感,大陆学者常常过分重视早期作品,对新的作品研究不够,导致不能全面研究,不能准确评价一个台湾诗人的创作。
王觅:《台湾诗学季刊》第31期(2000年夏季号)是“图案诗专号”。第33期(2000年冬季号)“现代诗学”栏目发表了丁旭辉的论文《詹冰图象诗研究》。他在文中称:“台湾现代诗人中,最早创作图象诗的应属詹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现代图象诗便生机蓬勃的发展开来了,洛夫、罗门、非马、杜国清、萧萧,罗青、苏绍连、杜十三、陈黎、罗智成、陈建宇、林耀德、罗任玲、颜爱玲等前行代、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图象诗作者,以大量而优秀的图象诗作品,将詹冰、林亨泰、白萩撒下的种子,灌溉出一座花团锦簇的图象诗花园。”您是台湾著名的图象诗人,请谈谈您所知道的台湾图象诗的历史。
苏绍连:我所知的图象诗发展情形,应与“图案诗专号”探讨的内容一样,不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看法。
王觅:您对台湾的图象诗热有何评价?
苏绍连:过去是有图象诗创作的热潮,但现在是冷却了,冷却好几年了。可能是现在的创作者认为图象诗的技巧在跨界的时代已经不重要了。现在诗的跨界已经很普遍,有些与图画联合,有的与装饰艺术联合,过去图象诗仅仅是在语言内部的变化,与跨界艺术比已经落后了。有些热潮需要诗社和诗刊来推动,才会带来热潮。不过,几乎每个诗人在诗创作的过程上,多多少少都会写几首图象诗的作品。另外,在某些诗创作比赛里,也会有图象诗和分行诗一较高下,得奖的有时是图象诗。
王觅:请谈谈您的图象诗的创作经历和经验?
苏绍连:我有段时间去做图象诗,有段时间去做散文诗,有段时间去做跨界的诗。我有过一段时间特意进行图象诗创作,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从“物形”思考,到以诗句代入物形;二是从“题材”需要,将诗句以物形呈现。
王觅:您认为图像思维会在新诗创作中越来越重要吗?
苏绍连:图像就是影像,图像思维是形象思维,图像才能产生意义。图像思维在以意象为主的诗创作是,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每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诗的表现形式,都值得尊重,都有其必要的存在价值。
王觅:长诗是新诗中定型较早、较完整和较长期稳定的诗体。闻一多认为:“我觉得布局design是文艺之要素,而在长诗中尤为必要。因为若是拿许多不相关属的短诗堆积起来,便算长诗,那长诗真没有存在底价值。有了布局,长篇便成一个多部分之总体,a composite whole,也可视为一个单位。宇宙一切的美——情绪的美,艺术的美,都在其各部分间和睦之关系,而不单在其每一部分底充实。诗中之布局正为此和睦之关系而设也。”1981年,您以《小丑之死》作品获第四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叙事诗佳作,以《大开拓》作品获第十七届国军文艺金像奖长诗铜像奖;1982年,以《雨中的庙》作品获第五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叙事诗优等奖。您的长诗写作及叙事诗写作有何创作经验?
苏绍连:我赞同闻一多的观点,长诗一定要布局。布局就是让诗的结构更宏大一点。长诗要有一个气势,气势要连贯。我非常重视布局。
王觅:您如何评价小诗?这种诗体有何优点和缺点?
苏绍连:诗体的存在,各有存在的价值,不容排斥,但是不能因为太容易写,太容易传播,就过度推崇。这是一体两面的事,优点也是缺点。视界太小,所见虽聚焦,但有局限;视界太大,所见虽广,但恐失焦。小诗要写得很大不可能,容易模糊。对一个诗人来说,小诗并不是他创作的重点。他的重点是把诗写得长一点,要有一定的格局,写长一点才能显出他的创作实力。
王觅:您如何评价近年的小诗创作热?您认为小诗还会热下去吗?
苏绍连:创作热潮,是因时代因素而现,大家追求易读、快读,全因作品量大而读者时间有限,所以创作者热中于写小诗。但物极必反,创作者仍会回来创作中长诗。只是小诗在读者的阅读方便下,是不会消失或退烧的。
王觅:从冰心到宗白华,直到当代,小诗形成了“哲理”传统,即使写小情绪,也要想办法写出哲理来,诗人的写作与其说是宣泄情绪,不如说是在记录思想,进行哲理追寻,在追求哲理的过程中,诗人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抑制自己的想象。您的小诗创作会为了说理压抑自己的情感吗?请谈谈您创作小诗的技巧?
苏绍连:诗因求其小,要限制字数和行数,任何想在有限的诗行里表现的东西,都必须浓缩和压抑。情感无法发泄到淋漓尽致。虽然要表现哲理,也只能写某一个点。有哲理却不泛述,重情感却不泛滥,小诗的表现能做到这样,就非常得宜。
王觅:近年新诗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叙述”,甚至有诗人提出拒绝“抒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苏绍连:诗中多用叙述,这是一种表现的方法。现在很多人喜欢叙述的东西,因为可以表现得很清楚。或有其目的性,写得好亦无不可。拒绝抒情,是个人的创作观念问题,个人想要什么,或不要什么,也只有尊重。诗创作是自由的,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就让时间来证明。因为写诗是自由的,你愿意抒情就抒情,愿意叙述就叙述,没有必要强求。
王觅:有人认为散文诗是散文,有人认为是诗,有人认为是独立的文体。您赞成哪种观点?
苏绍连:在我认为散文诗就是诗。但诗是什么?怎样表现才是诗?仍有很多人观念不一致。所以散文诗是怎样的文体,各地区的看法也是纷歧的。台湾和大陆的散文诗不太一样,大陆的散文诗是与诗分开的的。但是台湾的散文诗就是诗,没有分开。
王觅:您是台湾最著名的散文诗人,出版过《惊心散文诗》(1990)、《隐形或者变形》(1996)。台湾写散文诗的诗人不多,如方明出版过散文诗集《潇洒江湖》。您认为散文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是什么?它与诗和散文有何质的区别?
苏绍连:散文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就是“不分行”,它只是分段但没有分行。虽然写下来就像散文一样,但是它注重诗的本质,如音韵、意象,尤其重视想象空间。所以散文诗本质上是诗。
王觅:您1975年3月27日写了一首散文诗,题目是《七尺布》,全诗如下:“母亲只买回了七尺布,我悔恨得很,为什么不敢自己去买。我说:‘妈七尺是不 够的,要八尺才够做。母亲说:‘以前做七尺都够,难道你长高了吗?我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母亲自觉地矮了下去。/母亲仍按照旧尺码在布上画了一个我,然后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 把我剪破,把我剪开,再用针线缝我,补我,……使我成人。”请您谈谈这首诗的创作情况?为何要采用对话?
苏绍连:这首诗应用了对话。散文诗可以借鉴小说的对话,对话可以产生冲突。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对话的结构,诗用对话很好,对话也是向小说借火,点燃事件的冲突性。对话之中可以产生不同的想法。
王觅:1975年9月11日,您定了散文诗《太阳》,全诗如下:“行人的影子都晕倒长长的街上,其中唯我抱着影子痛哭,影子中有一个个我作无限久的漫游。一个个细小的我布满在所有的影子里并作忙碌的蠕动,其中唯我的影子里没有一个个我。/我面向着太阳,手指着太阳,眼映着太阳,我发现自己瘦瘦的十字身影还插在远远的太阳里。”请您谈谈这首诗的创作情况?您认为写作散文诗是否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苏绍连:对,我写诗都是需要想象的。想象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什么感动,或者什么启发,把它写出来。生命无助,人受某种威权控制,人需要救赎。此诗是为这样的意思而写。比如太阳是在控制影子,可是人就需要太阳。太阳在控制你。不管写怎样诗体的诗,都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王觅:很多人认为散文诗是美文,也是想象的文学,不方便写日常生活。但是您的《读信》却写出了“家书抵万金”的普通人的情感。全诗如下:“撕开信封,你信纸上的那些黑字游出来。…… /那些黑字兴奋地向四面八方游去,然后,自四面八方艰苦地向我游来。每个字均 含着泪光,浮浮沉沉地游着,游到了我的身体上。有的字在我的袖子里潜泳,有的字停泊在我的臂弯中,有的字失去知觉,在我的口袋里沉下去,有的字抽了筋 ,掉在我的膝盖上,有的字呛了水,搁浅在我的衣领上,有的字被我的食指弹回去,有的字在我的鼻梁上嬉戏浪花,有的字在脸颊上的泪珠里仰泳,有的字被我的眼睛救起,有的字渡不到我身上,便流失。从彼岸游到此岸,是这般兴奋又这般艰苦吗?”请谈谈这首诗的创作情况?您认为散文诗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题材和普通人的世俗情感?
苏绍连:想象与日常现实生活在创作上并不冲突,现实是真实,想象在作者的作品里面也是真实。许多现实生活的题材写入作品里,为达到文学表现的高度,不是直接采用现实,有时必要融合想象,让现实生活的题材变得精彩好看。世俗的情感会让世俗的人亲近,因为你想象中的有些情感也是现实中的,也容易使人感动。易感同身受,却也显得太直接,所以世俗的情感在文学里必须含蓄、隐藏、转化。
王觅:您觉得台湾的散文诗和大陆的散文诗有何差异?在台湾是最优秀的诗人才写散文诗,在大陆散文诗几乎成为通俗文体,人们通常是先写散文诗再写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苏绍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台湾不会先写散文诗才写诗。台湾的散文诗不会称为“美文”。“美文”指的语言的美和情感的美,二字反而是对散文诗的羞辱,像“文句词藻很美、景物描述很美、情感形容描写很美……”这样的“美”都令人作呕。散文诗写不好的人,才会把“散文诗”和“诗”分开看。
王觅:您是台湾最重要的网络诗人,您任过“台湾诗学季刊社”的论坛刊物《吹鼓吹诗论坛》主编及网站站长。您在网络上设置了“现代诗岛屿”及“flash超文学”两个个人网站,及“意象轰趴密室”部落格(博客),发表作品及回复读者的问题。由于对网络的热中及对数字诗(超文本诗)的实作,您2003年以网络笔名“米罗·卡索”的虚拟身分获得年度诗人奖。请谈谈您的网络诗及超文本诗的创作经历?
苏绍连:简单说,边学边做,学计算机语言、学软件包开发的程序,将之运用在网页制作、超文本诗制作,但本身要具有美学修养、影像和音乐的搭配能力,最基本的是要知道自己所做的作品是诗的表现,只是用网络和超文本的类型而已。1998年开始做到2004年吧。
王觅:台湾新诗学者商瑜容在2003年5月出版的《台湾诗学学刊》第一号发表了题为《米罗·卡索网络诗作的美感效应》的研究文章,高度评价了您的网络诗创作:“自1998年他开始尝试编写网络诗,并以笔名米罗·卡索在《歧路花园》和《美丽新文字》网站上,发表许多精采的作品。从一名优秀的文本作家,转战超文本的编制,其网络诗作的艺术表现,非常令人期待。”“米罗·卡索创新超文本中的互动模式,读者因而对过去的阅读经验产生否定,建立起新的视野,交流效果也得到增强。”十多年过去了,您如何评价您的网络诗作?
苏绍连:我是边学边做的,尤其是电脑语言,我用过就忘记了。草创之初,有些作品简陋,仍待精进修整,但因计算机语言的编写非我能力所及,故已放弃再进一步发展。就像一部车子,是人家做好的,我就去开,不是我的创造。你是小说家,是诗人,本身的语言能力就强,你要把超文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将音乐和美术结合在一起。我从1998年做到2004年,后来就做不下去了,原因是程序语言太难了,我不是电脑科系的,需要人家帮助。所以在2002年就开始感觉很困难,最后做不下去了。我现在看过去的网络诗的作品,我现在在检讨,觉得好的作品不多。商瑜容对我的评价并不是因为我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做得比较早,比较多。
王觅:您认为您的网络诗创作与过去的纸质诗创作有何差异?
苏绍连:网络诗需要打字,需要软体,受到工具的很大限制。工具会影响创作的方法和作品呈现的方式,超文本作品需要在计算机上操作,而静态阅读的,除了是屏幕网页的点进连结外,其它应和纸质作品无异。创作上,在网络易发表、易交流、易现也易逝。作者比较容易回应,不象纸本刊物,你发表了好久都不知道读者的反应。可是纸本比较精华,比较精致,作者刊出前会经过几次修改,创作的发表则较能经由筛选机制得到较好的作品。
王觅:您在文章《重返超文本诗的歧路花园——玩弄超文本:能变化、能探索、能互动、能操作、能游戏的诗》中说:“诗,放到了数字接口,从文本进入了超文本,似乎真的有了彻底的改变,变得似乎有神乎其技的感觉,这不仅是诗作呈现的面目大不同于平媒纸上印刷,诗人的美学思考及创作技巧挑战亦是一大跃进。”“当一名超文本数字诗的创作者,除了学会操作数字软件及工具外,仍得回归到创作艺术本身的涵养,懂得对诗文学质地的坚持与拓展,再把诗观念应用于超文本形式上,让它成为真正具有诗质的超文本作品,给阅读者有诗的感受。”请您总结“超文本诗”的特点?
苏绍连:“超文本诗”的基本特点是:能变化,能探索,能互动,能操作,能游戏。因为它需要用电脑、用滑鼠、用键盘,跟读者互动,作品本身会变化,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有不确定性,会有多向性,会让你得到声光效果的享受。一个很美,很完美,或者一个高科技的作品,它本身就要求很高,所以超文本作品需要很多人来共同创作,单一的一个诗人是做不到的,它需要一个团队,需要文字,需要美术,需要音乐,需要绘画图像。好的作品就需要这些结构。当然这些特点能够发展出来是很重要,但是你写诗,一定要有商业性质,买不出去,所以一个诗人要去做超文本诗作,或者文学作品,大概是做不出来的。
王觅:您认为网络给台湾诗坛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请谈谈您对台湾及整个华语世界网络诗的未来的看法?
苏绍连:网络世界,无所不通,我看写诗、读诗会更加兴盛,作者、读者会更多,并不是在减少。华语诗的网络未来,我认为诗人还是应该注重创作。同时一个聪明的作者,还需要行销。诗人,除了创作,还得有自我(或由经纪人)营销,能者,掌握发言权。网络正是最好的发表与营销的平台。未来,诗仍活跃在网络上,除非网络消失,现在还是需要网络。
王觅:台湾著名诗人林耀德在《谁在写诗》一文中认为诗坛的反动派“以诗反诗”有三个原因:(1)隐藏作者与真实作者的混淆,(2)诗坛大事与诗社动态的乱视,(3)艺术自主和政治自觉的胶着。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苏绍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种种穷山恶水、危波险浪间,他以大河式的叙述体裁验证‘现实究为何物,也以之向存在无止尽地前进。”“这九首诗贯穿了他的创造生命,呈现出一个隐藏作者发展的轨迹,他同时呈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自主与政治自觉。近十年来苏氏创办的诗社形同星散,他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值得注意的‘诗坛大事,也理所当然遭受冷漠和忽视,因为我们都不读他的诗,我们忘了他的诗才是非事件的‘大事。”您如何看待他对您的这个评价?
苏绍连:我喜欢林耀德这么说,因为他看到(或是预测)我的诗创作过程的变化面貌,是与台湾的诗创作演进变化相吻合,或说我的诗创作风格的更迭是台湾诗创作的见证。
王觅:您认为写诗有“治疗心理精神疾病”的作用吗?您写诗是在难受的时候还是高兴的时候?如果理解诗的情感宣泄功能?
苏绍连:我相信诗有疗愈的作用。诗人创作时的自我疗愈,或是读者阅读时的疗愈,都有可能。我写诗时,反而是情绪最安定、思考最沉淀的时候。写出了诗,也等于为创作者自己的情感找到出口,读者读了能代自己发声的诗,当然情感也借着诗而宣泄。
王觅:近年“方言”入诗成为潮流,台湾甚至出现了“台语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苏绍连:在地的语言,说出在地的声音,是很自然的事。诗,是语言的万花筒,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写诗,也是很正常的事。
王觅:在纷乱复杂的诗歌生态中,台湾诗歌应该如何继续良性发展?
苏绍连:不排拒,多实验,自由,交流。
王觅:您觉得诗的生态决定诗的功能吗?如台湾近年政治较动荡,诗人就较关注社会民生。您1989年直面现实,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台湾镇乡小孩——为生活在台湾土地上的孩童而写》,写了14个小孩。请您谈谈这首诗的创作过程?
苏绍连:还是我在小学任教时,对儿童的关注。那个年代,台湾城乡差异,乡镇向着起飞的城市经济学习,城市的生态亦悄悄植入乡镇,儿童也受其影响,故而想把这些现象写出来。
王觅:您认为新诗的叙事与散文或小说的叙事有何差异?是否诗的叙事在语言上更简洁和更有弹性,在手法上更重视情感性、戏剧化和意象性。
苏绍连:诗绝对是跟散文小说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语言形式,诗的语言当然是要更简洁。诗的叙事还是需要有一个方法,需要挑一个重点,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叙事。你要进入下一个地方的时候不用连词写,一定要跳跃,跳到另一点去。这种跳跃可能就是与小说散文的叙事不一样的地方。跳跃是诗的叙事的重要方法。
王觅:您对新诗的前程有何展望?
苏绍连:诗的不同世代有不同世代的背景,不同的世代造就不同的诗的面貌。前人无法干预后人,所以,对于未来怎么样,新诗的前程怎么样,应该是只有祝福,让新诗更好一点。诗是会继续存在的,是不会灭亡的。
*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项目“中国台湾新诗生态调查及文体研究”(项目编号:CYS14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台湾诗学季刊社;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