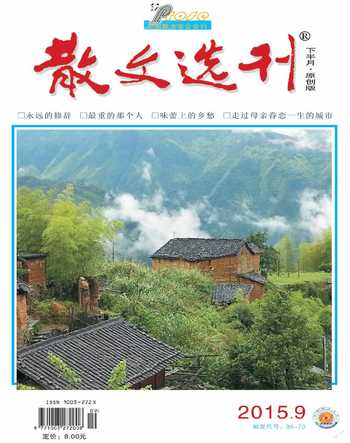我的戴海老师
吴昕孺
1985年,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进入大学后很迷茫,就附庸风雅,捉起笔写当时最流行的诗歌。由于缺乏文学训练,写得一点都不像。我在乡下长大,别的能耐没有,吃点苦不在话下。我就傻里傻气地天天想,天天写。不久,我的傻劲在校园里竟熬出了点名气,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戴海书记(这个词特别扭,原话照录)要见见你”。那时只在学校大礼堂、大操场讲台上远远地见过“书记”的,大多是听他那“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的演讲,非常佩服他能把人生、命运、奋斗等大道理讲得如庖丁解牛,丝丝入扣。
那是秋天的傍晚,岳麓山用清风和鸟语营造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戴老师在他家前坪接见我。我恭恭敬敬地捧上写诗的本子,他翻了翻,问了我几句,尔后多是鼓励的话,我只顾瞻仰他光秃的头顶,加上有些紧张,他的话没记下一句。这次会谈再无第三者旁听,但在校园里流传得很开,甚至有老师收我作义子的说法。我闻之真有“一跃龙门而身价百倍”之感,更加兢兢业业写诗,夹起尾巴做人,生怕有辱师门。
大二的暑假,我约三个同学一起自费考察湘西。老师托人送给我一张旧席,以壮行色,我们非常感动。那张苇席伴我们将近一月,行程千余里,在凤凰,在矮寨,在天子山,它好几次承载着我们四个年轻的身体,于星月下、草地上做着茫无涯际的梦。那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它对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说的,我就是在湘西知道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万古洪荒般的“魔幻”风景让我顿然明白了永恒与短暂的天壤之别。短暂之人生,如何揭开永恒的神秘面纱,以及用怎样的心灵来守护它,将成为我一生的追寻与探求。
戴老师经常从忙碌中抽出时间,约我爬爬山,或到他的办公室,再以后就去他的家,谈诗书,论人文,纵横古今。我藉此得以领略老师温蔼谨严之外的另一种性情,一旦涉猎诗文书事,他辄逸兴遄飞,眉间额上都生发起一种灵光,澎湃的激情使他手舞足蹈,表现出孩童般的天真稚拙。那时,我不揣冒昧,大胆地建议他写些文章。戴老师是演讲家,嘴上功夫已是天下一流,我劝他强化手上功夫,他并没有因为我年幼浅薄而认为我信口雌黄,他真的就胆大包天地握管向作家的专业领地挺进,他的文学人生从50岁开始。他笑称自己是“湖南年纪最大的年轻作家”,此言不虚,因为他拥有做文学最珍贵的本钱———半个多世纪真诚而又饱满的人生。
上个世纪60年代,风华正茂的青年戴海走出洞庭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旋即又迈着青春和爱情的步子,奔赴天山脚下,在绿洲与戈壁度过了一段峥嵘岁月。他的妻子,由接班人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两个年轻的心灵在寒荒大漠和浩茫苍穹间品尝人生的况味。
80年代初回到湖南,戴老师一直担任高校的领导职务,在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心目中,“戴海老师”是他们爱戴的“学生头”。他阅人、读书无数,还经常卷着铺盖去学生宿舍和“同学们”一起开卧谈会。他给学生的回信是一篇篇佳构,他和学生的谈话是一曲曲玉音。他在大江南北的学校、企业、机关作过难以数计的演讲,足行万里全因肩挑道义,舌烂莲花只缘心有活水。
半个世纪过去了。麓山回眸处,故乡、北京、新疆,万里风云奔眼底;诗书,山水,家园,千种风情涌心头。昔日的青青子衿,如今已鬓发萧疏。但意气仍在,理想仍在,向往仍在。甘苦备尝的生命阅历与生活体验在他的笔下凝成字字珠玑。他的第一本书《人生箴言录》被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眼看中,起印过万册,可谓打响了第一炮。1997年,中青社欲推出他的《秋林拾叶》,他又做了一件胆子极大的事,竟然嘱我作序。此前,我虽写过一些文字,但从未为别人的书写过序,那一般是名家的事情。我收到任务,受宠若惊,又诚惶诚恐,那序是要放在书首的,万一没有写好,岂不是佛头着粪!老师曾经说过,出书是书人的盛事、雅事,他要我这个学生为他作序,一不怕将盛事搞砸,二不怕将雅事弄俗,这个风险实在冒得太大。他则笑呵呵地打消我的顾虑:“我善出奇兵嘛。”我答道:“可惜我不会写奇文,否则奇峰并起,必有大观。”其实我心里知道,老师叫我写序,是对我最好的提携,最大的鼓励。
《秋林拾叶》出版后,反响热烈,一版再版。老师在送给我的样书上题了几句话,都是极好的性灵文字:
拨开杂草袁我的心路袁我的足迹袁或许隐约可见遥/站在山谷与你对话遥半山坡上的后生袁何日听到你的回音钥
2001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酝酿一套“阳光文丛·我们身边的佳作”,丛书面向青少年读者,他们想找既在教育界又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作者,戴海老师深孚众望,乃当然的人选,而我拣个篓子,也叨陪末座。老师出的是一本教育随笔、演讲集《坛边话语》;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声音的花朵》。老师捧着书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缘分越修越深了。
我曾有幸与老师多次出游,渡黄河,过洞庭,越鄱阳;上嵩山,爬庐山,登石钟山;游开封古城,探白鹿洞,宿星子县城……我们狎玩山水,餐饮烟霞,游戏泉石,一路上拿各种典故和风景进行对话,常常灵犀迸溢,机锋四出,每于电光石火处,拊掌大笑或仰天长啸,大有林下风致,让行人侧目。
老师是个爱生活、重感情的人。他和师母刘晓清老师这么多年来历经沧桑,相濡以沫,始终心心相印。他们的爱情故事以其特有的传统和前卫被传为佳话。我们这群调皮学生,隔三岔五地要跑到老师家里去碰撞一把,老师和我们“疯”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旁边师母那慈蔼平和的微笑,仿佛中国文化的标签,昭示着更深邃的道理和更明澈的意境。师母是气象专业的教授,但在我们印象中,她的神色与内心一律清明景和,没有阴雨,也没有风霜的痕迹。
这些年,老师因白内障视力大降,他怕见了熟人不打招呼引起误会,所以不太与人交往。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精神拓展,相反,这对公认的“神仙眷侣”不是陶醉于书本,就是浸淫于自然,每有心得,辄写成文字,与几位戴门弟子共享。
2010年是“微博元年”,老师认为这种文体十分适合他的写作方式,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他宣布进军微博圈。
“在下,姓戴名海,岳麓山下之村夫野老。退休十余年来,我在书房,在旅途,过着伏案、漫游的生活,宁静、清爽、惬意。因眼疾,不上网,自嘲漏网之鱼。去夏,女儿给我一个东西玩。玩什么?手机。今秋又听说,手机短信可以发到网上。是吗?今日试将‘戴海村语当微博。朋友,您不觉得多了一条网虫悄悄爬上脚背?啊哈,退休以来,我一向‘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而今试玩微博,闲耶?忙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这是发表于2010年11月18日的“微博开篇”,也标志着“戴海村语”正式开张。
此张一开,老师不计其数的学生、弟子,昔日同学、同事,学生与弟子的学生和弟子,同学、同事的后辈,曾亲聆老师演讲的听众,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追随者……渐渐形成一个十分稳定而可观的“粉丝群”,还有通过各种途径进村的“鬼子”,他们纷纷在“戴海村语”中搜刮营养,饕餮菁华,乘兴而来,乐而忘归。
不到两年,“戴海村语”已由当初的小村庄发展成为一个文字的殿堂。一般人侍弄微博图的是信息的方便、快捷,这可不是老师的风格。他经营微博,像办一本杂志,“说它杂树生花也好,杂草丛生也罢,我的本意就在‘杂”。杂便并不难,杂而不乱就有难度了。在“戴海村语”里,每一个进村的“鬼子”都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比如:“阅读,一种恒久的时尚”、“哲理,寓于平凡事物中”、“回忆,一条时隐时现的河流”、“卧游,于冥想中重现山山水水”,等。有一天,老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开启他微博世界的密码是十二个字:“山里山外,窗里窗外,书里书外。”我听了戏拟一联:“出入皆无影,里外不是人。”横批:“神仙生活。”他听了大笑,逼我喝下一罐高达八度的葡萄汁,弄得我醺醺然,不知今夕何夕。
别看“戴海村语”皆握拳伸掌的短小文字,但熔铸老师数十年人生阅历、经世智慧与胸中万卷书、脚底万里路的富厚和豪迈,不少篇章隽永中见宏阔,幽默间显旷达,活脱脱现代版的“世说新语”:
微博学:《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喻国明等四人著,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是科盲,说实话,连《序言》都没看懂,等于连门都没喊开。不过,我从后窗探到一点儿动静,就是此书最后一章的《微博用户深度访谈》、《新浪微博用户满意度问卷调查》。
唐诗信息:细读唐诗,找到千年以前岳麓山上的生态信息。例一,山间一道澄清的流水,为什么忽然浑浊?刘禹锡有诗:“浅流忽浊山兽过。”例二,麓山冬夜,大雪纷飞,会有什么响动?韩偓听到:“松因雪折惊鸟啼。”我住岳麓山下近30年,也有类似体验。
在银滩:去年七月,到胶东乳山避暑。地处黄海之滨的银滩,大约有200个新建的小区,处处“售楼”,处处楼空,夜间亮灯的极少。走在优雅的滨海大道上,人问:“买房了?”我答:“没。”人问:“买房吗?”我答:“不。”路遇河北来的老两口,买了房。我问:“来一趟住多久?”他说:“两个月。”我以每月600元租两间房,包括厨卫、家电,也住两个月呢。
艾青答问:1965年,在石河子,有天傍晚遇见艾青,彼此打过招呼,我问他近来写什么,他答:“小说。”诗人也写小说?我问什么书名,他答:“孩子出生了才取名。”大约十年之后,我在长沙购到他的那部作品《绿洲笔记》。读后得知,他原拟的书名是《沙漠在退却》。我理解,他想以这样的诗句,歌颂石河子人开垦绿洲的业绩。
2012年7月,20余万字的《戴海村语》由华文出版社隆重推出,蔚然成书坛之盛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序言是从各路“鬼子”中选出23位,其中有大学生、离休老干部、学者、教师、诗人、小说家、博士、编辑、电视制片人、公务员、科技工作者、网络传媒人、文化产业从业者、出版人等等,最小的18岁,最大的81岁,每人写一段话,等于召开一次“网友笔会”。所以,读者诸君在欣赏戴海老师的神仙生活之前,还得忍受23段“鬼话连篇”。这样的待遇,在其他书里面可得不到哦。
数年前,戴海老师曾将自己的五十年日记结成《逝者如斯》出版,在给一些朋友赠书时,他常在扉页上题写这样一句:“看一个少年怎样变老。”而我读《戴海村语》的感觉是,在看一位老者怎样变小。不信,大家读一段《探路》吧:
那年登黄山,初见始信峰,为着走路,撇下了。今天邀何易去登香炉峰,且当南岳“始信峰”吧,为黎老探路。我们进入诗林,踏过“石浪”,六年前的那块指路石板不见了,我凭记忆找到登高的石阶。可是,游路被竹丛灌木封闭了。我持长棍在前头扑打,谨防“竹叶青”蛇!前面一方巨石挡路,此路不通怎么办?有人喊退,有人劝我“莫着急”。我说:“这不是党交给的战斗任务,我着什么急!”我不甘心,转身下行七八百米,发现路边石上刻着“去香炉峰”。我顺其所指,拔腿即上。呀!上头跳出两行红字:“森林防火戒严期,游客至此止步!”告示写在金属板上,我用长棍敲得铛铛响。
领教了吧?可见“戴海村语”最大的“鬼子”不是别个,正是这个聪明绝顶、目中无人(老师患白内障,看不清人)、读书时静如处子、行走起来披荆斩棘的老头子!
责任编辑院黄艳秋
美术插图院黄耿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