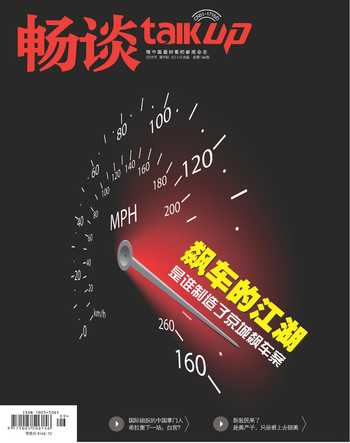宋朝人如果在闹市“飙车”该当何罪?
吴钩
不独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喜欢飙车于闹市,古时的公子哥儿也有这种坏习惯---不过那时候飙的当然不是法拉利、兰博基尼跑车,而是四条腿的宝马。
但是,纵马闹市,拉风是拉风,对公众安全却构成严重威胁。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快马撞人的场景:在河边的一条道路上,有两个人纵马驰骋,一名挑担的农民(也可能是小商贩)被撞翻在地,担子倾倒在路边,但骑马的两人并无停下来的意思,继续疾驰而去。这场“马祸”发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要是在热闹的街市上“飙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处罚?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虽出自清代宫廷画师手笔,却假托宋朝背景,宣称画的是宋朝市井风情。那么在宋朝,驰马伤人的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针对交通肇事行为,宋朝政府已有专门的立法,叫做“走车马伤杀人”罪。《宋刑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
又议曰:“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 私谓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而走车马者,不坐;虽有公私要急而走车马,因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
宋政府的这一法条,需要解释一下。
唐宋时期行文中的“走”,不是“行走”之意,而是指“疾跑”。“走车马”即是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
“无故”,指没有公私紧急事务,“公务”指急递公文、传送敕令、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务,需快马加鞭,不容逗留;“私务”指报丧、送病人治病、紧急追人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误。
“人众”,按唐宋法律的解释,“众谓三人以上”,有三个人以上即可称“众”。
也就是说,宋朝政府对市区交通实行“限速”制度,除非有公私紧急事情,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均视同“危险驾驶”,给予“笞五十”(屁股打五十小板)的刑罚。就如今天超速驾驶,不管是否造成事故,都要对驾驶员扣分。 如果因为“飙马”“飙车”而撞伤路人呢?则比照“故意伤害罪”“减一等”进行处罚。宋代刑法将故意伤害罪称为“斗杀伤”罪,根据伤势轻重给予不同量刑---以“见血为伤”,轻伤“杖八十”,导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打掉人牙齿、毁坏人耳鼻、损伤人眼睛、折断人手指脚趾、打破人腦袋、烫伤人肌肤,为重伤,“徒一年”;打掉人两颗牙齿、折断人两只手指以上,及揪掉人头发,“徒一年半”;“殴人十指并折,不堪执物”,致人终身残疾,为严重伤害,“流三千里”;因斗殴致人死亡,处绞刑;使用凶器故意杀人,处斩刑。
宋朝法律对“无故走车马伤杀人”的处罚,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相应地“减等”,比如“斗杀伤”致人终身残疾,依法应“流三千里”,而“无故走车马”致人终身残疾,则“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紧急事务要办,法律允许办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在街巷快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人受伤或死亡,则以“过失伤害罪”论处。宋朝法律对“过失伤害罪”的处罚较“故意伤害罪”轻,而且允许赎刑。赎金支付给被车马撞伤亡的人家,相当于支付经济赔偿后达成刑事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车马”,由于马匹受惊、不可控制而致人伤亡,则按过失伤害罪“减二等”论处,也允许赎刑,赎金会少一些,但同样作为经济赔偿金支付给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车马”并没有伤人,只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则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赔偿标准按“减价”即财物因受损坏而发生价值减损的那部分计算,如果致使他人财物灭失则按市价全部赔偿。
可以看出,宋朝政府针对交通肇事行为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不过执行情况如何,还需要再加考察。那时候有条件养宝马、备豪车的,想来都不是寻常家庭,非富即贵;而敢于在闹市“无故走车马者”,恐怕也要以飞扬跋扈的“官二代”‘富二代”居多。这些人有钱有势,撞伤了他人,法官对他们能够秉公执法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朱熹严惩纵马伤人的“官二代”
我不敢说宋朝的衙内之流“走车马伤杀人”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不过,许多事例表明,宋朝衙内如果触犯了法律,他们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宋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 “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少不得要干些闹市“飙马”“飙车”的勾当,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知永兴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但陈尧咨赴知永兴军上任之后,便立即严惩了这帮“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南宋时,监察御史黄用和的族人“纵恶马踏人”,黄用和也是严惩族人,并“斩其马足以谢所伤”,将踏伤人的那匹马杀掉,以弥补受害者受到的伤害。
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当地有个衙内,“跃马于市”,踏伤一小儿,伤势严重,“将死”。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将肇事者送入监狱,等候审判。次日一大早,朱熹便交待具体负责审理这起肇事案的“知录事参军”(法官):“栲治如法。”按照法律,无故于闹市内“走车马”者,先打五十板子再说。
到了晚上,知录事参军过来禀报,“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朱熹心里不大相信,亲自到监狱中查验,却见那肇事者“冠屦俨然”,哪里像是被“栲治”过的样子?原来肇事者已买通吏人,“栲治”只是虚应故事而己。朱熹大怒,立即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第二天,吏人被“杖脊”,并开除公职。
这时候,有一名相识的朋友登门拜访,对朱熹说: “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意思是说,那纵马伤人的肇事者,是个“官二代”,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但朱熹不买账,说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后来那名肇事的“官二代”受到什么处罚,朱熹没有细说,只说“遂痛责之”。若依宋朝立法,他受到的刑罚,将视那名被马踏到的小儿的伤势而定,但那名小儿最后是不是不治身亡,朱熹也没有交待清楚。因为记录这件事的是朱熹的个人谈话录,而不是司法档案,所以许多细节都语焉不详。假如那名小儿伤重不治,肇事者将按“斗殴致人死亡”之罪减一等处罚,即判处流刑——流三千里。宋朝在执行刑罚(死刑除外)时又实行“折杖法”,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脊杖二十,再配役一年。
尽管故事的细节已不可考,不过,当我们讨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飙车现象时,朱熹的这段话无疑是值得记住的: “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