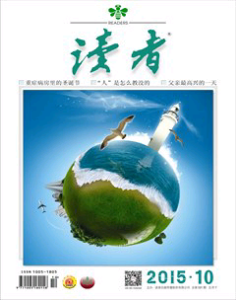那时的事
夏 天
1966年夏天,与以往不一样。一天,吃完晚饭,街坊邻居都在门口铺上席子聊天。西天是晚霞,对门老李家的指着坡下说:“那不是你家老四吗?”四姐穿军衣,扎袖标,腰间还系着武装带,短发齐耳,都认不出来了。
父亲问她:“你的大辫儿呢?”四姐说:“剪了。”
四姐是第一批红卫兵,马上要去北京。
二哥回来,没有红袖标,也要去北京。
四姐十七岁,马上初三毕业。二哥十四岁,过了秋天上初二。
没有几天,母亲下班,我们发现她那个很厚的发髻也给剪了。
父亲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嘚瑟个甚。”
母亲说:“都剪,你不剪,行吗?”
父亲问:“那个银簪子呢?”
母亲说:“给扔了,谁还兴那个。”
第二天父亲去找,在一堆标语里把银簪子扒拉出来了。
后来父母不在了,三姐把这银簪子传给了我妻子。不值什么钱,却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父母的物件。我也渐老,才认识到,我们都比不上父亲。
关节眼
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
一天半夜,有一辆摩托车从大老远开过来,声音震天响。有人喊我父亲的姓名:“王锡良!王锡良!电报!电报!北京电报!”父亲找衣服,找不到,光着身子开了门。
第一次收电报,父母慌,怕是四姐或二哥在北京闯了祸。父亲四处找剪刀,母亲等不及,用牙给撕开。父亲念,就这几个字:“今天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最最健康,我最最幸福。”
母亲一口把蜡烛吹灭,上炕躺下,骂:“养这么个彪闺女。”
父亲又把蜡烛点上,数电报上的字,说是二十三个字,得六块九毛钱啊。父亲咳嗽一宿,没再说话。
我家那条街,小八家的天京号杂货店先给抄了。小八他姥姥和姥爷,还有他爹妈都在门口跪着,旁边是坛子和账本,还有成捆的绸缎。问他们还藏了什么,不说。打他爹,他爹说了,说他老丈人在鸡窝墙里砌了金条。
第二家挨抄的是理发馆的老田。没抄出东西来。他老婆带着孩子来了,抱一个,领两个。她告诉红卫兵,老田养了个小妖精,钱物都在那里,那里还藏着大烟土。还说那个小妖精住在码头,她可以带路去揪。
那天夜里下大雨,我听见里屋父母小声说话。母亲说:“等老大回来再说,他稀罕。”父亲说:“扔,等不得。”一大早,看父亲打着雨伞,拎着大尿桶,往公用厕所那儿去。
过了多少年,我才敢问父亲这事。父亲说:“就是一台小日本的留声机,隔壁日本人岩源借咱家半袋大米,还不上,1948年遣返,就拿这个东西抵了。不扔干什么?那个关节眼,别说是日本货,就是祖宗也得扔。”
表 态
薛老师教音乐,拉风琴。她教我们唱新歌,是《丰收的歌儿飞满山》。
“苹果熟了红艳艳,一篮一篮沉甸甸。红小兵摘果脸带笑,丰收的歌儿飞满山……”
老师问:“哪一句写得最好呢?”
我举手说:“‘苹果熟了红艳艳,一篮一篮沉甸甸最好。”
老师问:“为什么呢?”
我说:“像真的一样。”
老师问:“像真的一样就好吗?”
我说:“我喜欢真的。”
老师摁下我的头,再寻找举手的。
我前排的女同学梅卫星高举起手。她说:“‘红小兵摘果脸带笑,丰收的歌儿飞满山是最好的。”
老师笑了,问:“为什么呢?”
梅卫星说:“因为‘红小兵摘果脸带笑是主题。”
老师抚摸梅卫星的头,问全班:“梅卫星同学回答得好不好啊?”
大家大声喊:“好!”
我没喊。
老师走到我跟前,说我:“怎么不表态呢?”
我低头。老师动员我表个态,我想不出话来。老师跟全班说:“来,咱们一齐鼓掌,欢迎王陆同学表个态,好吗?”
放学铃响,各班都在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脸有些变,说:“你不表态,同学们怎么能放学。‘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不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是不是?看看同学们,大家是在怎样期待你。”
全班同学向我起哄。梅卫星扭过身来,突然向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站起来,薅过她的小辫,把她的脸摁在桌子上,朝她的眼睛吐口水,口水不够,又把墨水倒在她的头发里。我背起书包往外走,薛老师拉住我,说:“你是红小兵,怎么欺负女同学?”

我说:“梅卫星的奶奶是大地主!”
梅卫星把眼泪抿到嘴里,跟老师说:“我家和我奶奶早划清界限了,我比王陆更热爱毛主席。”
薛老师不说话,擦黑板。就这么放学了。
晚上,我一五一十学给母亲听。母亲教我:“谁咬你手指头,你就咬谁脖颈子。”
后来,音乐课换了别的教师。薛老师被挂上大牌子,挨个班走,流着泪说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帮助她爹做了很多扑克,毒害了人民。
梅卫星一家随着她奶奶一齐被押送到农村。我记得是敞篷大卡车,梅卫星不上车,奶奶去拉她,她狠狠地向奶奶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去揪奶奶的头发。
多少年过去了,《丰收的歌儿飞满山》早没人唱了,但我还能唱下来。我把这歌词和乐谱发到网上,不走样,不是希望后人再唱这样的歌儿,而是希望后人能看到我和我们那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