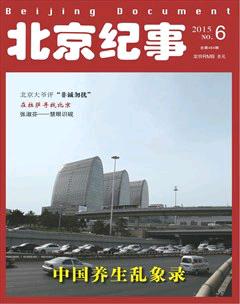一个“红卫兵”的?堕落与重生
丁品



阿朱(美增),1952年9月出生于北京市;家里有一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阿朱在文革中参加红卫兵,因打架斗殴伤人被警方拘留;后到五七干校劳动,文革结束后在京城某媒体(中国青年报行政处)供职至退休。2010年秋,笔者与阿朱一起重游干校故地,睹物伤情,阿朱竟放声痛哭。以下是阿朱的自述。
我的父亲(朱长富,原名朱长甫)是浙江湖州市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母亲是河北人,是家庭妇女。我小时,父亲对过去的事情从来缄口不谈。我只是从不同渠道断续了解到我父亲的大致历史:
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在家乡被“两丁抽一”,送到炮兵部队当兵。先是在江西受训,以后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据说还立了功。而后编入杜聿明指挥的新一军,在师长朱茂征手下做副官,当时大概是少校或中校军衔。父亲性格耿直,能双手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曾救长官于危难中,所以深得信任。后来父亲随部在印度受训,并参加缅甸远征军对日作战负伤,回国后在昆明养伤。其后在越南参加对日军受降仪式等,后来又随部队调防到锦州。
此时蒋经国任东北专员,蒋与朱茂征是浙江同乡,又是留苏时的同学,两人过从甚密,因此父亲也经常为蒋经国跑腿办事。大约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蒋经国派父亲等警卫人员护送俄裔夫人蒋方良从北平经上海回浙江奉化老家。父亲完成任务后,又奉命到台湾执行公务,而后从台湾回到上海。这时解放军已攻占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高官们纷纷带家属逃亡台湾。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认为去台湾没有前途,于是向长官提出解甲归田。长官同意了,给了我父亲800块大洋。我父亲先是回了浙江老家,以后又到上海托中共方面的朋友帮忙找事情做。经朋友介绍,我父亲到北京进入某机关(团中央,当时名称是中央青委)行政部门供职,直到1983年去世。
毛主席号召“要武嘛!”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我家里子女多,父亲工资不高,但机关年年给发补助,每年春节父亲都带几个孩子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做衣裳,一个孩子做一身新衣服,用的就是机关给的补助。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带回机关农场发的粮菜肉等实物,所以全家基本没有挨饿。
我大姐于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核工业部研究院做技术员。1959年我进入北京盔甲厂小学;1965年进入北京灯市口中学。在学校里功课成绩一般。
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被揭发出来,我以“贫农、工人”的红五类出身在学校加入了红卫兵。戴着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标感到很神气。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校红卫兵组织也参加了。那天清晨3点全体红卫兵到校集合,然后从灯市口步行开赴天安门广场,集体坐在金水桥前的华表下。各校红卫兵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口号在广场上此起彼伏。我校红卫兵组织头头不知从哪里领来了面包和汽水,给大家充饥解渴。大约在上午九十点钟,广场上高奏《东方红》和《敬爱的毛主席》等乐曲,据说毛主席已经登上了天安门,广场上人海沸腾起来了,大家都喊着“万岁”拼命往前挤。我那时个头小,在人群中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上看,只见天安门城楼上人头攒动,什么也看不清。很多人的鞋子被踩掉了,脚下到处是鞋子。金水桥前大批解放军战士拉起好几道警戒线,胳膊挽胳膊地维持秩序,但还是被冲得稀里哗啦的。接见活动到下午两三点钟才结束。
“八一八”毛主席在城楼上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还说“要武嘛!” 各地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走上街头,扮演起法西斯冲锋队员的角色,到处打人、抄家。我在北京站附近的方巾巷看到红卫兵抄家,这家里的一对老年夫妻据说是资本家,二老被拉到院子里来批斗打骂。家里的旧式家具、面料较好衣物、古代和外国的书籍等被从屋里扔出来,宣布为“封资修的破烂货”,然后拉走销毁,说是“破四旧”。
以后武斗越演越烈。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互相砸、抄、大打出手。为了收拾局面,北京红卫兵成立了“纠察队”,意在维持红卫兵内部纪律和社会秩序。我校红卫兵集体加入了“北京红卫兵东城纠察队”,分工负责维持北京火车站等地的治安秩序。当时全国“大串联”如火如荼,北京站一片混乱,我们一开始还很认真,渐渐地执勤时吃不上、喝不上,用劝说的方式维持秩序又基本没有人听,加之红卫兵组织本身纪律也很涣散,大家索性执勤个半天就各自开溜,结伴玩去了。不久 “东纠”“西纠”和“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起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部分骨干成员被捕入狱。
从“红卫兵”到“街头小霸王”
进入1968年,各学校仍一片混乱,校领导统统被打倒,老师们成立造反组织忙于夺权打派仗。所谓“复课闹革命”流于形式,相当部分中学红卫兵成为游手好闲之辈,在街头干些抢军帽、动刀耍棒、拍砖头、打群架、抢劫、“拍婆子”(拦截女生强行交朋友)之类的勾当,借以“拔份子”、称王称霸。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机关内部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我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国民党军官”,是受原机关领导包庇、隐藏下来的“反革命”。父亲在机关大院被造反派揪斗并拘禁在机关南院半年多。家里没人能管住我了,我就把心头的郁闷和怒火发泄到街头。
1969年7月的一天,我和10多个“铁哥们儿”一起去北海公园游逛,与另一群中学生不期而遇,双方开始是“犯照”(怒目而视),接着互相叫骂,到动刀子斗殴,我们抡着菜刀、锹把和自行车弹簧锁扑了上去,结果有两三人被捅伤腹部,张某(燕华)被人“开了瓢”(打破了脑袋),满头满身都是鲜血。我那时胆小,不敢上前,所以在这场恶战中没有受伤,也没有伤到别人。公园的职工立即关闭了大门,我们斗殴的这两伙人一个都没漏网,统统被抓进东、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那时拘留所里人满为患,一间屋子里关了十几口子, “佛爷”(小偷)、流氓、“野鸡”、“圈子”(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女青年)都有,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人犯统统睡稻草地铺,一天两顿窝头熬白菜萝卜汤。我被分局定为“参与流氓斗殴”,被拘留15天。然后分局让学校来人接走。这是我“一进宫”。
那时六八届毕业生已分配完毕,学校将我列入六九届毕业生分配名单。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我由于打架斗殴被拘的前科入了档,兵团来接人的干部不要我,学校也没人管我这号人,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街头流浪汉。我又和“铁哥们儿”鬼混在一起,为此还得了绰号叫“特务”和“走遍城”。
当年8月间,我又和一帮子哥们儿在故宫东华门的筒子河与人打架,这次我用军用匕首捅到对方(也是一个中学生)的腹部,顿时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我转身想跑,他一步赶上,将刀子也扎进我后腰,我捂着后腰蹲了下去,几个哥们儿七手八脚把我和另外几个受伤者送到协和医院。后来我被知情者举报,警察把我再次抓起来,这是我的“二进宫”。
我在东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被拘了一个多月,而后转送到地坛公园的斋殿,参加市公安局举办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里大约关了300多号人,我所在的大殿里关了几十号人。这里与拘留所的状况略有改善,大家挤着睡草垫地铺,但允许家属送棉被褥来,吃的伙食与拘留所大致相同。我们每天在管教干警的带领下读“毛选”、读《人民日报》社论,并要求在一周之内将社论背诵下来,否则就要被其他犯人拳打脚踢。同时,我们每天都要出操和队列军训,没有人身自由,不准外出请假。就这样我从1969年8月一直被关到1970年5月。有人传小道消息,说学习班即将解散,学习班里犯罪情况不严重、出身好、“有后门”的干部子女写下悔过书后被家人接出去当了兵,其余的300多人则要判刑、送茶淀农场劳改。我当时对自己的案子将如何定罪很着急,日夜难眠、不思茶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后悔万分。
负责审我案子的东城分局一位来自军队“支左”的管教干部叫王某(兴洲),还有一位姓白,他们审我时态度都比较和蔼。王管教告诉我,我的案子很可能定“过失伤害”罪,按当时的判案标准应判七八年有期徒刑。他还说,你没有犯罪前科,按政策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如果送去服刑劳改一生就毁了。他向分局领导建议把我送到已下放到干校劳动的父母身边去“改造”。分局领导同意了。王管教随后又找到机关军代表协商此事,军代表也同意了。我由衷感激好心的管教干部对我这个失足者的挽救。
干校,我的人生新起点
1970年6月,东城公安分局按规定注销了我的北京户口,王管教带我回家,让我收拾行李,然后“护送”我去干校。他去买了火车票,上火车后他给我打水买饭,一路上对我照顾得挺好。到达信阳后住旅馆、转长途汽车,也是他给买的票,一直把我交到干校军代表手中,他才回京复命。
报到后,驻干校军代表李某(浩)和我谈话,他鼓励我好好参加劳动锻炼、认真改造思想。还说,干好了可以调到机务连学开拖拉机。我提着行李跟父亲回到阔别两年的家,见到了母亲、妹妹弟弟。在饭桌上,父亲告诉我,组织上已经结束了对他的审查,结论是“有重大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全家都很好。他要我听从组织的安排,在劳动中磨掉身上的流氓习气!还说,干校子弟张某某,也是在北京街头打架、“拍婆子”,被警方拘留过。来干校后先是在窑厂连干活,转变快、表现好,一年多后调去机务连学技术了。
初到干校的几天,我跟着父亲在校部场院参加稻谷脱粒、翻晒和入库等劳动。我看到老红军出身的胡耀邦与其他五七战士一道,将成筐的稻谷往库房里搬运,每筐的分量足有百八十斤。他来回经常一路小跑,累得满头大汗,却极少停歇下来喘口气、喝口水,我挺佩服这个宁折不弯的“走资派”。
几天后,我提着行李去了全农场最边远的白虎冈,想到我背着个“蹲过大牢”的恶名,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心中十分郁闷。
没有想到,我的人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和二八连(均为机关干部)的“臭老九”们在大田里一起滚泥巴,很快学会了驭牛犁地、挑秧、插秧、挠秧、赶牛车、看水闸等活路。“老九”们把我当孩子,总是照顾我,让我干力所能及的轻活,并没有把我当“坏分子”看待。这让我非常感动,放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性格逐渐开朗起来。
我调到猪班养猪,胡启立是猪班的班长。他手把手地教我操作柴油机,如何粉碎猪饲料(他是北京大学机械系出身)等;我和他还一起在白虎冈上放过猪。当时二八连猪班饲养了近百头猪,个个膘肥体壮,在全干校名列前茅。
我和某杂志社副总编辑丁某某(磐石)一起放鸭子,和他同住在一个宿舍。他看我盖得单薄,半夜里将自己的一件棉大衣给我盖上,我在被窝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多年来,我已习惯对别人拳脚相加,甚至刀棒相向;也习惯了在拘留所和学习班里挤大铺,挨冻受饿,乃至忍受辱骂和拳脚。现在终于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关爱是何等的珍贵!他还在干活之余,指导我练习硬笔书法。看到我有微小的进步,就不断地鼓励我继续坚持练习,练了一段时间,我的硬笔书法还真有长进。
还有一位杂志社总编辑李某(致),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带到干校来的书可真不少,他全部图书都对我开放,唯一条件是“好借好还”,不得污损。他还自费订了参考消息、北京日报、河南日报,这在当时工资偏低的情况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鼓励我多读书读报,还经常与我讨论书中和报纸上的各种问题,使我的思想境界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升华。
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后,干校掀起“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读书热潮。受周围“老九”们的熏陶,我那时对读书学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连队发的马列6本名著和辅导材料,我都当作珍贵历史文献收藏至今。
俗话说,“人心换人心,粪土变黄金。”我拿出当初打架玩命的劲头干农活,样样不甘落后。有一次,白鹭河发洪水,半夜里我和《辅导员》杂志编辑王某(瑞)冒雨提着马灯上大堤查看水情,不料脚下一滑,我从大堤上跌入滔滔的洪水中,一下冲出去好远。幸好我的水性还不错,挣扎着顺着激流游到岸边,爬了上来,可把老王吓坏了。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想学开拖拉机的念头很强烈。于是自己跑到校部,找到驻校部生产组军代表王某某(永安),他管机务连。我说明来意,这位来自北京军区装甲兵的干部态度不冷不热,只表示要研究一下,说你先回去好好干大田吧。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白虎冈,干活也没有了精神。二八连连长赵某某(喜明,某杂志社编辑)了解到我的心思,主动出面与校革委、生产组以及机务连领导联系,介绍我一年来的工作表现,于是生产组和机务连的领导都同意我调机务连。赵某某马上把这个喜讯告诉我,后来又亲自赶驴车拉上行李,直接把我送到了机务连。我如愿以偿地开上了拖拉机!
机务连的师傅们多是我父亲的同事,徒弟也大多是我在北京的同学和邻居,大家相处得很融洽,这里同样也没有人歧视我。我也学会了尊重礼让他人、宽厚为怀,努力改掉动辄对人恶言相向、拳脚相加的暴力恶习。以后,我又通过积极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并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
在干校我获得了新生。而我的思想转变,主要是“老九”们言传身教的结果。他们是五六十年代从全国选拔到中央机关来的干部,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多,多数人文化底蕴厚、人品好、有水平,工作上有朝气,吃苦耐劳,作风朴素,没有官架子,能团结群众(包括周围农村的老乡们都喜欢有空到干校宿舍来坐一坐,拉拉家常)。70年代后期,这些同志大都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被委以重任,有的还担任省里、部委乃至中央的领导职务,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像暗夜中的灯塔,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八)
——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