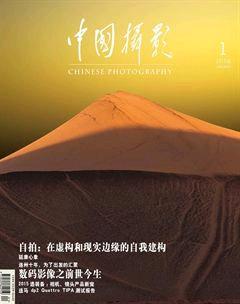摄影“灵光”考
海杰
前不久,一篇作者署名为菲戈的文章《虚假的灵光与司空见惯的异常性》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转发,文字批评指向首届北京摄影双年展的展览前言,只是该文语境是建立在北京摄影双年展巡回展的变种,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展的名为“中国当代摄影:2009-2014”的展览之中,他准确地指出了该展览部分作品“为已有的思想观念、已经变成模式的批判提供图例”的病灶,但未就这个已经在北京、武汉等地展出,并宣示了中国当代摄影2009以来这个时间射线的代表性陈词进行关照。这个在上海展出时由于自觉虚弱而砍伐了之前已有的主题“灵光与后灵光”的摄影双年展如何在题目和作品案例之间拉开了一道鸿沟,还有待我们仔细琢磨。我们不妨从题目所援引的“灵光”的源头说起,以使这个概念和其作品进行对照。
“灵光”(aura)一词源自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第一次出现是在他的《摄影小史》一文的第二章节里:“早期的人相,有一道‘灵光环绕着他们,如一种灵媒物,潜入他们的眼神中。使他们有充实与安定感。”而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对此进行强化论述。以宣布一个新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灵媒物”作为“灵光”的对应物,本雅明启用这个等同于巫术或者说萨满的魔术般的精神载体,使我们得以有理由去接近这一命名的神迹特征以及某种心灵感应,并对观者与早期人相之间的“通灵”进行辨析。在他的叙述里,“灵光”是短暂显现旋又消失的“幸福感”,是“美丽而适切”的“气韵之环”。
而他对“灵光”的确切定义事实上有赖他早期的犹太神秘主义视角,从而进入一种近似鬼魂说的视觉凝视—“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灵光”中所蕴含的死亡气息。
《摄影小史》一文我暂时没法确定写于哪一年,但该文一部分发表于1931年。至此,摄影术已经诞生90多年。本雅明之所以强调机械复制时代,是因为“摄影术发明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手不再参与图像复制的主要艺术性任务。”
本雅明所说的“灵光”的技术基础建立在早期相机无法征服黑暗的基础上,后来的相机变成了强大的光学仪器以压制黑暗,所以“灵光”开始消失。这个词有些鬼魅,就像我们现在明处,而灵光是在暗处,偶尔闪现,让我们震惊。但我们当下的处境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回放,不是一闪即逝,由于不断可以回放,以至于灵光很难存在。
早期摄影术对于人像经由时间的打磨之后散发的鬼魅和神性的灵光乍现,已成为一种交由个体感知的神学存在。“曝光过程使得被拍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间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长时的曝光过程里,他们仿佛进到影像里定居了。”
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早期人像里的“灵光”到了1880年开始消失,摄影家们开始意识到“灵光”,并进而模仿“灵光”。而后来的追随者们和阐释者们不断塑造“灵光”,比如我们在罗兰·巴特关于优秀照片衡量标准之一的“刺点”(punctum)的阐释里能看到德勒兹式的“强度”,事实上这个“刺点”是本雅明“灵光”的普及版,只不过巴特停留于刺痛感。他们所论述的观点,都是细节的宠儿,是审美的“点”,而不是巴特所说的“知面”(studinm);是时间的和精神的体验,而不是空间的物质的呈现。
在对于“灵光”的界定里,有两个时间轴影响着灵光的出现,一个是照片上的人多数成为逝者,成为曾经的存在,从而产生出遥远的怀念和古怪却又迷人的好奇,这个时间是历久弥新的,是被称为“岁月”的量化叠加;另一个时间就是灵光显现时间,它短促而又闪亮。前一个时间催生了后一个时间。由此,图像的祭仪功能被开启,而早期人像也就变成了古典主义者的视觉圣物,它看似走近我们,事实上却还是“遥远”的,它依然是信赖信众,而非观众。
本雅明选择推动“灵光”消逝的案例是法国摄影师阿特热(Eugene Atget ,又译为尤金·阿杰),在他看来,是阿特热的巴黎影像“预示了超现实主义的来临”,因为,阿特热对“墨守成规的肖像”进行“消毒”:“他下手的头一个对象就是‘灵光—也就是近年来艺术摄影致力追求的价值—把实物对象从‘灵光中解放出来。”由此,我们会惊讶地发觉,本雅明重笔描摩的“灵光”,被艺术家演化成“仿灵光”,它是“乌烟瘴气”的(这种乌烟瘴气在当下中国和相邻的日本泛滥成灾)。在他看来,阿特热唤醒了那些日常的被遗忘的景物,他的影像“把现实中的‘灵光汲干”。也就是说,阿特热用祛除“灵光”的方式体现出早已意识到的日常物的平等意义与民主性(当然不排除那是他的一个活儿,但我们在此评价它的意义是基于附着在作品上的符号意义)。而机械复制引发的能量衰减和物质性的衰落,将艺术从祭仪功能的神坛上解放,从而走向大众,即便这大众的评价机制是愚蠢的。这种对于民主性的推动,在本雅明的叙述里是一个积极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包括他在研究的祭仪价值到展演价值的演化,也都是在这个民主化的传播进程序列之中。
从他的表述里,我们可以发现,艺术神学的存在是对人格的压制,而仪式是对观看的压制,教堂是对美术馆的压制(而美术馆后来索性走向教堂)。
本雅明为什么要“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是他意识到技术对于影像平等性的意义,还是对于“灵光”消失的喟叹?在写《摄影小史》这篇文章之时,本雅明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已有几年,而他在《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将犹太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表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读者对“灵光”立场的复杂性的判断,从而他们将自己引向一个“仿灵光”的价值走向,这也是本雅明思想的复杂形象,但他对“灵光”的界定和对于阿特热所代表的“去灵光”的影像的褒奖,体现出他思想的革新意义。
“灵光”的衰退意味着我们不再被时间积压的情感与幻象的偶遇绑架,“灵光”虽使我们震动,却难以阻止新媒介的浪潮汹涌。而由“灵光”促动的审美欲求已然不能满足当代摄影的话语构建、批判与介入等社会功能的需要。
考证完“灵光”的概念,再次回到以“灵光与后灵光”为主题的摄影双年展,纵观它的时间纬度,从2009年到2014年的时间框架,旨在体现一种国家叙事下的起承转合,它遵循的是大事件背景下的时间节点。因此,我们可以由这一踪迹来纵览这200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摄影,可以得出这个特定时区的艺术批判性的总体特征,具体落实到展出作品的案例中,无论是王庆松的填鸭式的中国问题情境指涉,还是渠岩以艺术为驱动力的社会实验文本,都是着力于当下性的一种努力,断然无灵光生存的可能,即使是莫毅题为《望着我的眼睛》的去精英化的身体互动项目里,眼神也是取样式的,而非偶遇。甚至考察摄影双年展的主题构架:深浅日常、身体身份、溢出的界……几乎都是特定时代的热销术语,在这里,难觅“灵光”的神迹。作为一次中国当代摄影有固定时间区间的总结性陈词,很多本应出现的名字亦未进入摄影双年展之列。即便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付羽等人旨在宣扬的神奇执著的语言试验(这试验不是开拓,而是接近过去,这似乎是为数不多的走向“灵光”的愿景),也产生出某种在总体框架下的断裂。这模棱两可的学术梳理如何能与“灵光”勾连,几乎找不到支点,更遑论“后灵光”(这是否是“仿灵光”的语义变种?)。为何策展团队要在这样一个时刻祭出“灵光与后灵光”这个主题?是一次追逐艺术界普遍流行的学术时尚竞赛(这时尚吗?),还是一次看似总结陈词的攒展(每个策展人后面跟着一群好基友)?或者是以“后”和“超”为前缀的学术性疲乏与苍白的表征?在此,我们面向北京摄影双年展的学术合法性提出质疑,策展团队怪诞的审美愿景、对于媒介思考的滞后性以及和主题与实践的反常性分裂,令人大为不解。
展览主题与展览主体的撕扯,有如那个常常被我们用来既可以品咂古代判官的智慧,又可以测试真假母亲的夺子案,只是在这场撕扯里,主题和主体变成了真假母亲二人,小孩换成了观众—观众是最终的受害者,他们在这分裂的框架里不知所云。
如果一定要追踪“灵光”的痕迹,那么毋宁将方向引入日常家庭的相簿里,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依稀微弱的灵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断然不在当代摄影里,更何况是一个以商业化社会为背景的政治话语炼金术和短暂的时光点唱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