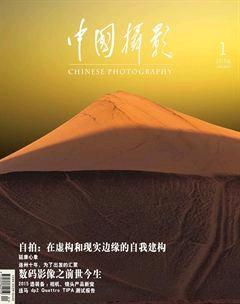宣传还是记录
《艰难岁月:爱德华·斯泰肯眼中的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是一本关于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摄影画册,也是同名展览的图录,但比一般图录厚重,书名非常直白,文字也不多。对中国读者来说,不管是要理解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还是理解摄影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仅仅这些文字是不够的。而且,展览和图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转化过程中遗失的信息非常多。这些遗失的信息就像拼图里的空白,填充起来很不容易。
美国在“一战”后期参战,以很小的代价成为战胜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许多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其中之一是倡导成立国际联盟。这是美国第一次尝试建立国际秩序,以终结国家间的丛林状态,结果是美国成了欧洲嘲笑的对象。巴黎和会对德国施加严苛的报复,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则转让给了日本。这些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端。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反应非常失望,导致孤立情绪抬头。参议院最终否决了《巴黎合约》,美国甚至没有加入自己倡导成立的国际联盟。
从那时起,厌倦、疏离和旁观者心态,就成了美国外交中固有的和周期性高涨的精神倾向。但政治上的挫折没有阻碍美国文化的兴起。“一战”后的10年被称作镀金时代。作为经济上的头号强国,美国的文化自信心在战后不断增强,批评家开始要求重估美国价值。这里面有美国人,也有以战后的新眼光重新审视美国的欧洲人。19世纪的美国作家如惠特曼、爱默生、梭罗、麦尔维尔和霍桑都顺利进入了文学史。年轻作家趁着战后欧洲物价便宜,纷纷到巴黎朝圣,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很快就崭露头角。随着纽约的“富二代”开始收藏欧洲艺术,赞助人和艺术赞助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粗鲁不文的新世界开始成为视觉艺术的中心。
1929年,纽约股市突然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0年的衰退。经济增长第一次受挫,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则继续繁荣。但萧条已经给所有的事物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危机感、大规模贫穷(托克维尔曾羡慕地说,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奴隶吃得比欧洲的穷人还好)、对贫富分化的愤怒,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1930年代不仅在制度和道德层面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艺术家的手法和理念。这种改变的后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充分显现出来。经过这次战争,美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开始跻身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和展览机构之列。1955年,MoMA摄影部举行了第一场富有世界意识(和美国意识)的展览。展览主题是“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共展出了273位摄影师拍摄的503张照片。这个展览是MoMA摄影部主任(也是著名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策划的,主题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从战争、自然灾难到儿童、爱情、死亡等等。展览空前成功,在美国的展出结束后,又在世界各地巡回展。MoMA的档案中说,最终在6大洲37个国家展出了这批照片。
关于“人类一家”的研究很多,基本上把这个展览当作“二战”后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案例来看待。展览的侧重点是人道主义。展览开幕时,“二战”结束只有10年时间,战争的记忆并没有远去,而“冷战”和朝鲜战争又加剧了危机感:那的确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生命和自由很宝贵,值得用一场战争去捍卫,但生命和自由也很廉价。很多美国老兵都见识过纳粹集中营,了解人性比兽性更凶残,深深知道何谓历史阴暗面。“二战”是自由之战,也是解放战争,但并没有消灭集中营。更多、规模更大的集中营在东方不断兴起,从冰冷西伯利亚一直延续到夹边沟,又经过寒温带、温带和亚热带,一直延伸到柬埔寨的热带雨林。人道主义是一种乐观主义,宝贵而肤浅。在那些苦难深重的地方,乐观主义很奢侈,说服力有限,反倒是在美国本土,观众们深受感动。“人类一家”这种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克服了对血腥的世界事务的厌倦感,让中部地区的农民也自觉,应该创造更合理的世界秩序,并将此看作是美国不可推卸的义务。直到奥巴马上台,这种意识形态才最终消失。但作为非洲裔留学生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女学生的长子,奥巴马当选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美国已经失去了重拾孤立主义的时机。
爱德华·斯泰肯的展览理念深受美国农业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or,缩写为FSA)1938年在纽约中央大厦举行的摄影展影响,不但如此,他还从FSA的档案里为“人类一家”挑选照片。对一个策展人来说,这些档案是取之不尽的。在1935年到1943年之间,FSA及其后续机构美国战时情报局(OWI)派遣摄影师拍摄了27万张底片,其中17万张收入国会图书馆档案。这些照片都是美国政府的财产。照相术从1839年发明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在摄影上投入过这么多人力和财力。
FSA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旨在对受大萧条冲击的美国农场进行调查并提供援助。许多中部地区的农民在危机中破产,被迫向西部移民,但西部的情况也并不好,在经济不景气的同时,这里还遭受了干旱和沙尘暴侵袭。沙尘暴和缺水显然与前期过度的农业开发有关,移民涌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前后有30位摄影师受委派去记录农场和移民家庭的处境。
摄影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是含糊不清的。最早,FSA雇佣摄影师是为了记录和展示罗斯福新政的成就,因此应该属于政府公关行为,但这个项目中显露出来的社会理念和美学上的成,就很快溢出了宣传范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伊·斯特赖克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摄影师的合作者和精神导师。他把这个项目定位成一种教育,也即为未来的美国人理解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代所保留的视觉文献,而几乎所有摄影师在拍摄照片的时候,都怀有明确的社会改良倾向,希望作品有利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穷和不平等。
FSA的照片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公众见面。它们被免费提供给媒体使用,尤其是和大量刊登照片的新闻杂志,如亨利·卢斯创办的《生活》画报(Life),保持着长期亲密的合作关系。展览是另一种重要形式。1938年FSA在纽约的展览启发了斯泰肯,他先是在自己编辑的《美国摄影》杂志上刊载了这批展览照片,随后拓展了这次展览的思路,通过1955年的“人类一家”大展,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展示照片的方式。斯泰肯尝试把这种展览方式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就像1920年代的欧洲批评家引入美国文学而重写世界文学史一样,他要在摄影、美国和时代三者之间建立更深刻的联系。这和罗伊·斯特赖克的雄心如出一辙。斯特赖克说,FSA的目的是“把美国人介绍给美国”(22页),斯泰肯说,“摄影的使命是使人了解人”(26页)。斯特赖克说,FSA的照片是“美国农业的图像百科全书”(30页),他还说,摄影师的工作是“帮助我们将这代人的形象与其所处的时代连接起来”,斯泰肯说,他策划的展览“的起源在于一种愿望,即通过一系列摄影作品来传递一种重要的人类经验”,而“摄影……是一个伟大而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介。”(19页)
爱德华·斯泰肯和罗伊·斯特赖克的相通之处,以及在前者执掌MoMA摄影部期间,FSA和MoMA建立起来的联系,最终促成1962年MoMA举办的FSA摄影计划回顾展。这是爱德华·斯泰肯以摄影部主任的身份为MoMA策划了最后一个展览,毫无疑问,其中包含着他对自己策展生涯的起点所做的回顾。斯泰肯从FSA档案中挑选了12位摄影师拍摄的208张照片,并为这些照片拟定了“艰难岁月:美国,1935-1941”(The Bitter Years: 1935-1941, USA)的主题。
“艰难岁月”没能重复“人类一家”的辉煌,尽管这两个展览在理念、技术甚至作品上都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斯泰肯离开MoMA的方式非常矛盾,既像是功成身退,又像是黯然退出。离开之前,斯泰肯和MoMA达成一项协议,“艰难岁月”结束在美国的展览后,展览使用的照片、展板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将捐赠给他的家乡卢森堡。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艰难岁月》这本书。
部分因为MoMA的特殊地位,部分因为这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介入摄影的时机和方式,也因为斯泰肯本人的身份和性格,MoMA摄影部甄选照片和摄影师的标准很早就受到质疑。斯泰肯不看重摄影师的个性,总是追求更具社会性的宏大主题。他偏爱的英雄主义风格,显然正是政治宣传、历史记录和社会改良的混合物。为了展览的整体效果,斯泰肯毫不在意剪裁摄影师的作品。这一点和斯特赖克很相像,后者经常在他不喜欢的底片上打孔,使这些底片彻底报废。有些摄影师极度反感这种做法。
有人说,在“人类一家”达到辉煌的顶峰之前和之后,美国摄影界对斯泰肯在MoMA时期的工作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是最早在MoMA展出作品的摄影师,也是FSA最早聘请的摄影师之一,对FSA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和风格有重要影响。但他也是最早离开FSA的摄影师,后来又公开表达了对斯泰肯的不满。
其他质疑包括:摄影在FSA、罗斯福新政或“二战”后美国形象塑造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称FSA摄影项目为“公然的宣传”(unabashedly propagandistic)。最有趣的是苏珊·桑塔格用了unabashedly 这个词。这个词的本意是一种指明知言行有亏却“毫不害臊”或“缺少敬畏之心”的态度。事实上,从斯特赖克到安塞尔·亚当斯到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他们一生都在为FSA项目辩解,就好像他们真的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似的。也许苏珊·桑塔格只是从智识上和道德上鄙视任何通过符号来操控现实的做法。但多萝西亚·兰格的困惑更加根本;她觉得自己无法把宣传从任何智识活动中剥离出去,“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在宣传你所相信的东西”。(27页)
政治宣传、历史记录、社会改良,在纸面上,这些概念有自己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在很多情形下,它们有着内在的冲突。争论的焦点在于,FSA摄影计划和“艰难岁月”这类展览,应该对应哪个概念或那些概念?它们如何塑造观众对世界的认知?公众认知与罗斯福政府、FSA负责人、罗伊·斯特赖克和摄影师们的期待是否一致?当然,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必须先问问,罗斯福政府、FSA负责人、罗伊·斯特赖克和摄影师们的期待本身是否一致?
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现实,因此不应该刻意模糊不同概念之间的边界。这没错。但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也不应该把概念当作现实本身。在现实中,不同的动机可以而且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有时候无法做出清晰的区分。拍摄照片、挑选照片以及利用照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摄影师、官员、策展人、作家和读者纷纷介入,他们必然受到多种动机的驱使。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下,人们对照片的理解也会呈现出出不同的侧重点。强行对复杂的社会行为进行分类,把它们置于特定的概念之下,对理解概念和理解社会都没有帮助。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问题本身保持开放。把罗伊·斯特赖克打孔的底片冲印出来,并和那些没有打孔的照片进行比较,以推究他代表FSA选择照片的标准。有人已经这么做了。(41页)爱德华·斯泰肯又是怎样挑选摄影师和照片?当摄影师自己获准出版自己的照片时,他们如何取舍?(40页)照片的生命在于展示和解读。在展示和解读中,新的问题会浮现出来,不同的观点会彼此辩驳,暴露出各自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相反,处心积虑的政治操控必然要刻意堵塞其他信息来源,最后不可避免地杜绝争论。
美国政府在FSA摄影项目和有关FSA摄影项目的讨论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复杂和有趣的。政府一直隐身在文化和政治争论背后,从来没有作为争议的焦点出现过,但它无处不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始终在推动拍摄、整理和利用这批照片。FSA档案中的照片是美国最早电子化的国家文献。可以从世界各地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站,(http://www.loc.gov/pictures/collection/fsa/),浏览、下载和使用这些照片。这个事实已经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将不断被提及,也让关于政治宣传、历史记录和社会改良的辨析变得更加困难。
1930年代以来,很多报纸、杂志、网页、展览、画册和学术著作使用了FSA档案中的照片,其中也包括一些中文的著作,如孙京涛在2004年出版的《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孙京涛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FSA摄影项目,其看法与FSA摄影师艾瑟·罗斯坦(Athur Rothstein)在《纪实摄影》一书中的观点基本一致。和大多数摄影史著作一样,这两本书按照时间和风格罗列了纪实摄影的不同观念和实践。这种体例一方面将FSA项目塑造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它和其他观念—个人化、反英雄主义、不加评价甚至是刻意疏离的记录—之间的差异。多年来,艾瑟·罗斯坦致力于为FSA项目的道德立场、工作方法和社会价值辩护,但辩护本身却流露了他的焦虑。孙京涛显然对这种焦虑感同身受。
《艰难岁月》提供了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FSA摄影项目、爱德华·斯泰肯和“艰难岁月”展览的回顾和研究,其中,美国学者迈尔斯·奥维尔(Miles Orvell)梳理了FSA档案的出版简史,特别是那些重要的画册。每一次出版都意味着对照片进行新的解读。这些解读不断加入争议之河,至今没有完结,也看不到完结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