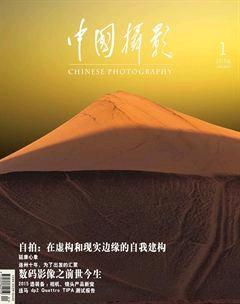自我鉴定报告
祖宇
一、源起
“自拍”,与绘画的“自画像”一并传达出图像的哲理性,它们是艺术家投射“自我”的镜子,让其在与“自我”的碰撞中,与国族、历史、文明的对话中,更加确定作为“人”在所处时代中的价值。有关“自画像”(Self-Portrait),其形式早在古埃及与古希腊艺术中就已出现2,其概念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得以明确。而“自拍”(Selfie,指用智能手机或电脑摄像头拍摄然后上传到社交网站上的“自拍”),到2009年被首次作为商业用词使用,并于2013年以“《牛津词典》年度热门词汇”进入公众视野。在互联网上蜂拥出现的“自拍”(Selfie),成为当下重要的影像文化现象。
诚然,追究“自拍”的源头,无法回避西方绘画。从15世纪起,艺术脱离对宗教的膜拜,转而确立对人本身的自我表达。有记载的最早的“自画像”(Self-Portrait)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让·富盖(Jean Fouquet)于1450年在黑色珐琅上绘制的金色小像。此后,艺术家便开始创作大量携带自我烙印的艺术作品,其动机或是出于对自身的探索,或是单纯的由于画自己最便利。一时间,几乎所有艺术家,包括雕塑家、画家,都在尝试这种自我探知。文艺复兴之后,每个时代的画家都会普遍绘制“自画像”,如丢勒、伦勃朗、梵高、弗里达、波洛克等西方艺术史上的伟大画家们都有经典的“自画像”传世。
17世纪起,法国的理性主义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主义美学再次启蒙了人类的心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休谟的“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理”,有关“艺术独立于主体”的观念开始被一种心理学观念取代,即艺术是人类心灵与情感的产物,这使艺术家注意到人类感知事物的过程,将其创作着眼点从艺术作品转向了体验过程,从物转向人本身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与情感的思考。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再次视“天才论”为其美学理论的关键,他彻底颠覆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模仿论”—“自然是艺术家的模特”,宣称“天才艺术家完全独立于自然”3。19世纪中叶起,艺术逐渐由主观化发展为形式化与观念化,绘画逐渐被逼上绝路、变“坏”,这在20世纪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中可见一斑,然而,在这一历程中艺术却被变“好”,并求得诸多新的媒介可能。“自画像”在20世纪迎来“情境”的表现,它们看上去更像是“泼墨的自传”(autobiographical outpouring )4。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ack)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证实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隐喻:真正的缪斯不是存在于绘画的主题,而是存在于绘画的媒介性本身。这些画作会被人禁不住地视为艺术家的移情工具。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及艺术家对“理想我”5的追逐,使“自画像”从“外观”走向“内省”(如丢勒、伦勃朗、梵高),从“真实”走向“虚构”(如弗里达),从“内容”走向“媒介”(如波洛克),它们不仅表现艺术家的外貌特征,还逐步迈向复杂的人性、强烈的情感,以及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记录。它们从作为自我标榜的艺术形式,发展为艺术家实现自我救赎的工具。这些,无疑让“自画像”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诞生之时,就为“自拍”提供可直接挪用的丰富养料。
二、在西方
1840年,摄影师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使用“故事性”的手法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张“自拍照” —《扮成溺死者的自拍像》。这张著名的“装死照片”让摄影第一次充当了“骗术”,也让希波利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造照片”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巧补了他不能成为“摄影发明者”的遗憾。他从1838年开始研究摄影技术,发明被称为“直接正片工艺”(direct positive process)的曝光方法。在1839年8月份官方公布达盖尔技术之前,巴耶尔就已向法兰西科学院汇报自己的发明,然而由于致力于推广达盖尔技术的阿拉贡的施压,使得巴耶尔的发明远离了公众的视线。因此巴氏制作了一张“自杀照”以表达自己遭受法国当权者不公待遇的强烈不满6。在这张照片的背面,也有摄影师的一番自我阐释7。有趣的是,这幅“自拍”以“自杀”的方式反而飞跃了“死亡”,并被世人广泛关注,巴耶尔也很快成为巴黎摄影界突出的一员。此后,几乎每位摄影师都有“自拍”,但彼时的“自拍”仍以“自画像”命名,其动机也与“自画像”无异。
从1839年至1890年是肖像摄影盛行的年代8,而摄影在其早期历史中的艺术尝试也引领许多画家兼攻摄影术。摄影师们开始以“自拍”进行自我标榜,他们不仅得意于自己对“新技术”的得心应手,也为自己尽管作为一名摄影师而不是其他艺术家(画家、雕刻家)的身份,但是应当获得同等的尊重进行正名9。此时的摄影,几乎无缝地对接绘画的各种风格及形式,并藉由其“纪实”特性,在真实与谎言、现实与幻想之间自由切换;此时的“自拍”,也足可以追溯个体在历史某一特定时空中的切片,它们“灵光”(aura)乍现,无可替代。
聪明的波西米亚人纳达尔(Nadar),在19世纪的巴黎卡皮西纳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Paris)35号开设摄影工作室,而在此之前,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的石版画作品《纳达尔的众神像》(Panthé-on Nadar,1854),其中包含了约300名法国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启摄影生涯,并为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定制拍摄“名人肖像”,这些肖像中也包括他的“自拍”。
另一位绘画兼攻摄影的范例是表现主义绘画先驱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其一生除了创作携带强烈悲剧意味、描写人类真实心灵的绘画作品外,也使用摄影对自我的人生展开赤裸裸的记录与分析。蒙克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史上产生一种全新的气象,不仅是形式上,还有观念上 —使用19世纪80年代风靡挪威的“招魂论”。受其影响,蒙克在20世纪初还拍摄了一组照片,起名“宿命照片系列”(fatal destiny photographs)。这些透明模糊的图像还被称为“招魂摄影”10。这其中有一张最不寻常的“自拍”,是蒙克在“延时曝光”过程中不停移动的结果,“自拍”中的脸很模糊,并被房间里的阴影埋没,画面尽管失焦,却聚集“灵氛”,摄影师在那一刻与世界“通灵”。与同时期的其他摄影师比较,蒙克的“自拍”拥有忧郁神秘的基调,并包含一种向内的感触—记录自己的精神状态。

这种表达“通灵”的塑造精神的“自拍照”,刻画出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图像中的“自我”如“幽灵”一般在延时曝光中离开又回返。这类照片还受到欧美“有神论”者、占卜师和“灵魂不灭论”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从这些照片中寻得出口,以宣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压力。蒙克的照片启示了摄影将在20世纪与抽象艺术、观念艺术的呼应,有关艺术家的“自画像”,也由个体的物质性(长相、性征、穿戴、地位等)上升到“精神特质”的诠释。
除绘画的观照、欧美哲学与艺术思想的奠基,现代理念与科技的发展也推进“自拍”这一摄影题材在其相应的时代中顺应某种达尔文式的演替,它根植于绘画的“自画像”并脱胎于“肖像摄影”的“自拍”,让肖像与室内拍摄等传统题材历久弥新,其藉由如大画幅与中画幅相机产生的古典摄影术的魅力,也是摄影最具专业性的传承特色。然而,这期间也有特殊的例子,如包豪斯学院的摄影教师拉兹罗·莫霍利·纳吉,在学院倡导的“less is more”(少就是多)的艺术理念下,进行摄影实验,开创“物影照片”(photogram)—不使用相机与胶片(卷),直接在相纸曝光显影,其创作的“自拍”当之无愧地成为纳吉的个人标签,画面中纳吉的“身体”成为“自我”的物质客体。20世纪的“自拍”在新奇“制相术”此起彼伏的浪潮中,还让镜头与感光元件(胶片或电子芯片)成功地接力画笔与画板,摄影师们继续乐此不疲地展示想让观众看到的个体经验的秘密编录:个人标签、童年回忆,或是某种情感的宣泄、精神的灌注。然而,无论摄影师使用哪种方法,他都需要长久的基于“表义”与“隐义”地自我发现。每一幅“自拍”,如同“自画像”一样,都是摄影师或画家的自我鉴定报告。这种“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方式,之后成为当代摄影的重镇。
“身体”在当代摄影中不再仅仅作为“自我”的客体,还是文化的“客体”。有关“自我”与“身体”的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形成对“身体”进行理论研究的高潮中,有米歇尔·福柯著作的影响11,有女性主义的影响12,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文化的膨胀13。20世纪70年代后,摄影中“身体”的含义获得再生与翻新,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定义了“身体”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属性。此时的“自拍”是以“自我”为对象探索“身体”与历史、年龄、种族、宗教、性别、国家、民族等的关系,照片中有“另一个人在我体内复活”。摄影师不仅用“自拍”进行自我释放与救赎,还使用“他者”的视野表现镜像中的自己,或将自己伪装演绎成他人,以验证对“自我”与“身份”的理解。“自拍”,从最初作为个人传记,转而成为被“外界”(大都是“自我”模拟的外界)观察的对象。事实上,后者是摄影师探知“别人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借口,他们大都行走在主流世界的边缘,并为自己及其所属群体博得认同与权利。
在这场“自我”与“他者”交欢的视觉盛宴中,“身体”已然超越原本的物理属性与审美特征,成为文化与政治的利器,它刺破传统权威的屏障,引领“自拍”走向“游戏”与“戏剧”的狂欢。这场视觉派对还将在70年代完成经济转型(向消费社会转型)的美国推向风口浪尖。例如,“女性主义者”辛迪·舍曼殚精竭虑地使用“表演影像”复现男权视阈下被窥窃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生活的细节,画面中那些“被强调的女性气质”(emphasized femininity)恰是舍曼用来挑战“霸权式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14的武器,批判女性对男性、家务的从属状况;另一位女权斗士南·戈尔丁借助女性身体的疮伤记忆控诉男性沙文主义掌控下的两性关系,为其弱者及受害者处境申辩。舍曼与戈尔丁的作品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的硕果体现。这种对性别与性的公开质疑,还突出地表现在男性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的作品中,梅普尔索普运用“自拍”与“身体”开诚布公地演说男同性恋群体的身份意识与性别认同。
有关“身体”的易装,让“自我”在客观历史中获得“假释”,摄影师们狡猾地从特定历史语境中脱身,幻化成其他历史语境中的人物,经历着超现实的历史体验。如吉莉安·沃林(Gillian Wearing)在她的作品《相簿》中对家族史的探讨。她在这个系列里扮演并诠释家庭老照片里的双亲、兄长、叔舅以及少女时的自己。其中有一张是沃林挪用父亲昔日的身份 —一个精干利落的青年。她带上假脸面具,却刻意让眼睛周遭的面具痕迹清晰可见,观众得以微妙但确切地感受到沃林其实挪用了“他者”的身份。她借助摄影挪用亲友的身份与他们的生命瞬间,敏锐地将“自我”的历史与“他者”的历史进行交叠,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历史情境。
围绕“身份”展开的“自拍”,在世纪之交的非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中也颇为醒目15,他们在后殖民时期为“自我”或“在地文化”寻找原乡。如萨摩亚群岛土著艺术家木原重幸作品中对自我的性别、信仰等身份的理解;日本摄影师森村泰昌以东方人的身份与视角解构并置换西方的文化视野,将西方的文化艺术偶像拉下神龛,通过自我的扮演与模仿,质疑、挑战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权威性。与此同时,努力探索自我、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当代摄影师,也通过“自拍”验证积压长久的那份对文化原乡的寻根式的思考。他们在以西为镜、以镜自鉴的过程中,鞭策着本土摄影语言的催生与壮大。
三、在中国
较之西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我探知”则完全不同。受传统艺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画家中“自画像”者寥寥。中国的人物画在时间上也晚于山水画而出现,即使山水画中有人物也只作点缀,多彰显自然之大;人物画则多用于膜拜宗教或标榜赞助人,很少直接表现画家本身。此外,中国画家借用“他物”替代“自我”作为画中的主体而存在,受益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思想,中国画家常抒“胸中丘壑”于“笔底烟云”,奠定“超乎象外”的绘画意境,并多强调神与物游、以景抒情、借物托志,将“人”本身的物质属性与审美特征幻化为“他物”作为艺术作品的客体,回避直接刻画艺术家本人特征。所以,很难从中国的传统绘画与思想中寻得对“自画像”的观照。由于摄影术是西方舶来之物,故与西方不同,中国摄影的“自拍”不可与绘画中“自画像”的意义重叠,其成型也与中国传统绘画并无瓜葛。邹伯奇先生早在1844年就实现了“自拍”,这仿佛与西方摄影的“自拍”同时出现,但那仅作为对西洋科技的效仿,缺乏像大多数西方艺术家“自我鉴定”的动机。中国摄影师在之后一边翻译这些舶来之术,一边利用它们建立“自我”与世界的关联。然而,由于摄影及“自拍”由西方借来,尽管中国摄影师在早期创作中有“自我”的主体存在,却无法摆脱“他者文化”的影子,这主要是由于摄影师对本土文化的内观与内省不够清晰、独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摄影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拍”,伴随大量“外来”思想的涌入,以及海外阅历的增加,中国艺术家在作品中标榜“自我”的意识逐渐强烈。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实现转型(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大众传媒与消费时尚引领了对流行事物的追崇,并鼓励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解放个性;艺术样式开始从西方直接挪用,逐渐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国族自信开始变得鲜明,并渗透到个体行为中。此时的“自拍”,中国摄影师在携带政治性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将行为表演与摄影相结合来创作“表演的自拍照”(performed photography),“回归更为自发并即刻的影像世界,将自我放回影像,即回到自拍”16。
出生于香港后定居于美国的华裔摄影师曾广智,拍摄于1979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前纵身一跃的自拍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画面中摄影师本人在纽约港身穿中山装,使用闪光灯“曝光”自己跳跃的姿势与呼喊的表情,充满强烈的爱国志与国际感,也表现出新时期中国人渴望被世界关注、与世界接轨的自我意识。这种具备时代特征的个体精神至新旧世纪之交,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席卷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鲜明。以“自拍”为例,一时间涌现出诸多的中国当代摄影师将“他者”作为人格面具挖掘城市人的群体性内心变迁。
洪浩,在其1998年的《不错,我是Mr.Gnoh》《时常在拱形屋顶下等候阳光》等作品中扮演的是“忠于自我”的另一个自己(“other”—小他者17),讽刺的是,画面中的洪先生尽管是身着中山装的中国人,但却享受着豪华的西式生活(漂亮的游泳池、西式服务与家具、阳光、沙滩、美女)。
洪浩的另一组“自拍”《我所认识的洪先生》,仿佛用影像实证一位中国人是如何被“全球化”淹没的。画面中的摄影师手持镜子,注视着自己“变型”为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士。连标题中的文本也被西方化,英文标题中的“Hong”,已变成“Gnoh”这一不可读识的异国名字。这幅作品也放大了中国年轻人有关西方的幻想。
这些照片在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中反射着精神分裂式的、碎片化的个人,它们上演着有关“全球化”的荒诞剧,嘲弄着小市民的欲望清单。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冲突,催生出中国摄影中“在地化”的图像符号,它们也出现在“自拍”中。如赵半狄在作品中“每次出现都和熊猫在一起”。他视中国的“国宝”熊猫为亲密伙伴及其影像语言中的重要符号,他的“有感而发”从一种冲动变成一种能力,也使其影像具备了不可替代性。张洹、邱志杰等人通过摄影来记录“自我”对身份与“文化”的演绎,尽管他们的作品并非是以照片为主体来表达“自我”与世界的关联,但摄影作为其创作过程的记录手段,“自拍”也就成了作品最终的存在媒介。这些“镜像”,透露出中国摄影人在世纪之交“文化身份”的忧虑。
21世纪互联网开启信息时代,发达的媒体技术生发新的大众社交模式与媒介环境。2007年美国苹果公司发布第一代iPhone智能手机,2009年中国迎来微博元年,并于同年1月进入3G时代。“全球化”与“全媒体”双重语境下的中国,先进的拍照工具、互联网社交平台以及通信速度,让人人都当上摄影师,人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杂志。由于虚拟的空间有别于现实世界,为逃避、欺骗和伪装提供了更多机会,也让新世纪的中国人痴迷于表演、作秀、成名的快感。“自拍”开始在“模仿秀”与“明星脸”的大潮中翻滚,并借助各种媒介途经寻求鲜花与掌声,快门不断,曝光频频,“个体”成为“自媒体”,引爆群体性的欲望释放。在那里,“自拍”让摄影师实现一个完全相同又完全不同的自己,它让人不厌其烦地自我关注、自我保护、自我表露、自我创造。对此,摄影师的自我探知,有时甚至还可能是病态的“自恋”,它使“自我”在幻象中完成认同的过程18。回朔这种“自我迷恋”,源自西方19世纪的大工业进程中人被当成机器体系的碎片,并在现代社会转变为对“身体”与“美丽”的崇拜。事实上,这也是人在被碎片化之后从外在进行自我救赎的方式,它并非接受人的自然身体与面貌,而是将其纳入美丽的模式。
居住在纽约的上海籍摄影师沈玮,其“自拍”作品系类《已经想你了》(I Miss You Already)通过自己的肉体来架构摄影的视阈(某种意义上还是“视欲”),如同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笔下的纳克索斯(Narziβ)神话一般迷人,他试图扮演成“另一个自己”,欣赏、爱慕、挣脱又依赖,“自我”与“他者”在沈玮的作品中相互转换、保持统一。这些作品透过独特的“男性视线”(male gaze)诠释男性世界罕见的细腻与精致,照片中充盈一种画意的、阴柔的、同性间相互爱慕的气质。这些“男性视线”穿过照相机的镜头映射出都市人的“偷窥癖”,指向都市人的欲望中对“男性至上主义者”(sexist)的迷恋,它们也因此构成作品中对“性”与“身份”认同的探讨。
刘勃麟创作于2010年至2012年的一组“自拍” —《城市迷彩》。这些作品通过行为表演,以堆满商品的公共空间 —“市场”为语境,与中国社会对话。在此,摄影师将“自我”隐身于“资本的景观”19,将艺术的行为贯穿于消费的行为,将“人”的价值消解于货币或大众传媒的符号。在这场以摄影师本人为物质载体的表演中,观众或会滋生一种“共同感” —同情心:今天的人类正在使用最先进的科技、最快速的效率、最节俭的沟通,以及最大功率的消耗,加速埋葬人类自身。观众还会发现,这些当代文明的背后潜伏着人类近乎自我毁灭式的危机,逐步吞噬人类的肉体、情感、生存空间。然而,这些“自拍照”已经无法帮助捕获“自我”,无论那个“自我”是摄影师还是观众本身,“肉体”被“景观”的矩阵遮蔽。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它拆穿了“理想我”的幻觉,大义凛然地批判人本身的拜物教20。
中国摄影中的“自拍”,伴随西方摄影的进程在不断“挪用”与“效仿”的道路上孜孜以求。这顺应了当代艺术与摄影的大趋势,它们或被淹没在新科技洪流的簇拥之中,或在“全球化”大趋势的迷途中处心积虑地争取一个观看者的座位或发言者的资格,或是在长久的个性压抑之后挖空心思地寻找曝光露脸的时机与空间。那么,以研究“自拍”为契机展望中国摄影:如何建立有本土文化支撑的、本土艺术家灵魂的影像语言,让中国摄影自信地使用一门官方语言与世界对话,而不是被殖民于其他国族或文化的影像语言之下,或是每一个中国摄影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J. Lacan, Das Spisgelstadium als Bildner der Ichfunktion, in: S I, S. 67.
2 较之绘画,雕塑中的自我表现可追溯至更加久远的古埃及阿玛尔纳(Amarna Period)时代(约公元前14世纪),埃赫那顿法老(Pharaoh Akhenaten)的首席雕刻师巴克(Bak)把自己与妻子的肖像雕刻在石头上。在那之后,为帕特农神庙创作雕塑的古希腊雕刻家菲狄亚斯(Phidias),传说于公元前5世纪曾被监禁,原因是他在其创作的雅典娜神像的盾牌上也留下了自己的“签名”—一尊小的自我雕像,而膜拜神性的帕特农神庙禁止人类的自我表达。
3 陈平,《西方美术史学史》,p73。
4 Sean Kelly, The Self Portrait: A Modern View(London: Sarema Press, 1987) p.24.
5 “按照拉康的分析,在镜像中获得的主体的形象,是一个‘理想我,这个‘理想我构成了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后作为自我认同的基础。……这种理想化的虚构还会产生种种转换,将“我”与人自己建立的塑像,与支配人的魔影,以及与这种制作的自动机制联结起来。”仰海峰著,《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p317。原文中引文自拉康,《拉康选集》,p110。
6 巴耶尔获得了600珐琅用以改进设备和资助进一步的实验,但条件是推迟发布其技术工艺。参见赫尔穆特和艾莉森·葛先姆《达盖尔》,p88。
7“正如您所看到的尸体,是巴耶尔先生,正是这个(摄影)过程的发明者。据我所知,这名勤奋的实验者为他这个发现贡献了三年时间。但政府只对达盖尔先生过分慷慨,而对巴耶尔先生无力以施,随后这个可怜的家伙自溺身亡。命运真是多舛啊!他在停尸间度过数日,无人问津。女士们、先生们,以免冒犯您的嗅觉,请最好快速通过,正如您所见,这位先生的脸跟手已经开始腐烂了。”
8 内奥米·罗森布拉姆著,包甦 田彩霞 吴晓凌译,《世界摄影史》,p38。
9 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认为摄影成为“那些没有才华的画家的救命草”。……很多失业的画家、收入不高的画家、雕刻师开始拿起相机,以拍摄人物肖像谋生,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Ibid., p41。
10蒙克这样写道:“灵魂真的存在!我们看见所能看见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眼睛—我们是什么?可能动的能量—燃烧的蜡烛—有着灯芯—内在的温暖……存在于我们里面—私人的灵魂—爱人的灵魂—和邪恶的灵魂。” 阿尔内·埃格姆著,张璐瑶胡默然译《蒙克与摄影》,p62。
11 米歇尔·福柯独特的学术规划探讨了权利、知识和人的身体之间变化着的斗争对抗关系。福柯关注权利通过实践、话语和技术被烙印或“铭刻”在人的身体上。
12 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认为,分析和测试女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女性体验的特殊性。
13 消费文化加速了人的身体的商品化,在接受和展示身体化差异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细化的、地位分明的等级秩序。
14 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W. Connell)的专著《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15“他们通过对自我的描绘来表现转型中的国家,而国族身份的转变、国家未来局势的动荡同样会影响艺术家的个人认同。……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加之印度、巴西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意味着21世纪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苏珊·布莱特(Susan Bright),《自动对焦:当代摄影中的自拍照》(Auto Focus: The SelfPortrait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p19。
16 苏珊·布莱特(Susan Bright),《自动对焦:当代摄影中的自拍照》(Auto Focus: The Self-Portrait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p20.
17“拉康的‘他者(the other)分为大、小他者,分别译作‘大写的A和‘小写的a。其中‘小写的a处于想象界,是一种直观的、具有自恋性质的视觉认同对象。”曾胜,《视觉隐喻—拉康主体理论与电影凝视研究》,p50。
18“这种自我认同,不仅是一种幻觉,而且是一场悲剧。……‘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循环打破,导致了永无止境的自我验证。”Ibid., p318。原文中引文自《拉康选集》,p93。
19“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p10: 34。
20“从人本学的立场来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是人本身的拜物教,因为现代拜物教的前提是将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劳动力,而拜物教意识的现实意义在于,自觉或自发地将这种“自由人”纳入到资本体系的过程。” 仰海峰著,《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p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