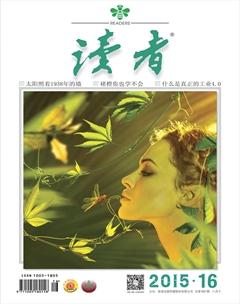喜欢的人
赵瑜

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
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她,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她眼睛好看,我喜欢看她;她有些羞涩,这让我对她更有好感。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说。
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她看我新写的诗句。她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她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她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
我终于发现,她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她的字是欧体的底子,果然,她一捉毛笔我就看出来了,耐心,透露着家学。那时,我正喜欢向外面投稿,写好草稿以后,会交给她,说,你帮我抄写清楚。她倒也习惯看我潦草的字迹,仿佛在那一份潦草里,她看到了我日常生活的粗略。有时候,我在图书馆做的一些读书笔记,字迹太潦草,过了些日子,我不认得了,会拿给她看。她给我用工整的字标注得清清楚楚,她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书写的习惯。
这真是一份相互阅读的欢喜了。我那时深信她是喜欢我的。有一次,我往她的书里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我当时想,我略去的内容,她大概应该猜得到,反正,她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她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她的想象力。
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她写下这四个字,她就应该自己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六百字的甜蜜。哪知,她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看了,从未发现有小字条。
或者她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她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她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
此时已是夏天,她的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她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她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
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坏人。
我常常想,我和黄小帽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帽帮助我抄我写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她倾诉爱慕。然而,她始终没有将她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她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
青春有时候真让人伤感,两个人相互看着,在心里相互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黄小帽”这个称谓,我都恨不能找一块橡皮,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
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她。因为是假期,她们宿舍只有她一个人。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她说话。
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她的身边。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两个人说话的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她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昵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
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她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她。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有电话,只好写信给她。
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她收到信后的情形,想象她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她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
我没有收到回信。
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她,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中,我和无数人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她第一句应该问她什么。
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她。这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她的时候,她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
到了晚上,见到她,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她讲了。而她并不知道我前后找她多遍的热烈,她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她,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
她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她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仪式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儿,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飞翔。
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
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稿纸上,投寄了出去。
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帽。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