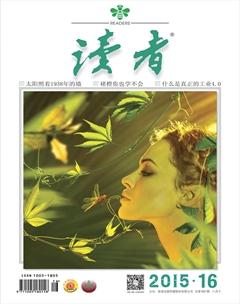寒夜急诊
陈妙青
一
睡意渐渐袭来。她拉了拉被子,掖好被角。刚要睡着,忽听他说了一句:“家里有止疼药吗?”她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他用胳膊肘碰碰她,又问了一句:“有没有止疼药?”她没好气地说:“没有。”
他性子急、脾气倔,而她爱唠叨,又小心眼儿。两人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角。两天前,他们刚刚吵了一架。起因很平常。那天,她一直在厨房手忙脚乱地又是切菜又是翻炒,而他却悠闲地斜躺在沙发上摆弄手机。忙着忙着,她的无名火就蹿了上来,不由得对着沙发上的他唠叨开了:“你每天进了家门就知道玩手机,从来不做家务。有你这样的吗?凭什么家务就该我一个人干!”如果此时他能发扬风格,明白女人的唠叨都是有口无心,少说两句,让她发泄一下消消气,也就算了。可他偏偏毫不让她,不耐烦地回敬:“我不就闲这一会儿吗,你做个饭还以为自己有多大功啊?”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谁也不肯少说一句。吵急了他突然拿起手机狠狠地往地上摔去。“啪”,那部刚买不久的手机瞬间支离破碎。她一下子愣住,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厨房,“砰”一声关上了门。随后,他也摔门而出。
屋子里很静。路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斜斜地落在床上。她从被子里坐了起来,看了看,黑暗中他没动。她打开灯,看到他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整张脸痛苦地扭曲着。
两天来,他们一直在冷战。想起他平日的种种“劣行”,想起他摔手机的“野蛮行径”,又想着自己辛辛苦苦操持着这个家却不被他理解,她觉得心灰意冷,恨他入骨,甚至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二
她“啪”地关了灯,重新躺了下去。风凉凉地灌进了被子,她缩了缩身子,拉紧被角。他呻吟了一声,缓慢地翻动着身子。片刻,她又坐了起来,把灯打开,冷冷地抛过去一句:“你哪儿疼?”“好像是胃。”她犹豫了一下,拿起衣服往他身上一扔,说:“起来,去医院。”
到医院时,已是凌晨1时。下了车,他强撑着想要站起来,却怎么也无法直起身子。她用力搀着他来到急诊室,迎面出来一位医生,她急急地说:“医生……”对方打断她的话,匆匆地说:“这会儿不接病号,正在抢救病人,你们去急诊科找值班医生。”
此时,他已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双手捂着腹部,蹲在急诊室门外的走廊里。她连拖带搀,把他弄到急诊科,简单说明了情况。值班医生稍作询问,说:“先去做心电图和彩超检查一下吧。”随后又边开单子边说:“去西边楼大厅交费,再去后面二楼做彩超,四楼做心电图。”
她搀着他又一步一步地挪下楼,找到交费大厅,把他安顿在椅子上休息。她跑到交费窗口,“咚咚咚”敲着玻璃窗。
好不容易交了费,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看过检查结果说:“像是急性阑尾炎,抓紧时间去对面五楼找外科医生。”
看着他双手死命地顶着腹部,紧咬着牙,脸色苍白的样子,她转过脸悄声问医生:“医生,能不能先给他用点止疼药?麻烦您了。”“不行啊,你赶紧带他去外科楼吧,到那里看医生怎么说。”
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一把扯开羽绒服的扣子,再次扶起他艰难地往楼下挪去。
深夜的医院显得寂静、清冷而又空旷。她抬头看看天空,没有月亮。路灯的光惨白地照在冰冷的地面上,寒风一阵阵刮过来。她紧搀着他,在路灯下却像是只有一个人的影子。
他突然停住脚步,蹲了下去。
她说:“干什么?别停,得赶紧去。”
他的头垂在胸前,声如蚊蚋:“起风了,扣上你的衣服扣子。”
“少废话,快走。”
三
找到外科医生,她把检查结果呈给医生,心急如焚地等待“发落”。
她觉得犹如经历了一个世纪般漫长的时间,医生终于开了金口。
“你是他……”
“爱人!”她迅速地答。
“那好,在这儿签你的名字。”医生指着一张单子的空白处说。她看都没看单子上的内容,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趴在办公桌的一角,双脚不停地在地上蹭来蹭去,嘴里不住地发出呻吟声。她再次谦卑地请求医生:“医生,您看,他疼得受不了了,先给他用点止疼药吧?”“这儿没有止疼药,你赶快去一楼交押金,我给他办住院手续。”她转身就跑。
经过楼上楼下的几番折腾,加上心里着急,本来瘦弱的她已感体力不支,可她此时只想快点把手续办好。
她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对歪在休息椅上不住呻吟的他说:“你在这等着,我马上来。”说完,她匆匆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去。”
她一回头,见他已佝偻着身子,蹒跚地跟了上来。
“你去干吗?耽误时间。”
“你一个人不行,不认路。”
“你别管,我丢不了。”
“不行,我也去。”
她知道是拗不过他了,回头搀上他说:“累赘,快走。”他们像一对蜗牛,在深夜的医院里缓慢移动。走了几步,她把他一丢,迈开步子朝前奔去。
四
西北角的那栋楼黑黢黢的,借着微弱的光线,她找到了交费处。那个穿着毛衣披着棉袄的小伙子睡眼惺忪地接过单子看了一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唉,你来这儿交什么费啊?在办住院手续的地方交押金。”
突然间她感到无助极了。回头一看,他已经跟了上来。“你一个人不行,打电话叫个人过来帮你吧。”他说。她拿出手机,翻出弟弟的号码,可一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她没有拨,又把手机放回衣兜。
他脸色蜡黄,想呕。她掏出纸巾递给他说:“你就在这儿等我,我再去问问医生。”可她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她是路盲,在陌生的环境里从来不会辨方向,更不认路。平时家中出外都是他独当一面,她一直在他的羽翼下生活。很多时候,他都把她当孩子一样呵护着。
“什么事,什么事?”不知从哪间屋子传出一个声音。
“找外科。”
“去最东边。”
她拔腿往最东边跑去。“开门啊,麻烦了,开下门吧。”屋里没动静。忽然从走廊的另一头又传来一个带了几许无奈的声音:“连东西南北都不分了吗?”她一愣,意识到自己跑错了方向,她迅速往真正的东边跑去。一时间,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惭愧极了。
此时,她才发现在这寒冬腊月的深夜,自己的毛衣几乎被汗水浸湿。从外科出来奔到楼下时,她看见黑洞洞的楼梯口他蜷成一团的身影。
两个小时以后,她终于把他安顿到病床上,医生、护士开始忙碌。她跌坐在那儿,长出了一口气。猛一低头,发现自己居然穿着一双高跟鞋,鞋一侧的拉链已完全敞开,是出门时随便趿拉上的,难怪这么不得劲儿。
他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慢慢地睡着了。黎明时分,他醒来,一眼看见病床边的她,问:“你没睡?”她下巴一抬,眉毛一挑,嗔道:“我爱睡不睡,关你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