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蒋方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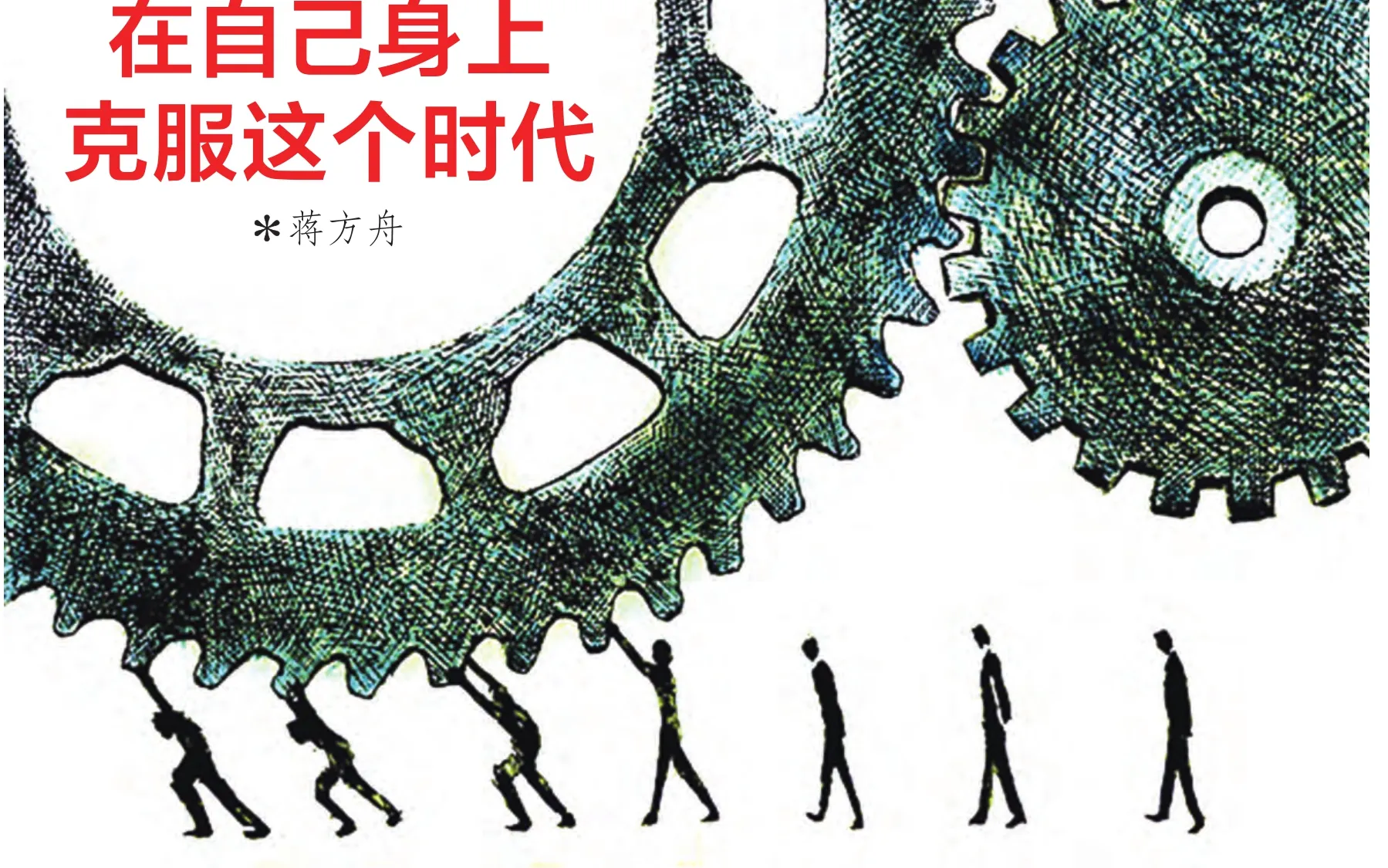
大概是我上大三,他也上大三的时候,我是清华的,他是北大的,我们共同上过《亚洲周刊》的封面。那个时候我是因为批评清华,他批评北大,我们作为时代的典型被上了这样的封面。但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非常难把他和我印象当中的这个人联系起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扮成了霸道总裁的样子,穿着风衣,头非常地油,围着围巾,拿着公文包。他说要去和某个银行谈几百万的生意,他自己是某某企业的创始人、CEO,达沃斯论坛什么领袖,跟薛蛮子老师对过话。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羞愧。当我们都大三的时候我们是两个愤青,几年之后我发现人家已经是货真价实的90后精英,我还是在做重复的工作,还是在写作,继续当个愤青。
现在所有人都在使用年轻人的语言。那天我爸对我说他终于要跟某个同事撕逼了,我听了非常惊讶,但我爸露出了非常轻狂和得意的表情。我去跟一个台湾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也跟我讲到一个类似的现象。他说台湾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萌化的社会,整个社会在模仿年轻人的语言,所有人都在尝试着去理解年轻人,理解他们的话语、思维模式。
我经常会感觉到恐惧,为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的时代?
首先是要放缓的经济增长,大家都应该有些体会。我写了一篇文章,泼了大学生创业一盆冷水。我大概的意思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生创业,政策也会鼓励大学生创业?那是因为大学扩招的关系,无法解决就业的问题,包括很多行业都在不断缩减。因为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所以让大学生用父母的资源去为国家创造税收是一个看起来再合理不过的事,再也没有比大学生创业更牺牲自己,造福他人了。立刻有人反驳我说,蒋方舟你不能这么说,你没有梦想。
你发现“梦想”这个词,就像武功里面的降龙十八掌或者是天马流星拳一样占据了很高的制高点,好像一打出就没有任何回击的余地。但我想梦想应该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是一个你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政策买单,这不叫梦想。
我面临的第二点就是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无力。我去年去台湾感受特别强烈,我发现那边的年轻人真的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做一些改变时代的事情和社会参与的事情,但就我们而言是非常少的。
第三点就是阶层的固化,这听起来很抽象,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具象的故事去描述。
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官方指定的老公,我们的父母都是好朋友,我们家也住得很近,我们俩长得都很像,一块上学放学,每次同学都在背后唱《结婚进行曲》,我们内心都非常羞涩地觉得我们以后会在一起的,虽然什么都没做,但总有一种什么都做了的感觉。我们俩官方配对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做了九年有名无实的夫妻。
后来我去武汉读高中,到北京读大学,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联系。直到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才见到了他。我愤怒地发现他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那种被背叛的感觉非常强。我们在路上遇到。我抱着一种非常奇怪而阴暗的心态劝他还是应该有梦想,不应该被困在家庭当中,拼命劝他抛弃妻子来北京。这非常不道德,但我当时是认真的。
如果我没有写作的话,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生命的映照,好像我看到他就知道我原来的命运轨迹会是什么样。我其实特别希望他过得好,实际上他在铁路工作,每个月两三千的工资,老婆是一个乘务员。本来应该是我,现在是一个乘务员。当然不能去否定他的幸福,但多多少少内心有一点替他不甘心。他劝我,你也不要替我不甘心,我已经认命了,我的父亲是这样,我也会这样,我一生大概就是这样。我非常想反驳他,但没有办法反驳他。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他说的是对的。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还是一个坏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去乘风破浪的时代,还是需要去诅咒对抗的时代?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幻想到社会上以后,一定要过特别丰富多彩的生活,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就迅速成为了职场小蒋,对人都很热情,经常去参加饭局。那个时候我非常兴高采烈,我觉得人生应该丰富多彩,我应该尝试很多很多的东西,再也不能过大学那样单调和闭塞的生活。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
去年我和阎连科老师合写了一本书,每个月我们都会写一篇同题的文章,后来永远是我在拖延,直到有一天阎老师非常忍无可忍,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每天都过得非常繁忙,非常五光十色,我也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大概是不好的。我当时看到之后非常惭愧。我们同样是写作者,他比我大很多,他不会打字,永远是手写。
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两个字,就是农夫。现在“农夫”好像是被贬低的一个词语,但在我看来所有专注的写作者都过着农夫一样的生活。什么是农夫?就是不仅过着规律的生活,而且按照农夫的时间去生活。我们现在都以秒、分钟、小时去记录自己的时间,但农夫的时间永远是和农作物关联的,专注的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专注的只有自己一小块的写作。
这样的生活其实是我向往的生活。你慢慢地去爬一座山,不看周围的人,也不看那座山有多高,直到有一天你抬头,你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和世界上最牛逼的人站在一起,这就是农夫的生活状态。
但人应该有直视自己的时刻,这一定是靠一种简单易行的生活方式去维持。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用简单易行的生活方式去克服这个时代。
第二点就是用独立的精神去克服这个时代。什么叫独立的精神?这句话我一直都不明白,直到去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明白了这句话。
去年我去南京的某个学校跟人交流,有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拿到了话筒。她拿到话筒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在大学永远是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人。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坐在最后一排,一直都不太听台上的人讲到什么,偶尔抬头注视一下讲台上的人,就会觉得讲得太傻逼了,然后就默默低下了头。
最后一排那个同学拿到话筒的时候我内心稍微有一点点异样,我觉得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她拿到话筒介绍自己说是大二的学生,她并不是有问题要问我,而是有三句话对我说。她说第一你介绍的你的经历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第二你讲的这些话跟我们每天看的心灵鸡汤没有任何区别。第三你自己说的这些话你相信吗?
我当时非常尴尬,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我当时没有回应,我没有办法回应她。直到这几个月过去,我才知道她说中了我的哪一个软肋让我当时如此难堪。
第一她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这一点我是没有办法反驳的,我的成长路径确实和他人不一样。我从七岁开始写作,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文艺女青年,她一直觉得是生了我断送了她的文学生命,一直觉得应该由我去续文学生命,就让我从小开始写作。从七岁开始写作,我也是因为自己的写作特长,上了我们那个时候最好的高中,然后读了清华。我的成长经历没有那么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在某种层面上我确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有办法反驳,我对此觉得非常羞愧。
第二她说你的话和心灵鸡汤没有区别,我发现她说的是对的,因为心灵鸡汤渗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爸这样一个五十多岁酷爱健身的中年男子也开始每天微信上面给我传一些文章,《犹太人教育孩子的五十种方式》《一个女人一生要看的三十本书》《孙红雷怎样教你做男人》之类的文章,他每天给我传这样的东西,还有各种震惊系列,什么《90后的话让世界震惊了》《小三的话让局长震惊了》等等。确实我发现连他的生活都被这样的东西所围绕,而我也非常惭愧地写过一篇心灵鸡汤的文章,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恶心的文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成为我流传度最广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类似“高三我只相信血泪”之类的,讲我高三怎样奋勇学习、六亲不认的故事。很多中学校长会在升旗仪式上带领全校朗读这篇文章,还有印了几百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感觉非常像邪教的做法的现场。这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恶心的一件事,但恰好很多人说那篇文章提供了非常大的鼓励。
她说的第三点,你说的话自己相信吗?我一直想,相信还是不相信,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第一次对这句话有感触是2008年高考刚刚结束,我就去了北川、汶川、成都等等。我去的理由也没有那么高尚,理由非常浅薄也非常自私,因为在高三我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应试机器,我需要一些真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把我从高三那种状态中解放出来。
我去了灾区,看到很多很多事实,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事情。比如当时灾区分配食物,你会看到很多人争抢。我也看到北川刚刚开放,可以让居民回来取自己的东西,看到非常衣衫褴褛的人扛着非常巨大的彩电,很明显不是他们家的。你看到人性接受非常多道德考验的时候,这种考验其实让当时的我稍微有一点失望。
上了大学,我选了一门“社会主义实践”的课,老师也提到灾区,当然提到的都是报道当中的正向的、积极的、催人泪下的事情。我当时跟老师说我看到的不是这样,我站着跟老师对峙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还是坐下,我发现自己是失败的。
我发现一个事实,当你相信一件事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变得容易很多;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会痛苦很多。如果我相信老师讲的,而不是自己看到的,我的生活会容易很多,我不会有跟老师对峙的尴尬,和失败之后的落寞。
从七岁开始写作,现在已经写了19年,对于写作的观念其实变化了很多。小时候,我觉得写作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一点,我感觉文章是可以救国的。再大一点,我觉得写作可以影响一代人。到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写作对作家而言并不是主流文化的反叛英雄,拯救的只是作家自己。
我把这个《堂吉诃德》音乐剧中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妄自翻译,念给大家听:
听我说:此地荒凉,难以忍受,艺术尽毁,品性败坏,骑士诞生,战袍招展,扔下手套,向你宣战,我只是我,堂吉诃德,使命召唤,我便出发,宁愿狂风,载我前行,风吹之处,荣耀之至,我之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