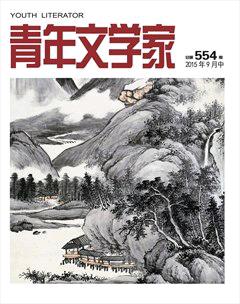博尔赫斯小说中的迷宫形象浅析
孙祎娜
摘 要:迷宫式博尔赫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通过《阿斯特里昂的家》,对博尔赫斯迷宫的构建方式、与镜像和永恒的关系,以及被困其中的囚徒形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博尔赫斯;小说;迷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6-88-02
我是在父亲图书馆的一本书里发现的迷宫插图。那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土话,整整占据了一页纸,画的是一座建筑物,有点像一个圆形的竞技场。我记得场地中间有个陷下去的洞口,视角是从高处向下看,高度比松树还要高,能看到围观的人的头顶。这个视角并不是最佳的,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但是我当时想,如果给我一个望远镜,我就能从洞口中看到一只弥诺陶洛斯。此外,这个圆形的形象也是复杂性的标志,是在生命中迷失的标志。我认为所有人都曾有过这种迷失方向的经理,在迷宫中我能看到这种迷失的表现。从那以后,我就保留了这种看待迷宫的视角。
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迷宫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的,有各种各样的迷宫形象。有时,这个迷宫有着宇宙的影子(《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博闻强识的富内斯》);更经常地,它是人类的眼中看到的世界的形象,即人类文化的形象(《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巴别图书馆》);或者一个用来是人类迷失的地方(《阿斯特里昂的家》);一种混沌的表现形式(《巴比伦彩票》);一种秩序的表现形式(《巴比伦彩票》,《巴别图书馆》);一种不可理解的事物(《博闻强识的富内斯》);上帝的文字(《神的文字》);非人类的东西(《永生》);严密的逻辑(《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博闻强识的富内斯》);理智(《死亡和指南针》)等等。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有另外两个要素与迷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永恒和镜子。一个完美的迷宫是永恒无尽的,就像沙漠中的沙子或者芝诺悖论,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逃离一个理想的迷宫,甚至,任何一个迷宫都应该用它无尽的形象来让人心生畏惧。镜子能够复制时空的影像,在镜子中迷失就恰恰像是迷失在一个迷宫中。而迷失在有镜子组成的迷宫中,无疑就意味着被困在永恒中了。
《阿斯特里昂的家》对于理解博尔赫斯的作品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阿斯特里昂与博尔赫斯的创作有极其深的渊源。在博尔赫斯的许多之前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了这个神话形象,最终赋予了这个形象特殊的、独有的意义。在《阿斯特里昂的家》中,迷宫不仅仅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主题,还构成了全文的叙述方式。
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博尔赫斯在担任杂志主编期间,为了补充一期杂志缺少的几页内容,用了两天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依照博尔赫斯近乎疯狂地追求篇章精简的写作习惯,小说的主题必定是他创作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事物,并且小说结构一定有着内部的紧密逻辑。这个迷宫的建成,就如同作者将脑海中的一个图形重建在现实中,然后对每块砖石的位置进行整理,去掉多余的碎屑边角。
故事架构
故事开篇引用了阿波罗多洛的一句话:“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斯特里昂。”这个开篇与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直接说出了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另一方面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手法,让读者感觉最后的谜底其实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是明了的。事实上,要想在这个点就知晓故事的结局,需要读者具有相当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智慧。甚至,即使读懂了这条开篇语,也无法理解这个故事。因为,揭出谜底的线索分散在整个故事中,只有在读完全部故事之后,读者才能明白哪些才是真正的线索,这些线索的作用又是什么。博尔赫斯用文字构建了一个迷宫,其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里面迷失。
故事接着由第一人称开始讲述。“我知道人们指责我傲慢还有说我孤僻和精神错乱的。这种指责(到了一定时候我自会惩罚他们)荒谬可笑。”直接突出了阿斯特里昂的独特性格。他不仅觉得自己被人们侮辱(明显自己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而且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与这些侮辱相对抗。关于他的家,是这样描述的:“这里找不到女人的美丽服饰和宫殿的豪华气派,只能找到寂静和凄凉。这幢房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某些人说埃及有一幢相似的房屋,他们是在撒谎。)甚至连诽谤我的人也承认房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另一桩荒谬的事在于我,阿斯特里昂,是个囚徒。难道还要我重说一遍,这里没有哪一扇门是关着的,这里没有一把锁吗?”到底是什么样的房间不需要加锁?如果没有锁,是不是就意味着房间根本就没有门呢?阿斯特里昂说有时候他会出门,但是很快他就会感到害怕而回来:“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看了害怕,那些脸像摊开的手掌一样平坦苍白。”又是什么样的人脸总是挂着毫无痛苦的苍白?接着阿斯特里昂用无辜的语气继续讲述:“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一个小孩的孤苦无告的号哭和教民们粗俗的祷告说明他们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四散奔跑,匍匐在地;有的簇拥在牛角庙宇的柱座周围,有的把石块堆起来。我相信还有人藏在海里。”很明显,是阿斯特里昂在使人们感到恐惧,小孩的哭声,教民的祷告,以及需要用石块堆砌墙来保护自己,都证实了阿斯特里昂的出现的恐怖的。
阿斯特里昂讲述了他非常奇特的消遣方式:
当然,我不缺少消遣。我像一头要发起攻击的小公羊那樣,在石砌的回廊里奔跑,直至头晕眼花滚到地上为止。我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者走廊拐角,独自玩捉迷藏。有时候我从屋顶平台摔下来,磕得头破血流。我随时随地都能假装熟睡,闭着眼睛打呼噜。(有时候真的睡着了,再睁眼时天色已黑。)但这许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假扮另一个阿斯特里昂。我假装他来做客,我带他看看房屋。我毕恭毕敬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先前的岔口,或者现在我们进另一个庭院,或者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小水沟的,或者现在你将看到一个积满泥沙的蓄水池,或者你还会看到一分为二的地下室。有时候我搞错了,我们俩高兴地大笑。
阿斯特里昂一个人住着,甚至他能在这个对称的、房间纵横交错的家中迷路。这样的房屋之所以建成像迷宫一般,很可能就是为了让住在里面的人永远无法完全地了解它。但是阿斯特里昂不仅在这个家中玩耍,还对房屋进行过思考:
房屋的所有部分重复了好几回,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地方。水箱、庭院、饮水槽、饲料槽不止一个;饲料槽、饮水槽、庭院、水箱各有十四个(也就是无限多)。房屋同世界一般大;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一切都重复好几回,十四回,但是世界上两桩事只此一回:上面,是错综复杂的太阳;下面,是阿斯特里昂。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楚了。
这世上唯一重复的事物是太阳和阿斯特里昂,而没有沿用故事中一直弥漫的昏暗场景(黄昏或者夜晚),太阳这个代表光明的意象,是作为作者的存在而出现在故事中的:照亮这个奇幻世界的光亮,正是博尔赫斯独特的想象力。
每九年有九个人走进这座房屋,让阿斯特里昂帮他们解脱一切邪恶。仪式仅持续几分钟,他们倒下去,阿斯特里昂手上没有沾一点血迹。当其中一个人预言说总有一天阿斯特里昂的救世主会到来,他很高兴,从此以后不再因为孤独而感到痛苦,并开始想象救世主的样子:“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最后一问给出了读者唯一的答案——故事中的我,是一个人身牛头怪弥诺陶洛斯。而阿斯特里昂最终的结局也在结尾给出:
早晨的阳光在青铜剑刃上闪闪发光。上面没有留下一丝血迹。
“你信吗?阿丽安娜?”提修斯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
回想整个故事,就会发现所有的线索和答案:阿斯特里昂就是弥诺陶洛斯,他的家便是迷宫,因此阿斯特里昂的出现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他会认为所有人的脸像手掌一样扁平;因此,他杀人却不会弄脏双手(因为用角),还会像小公羊一样奔跑。当阿斯特里昂把自己同太阳相比较时,他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他并不自知自己的兽性。这篇小说的重要性,就在于博尔赫斯在其中第一次面对了居住在迷宫中的人物的命运问题。
迷宫形象
在故事讲述本身,博尔赫斯做了精心的构思,将阿斯特里昂的真实身份隐藏到最后。首先,所有对人物和其住所的描述都是模糊的;其次,作者用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阿斯特里昂在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读者一直都以阿斯特里昂的视角去试图理解周围和发生的一切,不到结尾没人能想到博尔赫斯会借一个怪兽之口来表达恶魔的内心世界。这个构思本身就是一个文字迷宫。这个以迷宫中的人物为主题的故事,恰恰是以迷宫的形式构建而成的。
小说中,情节展开的空间(地点)是阿斯特里昂的家——一座迷宫,最初迷宫是作为一座防御性的建筑存在,结果最终却变成了一座无法逃离的监狱。主人公用第一人称来讲自己的生平,描述内心的不安、恐惧、对世界的看法、與其他人如何相处,让读者感到他的无助和孤独,心生怜悯。随着情节的展开留下一系列提示,在最后揭示了主人公半人半兽的真实身份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受到欺凌、被幽闭在迷宫中的可怜的恶魔形象。
阿斯特里昂作为迷宫中的囚徒这一形象,可以看做是人类自身现状的象征,他被关在自己的家中,正如同人类被困在我们生活的周边世界中。这个无法逃离的迷宫到底是什么?
就想弥诺陶洛斯一样,他的外表是个追求强大、令人畏惧的恶魔,但在内心深处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阿斯特里昂,是一场未完成的祭祀中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害者。他的一生开始于一个游戏,终于一场悲剧。整个过程如同我们读他的故事一般,开始于简单地猜测主人公的身份,后来意识到我们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阿斯特里昂的迷宫中,最终发现原来阿斯特里昂就是我们自己,是人类自身不幸命运的象征。
阿斯特里昂说:“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了。”如果是阿斯特里昂自己创造了他的迷宫世界:星星、太阳和大房屋,那么人类创造的正是人类的文化。人们在文化中寻找自己在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生存方式和自身价值,结果发现,正是我们人类自己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精神监狱将自己禁锢起来,人们信仰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等待有一天这想象中的神会来把人类从这禁锢中解救出来。一方面,这个迷宫是可怕的,人们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修正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然后以新的文化为依托继续生活;另一方面,用阿斯特里昂的家来影射和反思人类迷宫般的文化世界,从阿斯特里昂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来检视人类相似的行为。这都是以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为镜的表现。
总之,《阿斯特里昂的家》是一篇浓缩了博尔赫斯迷宫形象的各个要素的小说,从文章结构上的文字迷宫,到故事中描述的迷宫房屋,再到实物迷宫所象征的人类的精神迷宫,结合其中的永恒和镜子意象,集中体现了博尔赫斯独特的迷宫视角——永恒。
参考文献:
[1]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张雅秋.镜子·博尔赫斯·我们[J].文艺评论 1998年第6期.
[3]马翔.对知识的迷恋与恐惧——解码博尔赫斯的“知识迷宫”[J].台州学院学报2009年 第5期.
[4]李泽晖.博尔赫斯小说创作的交织循环与无限延展[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02期.
[5]肖燕.敢于向天问——试从时空迷宫和主体自身迷宫解读博尔赫斯的《另一次人的死亡》青年文学家[J].2009年06期.
——读《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