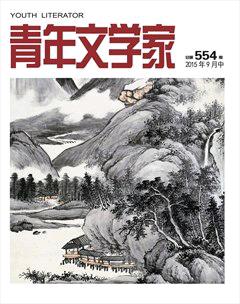艾布·阿拉·麦阿里及其“苦行”
摘 要:阿拔斯王朝(750~1258)又被誉为“阿拉伯文艺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统治达到极盛,不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学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1]。该朝后期,帝国呈现四分五裂的颓势,但这一时期的阿拉伯诗坛却奇峰突起,阿拉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被誉为“诗中圣哲”的盲诗人麦阿里正诞生于此时。本文旨在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当代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入手,结合特定时期社会特征以及诗人生平和诗歌创作,重点解析其“苦行”思想和行为产生和发展的渊源及特点,进一步理解出身名门、才华横溢的诗人选择用离群索居、清苦度日的苦行生活了却终身的深层次涵义,从另一个角度管窥在一个文明发达的“盛世”之中何以出现以“苦行”为标志的出世之风。
关键词:麦阿里;阿拔斯王朝;苦行;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李世峻,男,甘肃兰州人,1989年生,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现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6-84-03
一
1.“诗中圣哲”麦阿里——从“三囚人”到“苦行僧”
艾布·阿拉·麦阿里(Abu al-ala al-Maarri 973—10590),伊历363年出生于敘利亚北部的麦阿拉努尔曼小镇。其家庭属当地望族苏莱曼部落,祖父是部落中首位法官。三岁时麦阿里不幸患染天花,不仅先后双目失明,脸上也留下了凹凸不平的疤痕。之后当诗人从巴格达回到故里,选择称自己为“双囚人”,其中的“一囚”即指因早年失明而看不到世间的一切。然而,残疾并没有夺去儿时的麦阿里对知识和荣誉的渴望,反而激励他选择向命运发起挑战。他很早开始追随父亲和本地语言学家艾布·伯克尔·本·马苏德学习语言和语法的奥秘。麦阿里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从小便显示出非比寻常的学习能力。在求知欲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年轻的诗人拄着拐杖,先后朝着当时的文化之乡阿勒颇、安塔基亚、拉塔基亚和的黎波里进发。在这些城市,诗人遍访学术机构和图书馆,与当地学者交流、切磋,饥渴地汲取着学问的养分。一般认为,正是在游学期间诗人开始接触古希腊哲学思想。
当时,巴格达不仅是帝国的都城,更是享誉东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中心,自然对诗人有着难以言表的吸引力。伊历398年,怀揣一腔抱负的诗人辞别母亲辗转来到巴格达。在这里,几乎没有一次文学集会他不曾参加,没有一所学术之家他不曾造访。由于不愿用颂诗向统治者邀宠谋利,又与权威学者产生分歧,他仕进无门,在巴格达居住了一年零七个月后,终于选择离开巴格达。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又使他万分悲痛悔恨。继而回到家乡麦阿拉努尔曼小镇,开始其独居著述、“苦行僧”一般的清苦生活并终老至死。这里印证了诗人所说“双囚人”中的另一“囚”——将自己囚禁于家中闭门不出。同时,诗人又称自己为“三囚人”:即失明、房间和他抱怨的最多的被囚禁在肉体里的精神[2],诗人曾写道:
“我被囚禁在三重监狱,因此你别再问那隐秘
双目失明,在家蜗居
又将心灵藏在丑恶的躯体……[3]”
麦阿里青少年时期便著有诗集?燧火?,后在避世期间又相继完成《鲁祖米亚特》、《宽恕书》、《章节与目的》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麦阿里的诗歌不仅频繁涉及宇宙之奥秘、人生之哲理,更有许多带有明显的“苦行诗”色彩以及唯理不信的价值观。例如他曾作诗道:
“世上众生本贫穷,真主之仆无所持。”
“我生乃磨难,我死方安生;世间女子所生儿,与囚徒无异。”
“那愚迷轻鲁之人啊!倘若你还附有理智,就应常常叩问于他,理智就是你的先知。”
2.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其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4]。科尔曼[5]理性选择论以“理性”为基础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6]。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权利、行动种类等基本概念。首先,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7]。行动者即“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社会经济行动。一般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因此,两个以及以上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人际互动。“行动”本身有三种不同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由于中只有一个行动者,故这种行动“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行动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而那些人则控制着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8];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以期获得更多资源。资源的种类包括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等,这些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等性质。[9]”而行动者的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与偏好。
二
出身名门、才气纵横、追逐荣誉的麦阿里原本可以像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凭借名声和成就骄奢淫逸,通过称颂统治者过上富裕、荣耀的诗人生活。然而,他放弃了这些选择,满足于终其一生的“囚徒”之路。同时期还有不少同他一样选择苦行生活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均与当时当地那朝气蓬勃、发扬韬厉的时代精神大相径庭,这种可称之为“异化”的现象背后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10]。站在科尔曼的角度纵观麦阿里一生,其所遇到的三个决定人生方向的重要拐点——决定前往巴格达、选择离开巴格达、决心独居苦行均与“理性选择”不无关系。
首先,在麦阿里的“行动系统”中,诗人本身为“行动者”,其在古希腊“理性”哲学传入半岛的背景下对于理性的推崇与实践也表明他符合“具有目的的理性人”这一标准。然而诗人所掌握的和控制的“资源”及其追求的“利益”以及所完成的“行动种类”在三次拐点中却相继发生了变化。诗人前期的“偏好”主要有三:知识、荣誉和声望,这些非物质的偏好实际构成了诗人所追求的“利益”。家乡早已无法满足诗人的渴求,后期游学所至的阿勒颇等地也因其混乱的政治局势以及法蒂玛王朝和罗马人的争斗让诗人所追求的“利益”在这里化为泡影。于是,下定决心辞别母亲前往巴格达成为诗人在人生第一个重要拐点所做出了的能够使其效益最大化的合理选择。
在巴格达,麦阿里所掌握的独特“资源”——其卓越的语言技能、诗歌天赋以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成功帮助诗人获得了预想中的声望和荣誉,以至于“巴格达的文学家、学者、语言学家没有不知道他且喜欢他”。这一时期,诗人渴望人际互动,用三种行动类型中的第二种即将自己控制的“资源”与他人交换,以期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天性耿直、自尊使然,诗人“并不称颂统治者和官员,不接受馈赠和礼物,更不羡慕旁人”。在诗人看来,统治者是“魔鬼掌权[11]”,他拒绝用自己的“资源”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恰恰能使自己获利的大部分资源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此时的社会风气被黑暗和腐朽所笼罩,为了个人物质享受和私欲而大肆谄媚、四处行骗、毫无怜悯之心和道德可言的奸诈之徒比比皆是,诗人阅尽世态炎凉,清楚地意识到意图采取行动扭转眼前的世风是何等的困难。要获得这种行动的权利取决于两个方面:自身的权力及他人的承认。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要获得多数人乃至统治者的承认自然是天方夜谭。在行动权利被剥离的情况下,诗人的偏好和所求的“利益”演变为保存自己的尊严,努力唤醒守旧、麻木的世人,揭露谄媚、虚伪的小人。诗人断绝了与统治者进行互动的念头,实际上舍弃了最初的行动种类而选择了科尔曼理论中的第一种: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控制本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按照科尔曼的观点,这一行动虽不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却足以让少数做出选择的行动者流芳后世。这也是诗人在人生第二个拐点:在巴格达居住一年零七个月后毅然做出离开选择的另一重要原因。
回到家乡后,诗人又毅然决定终身不娶,放弃繁衍后代的权利。诗人对妇女心存芥蒂,认为妇女是万恶的根源。尽管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偏激、愚昧的,却客观上促使诗人做出放弃欲望、实现尊荣的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定。在他看来,独身是通向尊荣和真主恩赐的道路。他离群而居,专心著述,以青菜、蚕豆果腹,足不出户,将多余的家财周济乡里。此时,作为行动者的麦阿里选择了行动种类中的第三种:让渡(即放弃)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以求获得真正的“利益”。这里的“资源”有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财富、精神层面的情感(对尘世的留恋)。此时的“利益”,则升华为诗人自言“三囚人”中的第三“囚”:努力使被束缚在肉体中的精神得以解放。总之,诗人所选择“放弃”的目的,是对其所追求的最高层级“利益”的另一种“获得”。由此,不难理解诗人在人生第三个拐点所做出离群而居、苦行度日的选择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
三
麦阿里苦行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诗人对于“贫窮”和“富裕”的理解:那些没有忧愁、无患得失的人正是贫穷之人。他痛恨那些披着清修外衣、打着宗教旗号,内心却缠恋尘世、为自身谋利的人。独居近五十年,在“出世”期间却并没有断绝对尘世应负有的责任:他的行为、学识和思想感召了众人纷至沓来,聆听其教诲。选择出世的麦阿里并没有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继续其对于社会腐败、王朝弊病等问题的思考,试图通过言传身教尽可能改变不正之风、驱散浑浊之气。尽管认为人性本恶,却在诗中频频提及善行,认为人心是喜爱善的,智者能在其中找到欢乐和幸福。善应该出自自身的而非功利的“要求”,善若不服从与理性的判断就不称其为真正的善[12]。足见,此时的麦阿里没有舍弃同人民大众的人际互动,他选择继续将其所握有的物质、精神领域的资源与他们进行交换,以期获得更为高洁、朴实的“利益”:宣扬善行、精神解脱。此时的行动权利完全掌握在这位“智者”手中,也得到身边众人的充分认同,从而得以不受拘束、没有顾忌地行使自己的行动权,获取自己所追求的“最大效益”。
结语
面对尘世的诱惑麦阿里毅然选择不做欲望的奴仆、不随波逐流,并且坚守一生。“诗中圣哲”的哲学集学问、实践于一体,为后世做出最有力的表率。有学者认为,麦阿里在其所处的环境和悲惨的命运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苦行、厌世完全出于客观条件所迫;同时,理性选择论自身也存在着不足,集中表现在忽略个人的偏好、欲望等感性因素。诚然,诗人本身在做出抉择时也不可避免为感性因素左右。但是,在研究和评估其苦行思想、行为时不应忽略诗人本身的“理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分析阿拔斯朝“苦行、出世”这一社会现象时也不应离开对行动主体“选择”的重视。尽管麦阿里的一生备受争议,但随着以塔哈·侯赛因博士为代表的国内外现当代知识分子对麦阿里的逐步平凡和深入研究,一位真正的智者、诗人、哲学家的形象正在我们面前显现,并将照亮更多青年人的心灵。
注释:
[1]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2]汉娜·法胡里 著,郅溥浩 译,《阿拉伯文学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
[3]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
[4]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
[ 5 ]全名詹姆斯·S .科尔曼( J a m e s S.C o l e m a n,1927~1995),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曾是美国科学院仅有的四位社会学院士之一,被誉为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
[6]丘海雄,理性选择理论述评,《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1月
[7]同前注,第34页
[8]同前注,第39-40页
[9]同前注,第41页
[10]齐明敏,阿拉伯阿拔斯“苦行诗”与中国唐宋“出家诗”比较研究(上篇), 《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02期
[11]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16页
[12]汉娜·法胡里 著,郅溥浩 译,《阿拉伯文学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参考文献:
书目:
[1]汉娜·法胡里 著,郅溥浩 译,《阿拉伯文学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4]<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5]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译林出版社,2010年
论文:
[1]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2001年6月
[2]齐明敏,阿拉伯阿拔斯“苦行诗”与中国唐宋“出家诗”比较研究(上篇),《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
[3]丘海雄,理性选择理论述评,《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1月
[4]杨荣华,伊斯兰思辨神学的形成和发展,《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4期
[5]郅溥浩,诗中圣哲,哲中诗圣——记艾布·阿拉·麦阿里,《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3期
[6]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