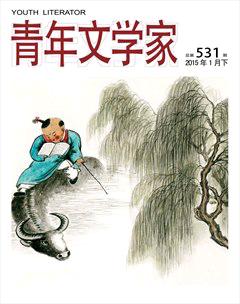探析野间宏小说《脸上的红月亮》中的人性观
胡备 孙爱婷
摘 要:野间宏的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这篇小说基于作者的战争体验,刻画了一个因饱受战争创伤,深陷悲观主义、对追求爱情也丧失了勇气的人物形象。在平淡无奇的小说情节中,对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写,使读者體会到野间宏对战争沉痛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
关键词:野间宏;《脸上的红月亮》;战争体验;人性观
作者简介 :
胡备(1959-),男,汉族,天津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日本语言文学、日本文化。
孙爱婷(1987-),女,汉族,河北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3-0-02
一、引言
野间宏(1915-1991)是日本战后重要作家之一,193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语系,大学期间曾参加《资本论》研究会及左翼进步活动。1941年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菲律宾。因思想进步一度触犯军法被关进陆军监狱。正因为野间宏作为士兵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战争,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脸上的红月亮》发表于1947年的《综合文化》杂志上,主人公北山年夫是一名复员军人,在熟人的公司里谋生,他偶遇战争寡妇堀川仓子,被她脸上的充满痛苦的美丽表情所吸引,但是,在与仓子的接触中,却不断勾起了北山的战争时期的痛苦回忆,他从仓子“白白净净的脸上的一个小斑点”联想到“战场上又红又圆又大的月亮”,“军人们发着高烧的黄脸”,沉痛的战争创伤与淡淡的爱情悲剧的重影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镜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小说超越了时空界限,用回忆和现实错落有致的叙述技巧,细腻地心理刻画,向读者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主人公北山年夫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国内对《脸上的红月亮》的研究主要有关于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的分析,以及对小说主题的阐述。而主题阐述大多指向对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对战争的控诉。日本木村幸雄的论文“关于《脸上的红月亮》”虽然发表于1963年,但因为是日本人的视角、以及更加接近小说的时代,所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笔者基于以上研究成果,通过比较作者的军队生涯与小说主人公北山年夫形象的关系,探析野间宏小说《脸上的红月亮》中所表现的战争反思与人性观。
二、小说的两条主线:恋爱与战争体验
《脸上的红月亮》的是围绕着恋爱与战争体验两条主线展开的。北山年夫从当兵前到复员后共有过三次恋爱经历。第一次恋爱以失恋告终,第二次是与一个“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他”,而北山并不真心爱的女子的恋爱。但是对于北山而言,这女人只不过是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满足自己的虚荣的替代品,因此北山对待这个女人非常苛刻。嫌弃他“缺少弹性的乳房”,甚至觉得那涂得血红的低级化妆术是对自己的侮辱!这个女人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满足不了对初恋念念不忘的北山,却仍然全身心地爱着他、信赖他。而北山年夫真正认识到她的爱的无价,是当北山进入战场后得知女子的死讯才开始的。于是北山在非人性的、残酷的战场上不断反省自己虚伪的爱,对不珍惜无私的母爱和女人的爱的负罪感不断反刍,痛苦不堪。
在这里野间宏并非是为了阐述爱情而描写这两段恋爱情节,因为,小说中这两个女人连名字都没有,而且,作者在强调这段感情无价时,有意地将其与母爱并列,所以应该说这种爱只涉及爱情的一个侧面——无私性。何况对该女人形象的描写丝毫不能让人产生美感,这也与精神与肉体完美结合的、理想的爱情大相径庭。实际上这里的爱情描写是作者有意将无私的爱与自私的“人的个体性”进行强烈对比,在思想上反映了人的自我否定、精神恋爱的高尚,在小说构造上也将恋爱和战争体验巧妙地连接起来。所谓“人的个体性”,也称为“人的肉体的个体性”是与人的群体性相对应的概念。人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可以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可以表现为个体性与群体性。单就个体而言,随着弗洛伊德对潜意识概念的提出,人的意识分为两个部分,即显意识与潜意识,如果说显意识体现的是社会性的层面,而潜意识体现的是本能的、自然的个体性的层面。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兵营生活对北山这样的新兵而言如同地狱一般,而人的个体性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也可以说人的动物本能如水坝开闸放水一般地被释放了。作为新兵的北山在部队里除了接受严格的训练,还会受到来自老兵的欺辱和私刑。正是这种非人的待遇才使北山领悟到母亲及女人无私的爱的无价,靠着这些爱的温暖回忆,北山才能勉强忍受着战争现实的苦难磨砺。
小说中的战争体验并没有描写和敌军拼杀的激烈战斗场面,而是通过行军等情节,突出在战争这样一个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极端条件下,因为食物不足,水源紧张,体力透支而引起的战友之间的“零和游戏”般的敌视现象。在战场上,“不要说和老兵,就是新兵战友之间原来的感情交流也消失殆尽了”。北山知道“如果自己的体力稍逊于同伴,就会立刻成为战斗中的落伍者,死亡就会立刻朝他袭来。当部队缺少补给时,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别人,那就意味着死亡。”战友之间为了食物互相仇视。在士官们的眼里,士兵的价值不如一匹战马。正如代理分队长对北山的呵斥:“你们死了有人顶,马死了拿什么替?”北山深刻地感受到了军队里的残酷,这是一个没有人情的世界。而北山却在内心深处唤起了对过去的爱情的强烈的罪感意识,这竟然成了他在非人般的战场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在拉着炮车的行军过程中,北山为了自己活命眼看着中川二等兵死去而不去相救。而残酷的现实是,在每个士兵都营养不良、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北山如果帮了他,自己就会撑不住,只能落得同归于尽的下场。因此,人的动物性,人的利己的本质在战场上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并被无限放大。
上述情景与野间宏的战争体验基本相同。
我在巴丹半岛的马里韦莱斯山中狭窄、险恶的山路上,背着沉重的步兵炮上的防护铁板,一边步履艰难地走着,一边想地狱也不过如此吧。由于热带气候,马背已经生疮化脓不能备鞍运东西,大炮只能分解后由士兵搬运,但四年兵以上的老兵不用搬,三年兵、二年兵只挑轻的零部件,而我们新兵不仅要搬大炮最重的部分,还要轮流替将校、下级士官背行囊。每当走得慢时,老兵们还要打我们。一个与我关系不错的新兵经常跟我说:“既然这样还不如让子弹打死算了!”不久他真的那样死了。[1]
战后的北山与战争寡妇堀川仓子有一段精神恋爱。吸引北山的是仓子外表常常显示的一种凄苦的美。北川蛮以为仓子和自己拥有同样的痛苦,因此两人是相互需要的,是可以在心灵上相互抚慰的。他很想要为仓子做点什么,并以此来摆脱挥之不去的对人性的不信任及自己所痛恨的利己主义。北山认为:“如果像他这样的人心中多少还存有真实和真诚的话,他想以这种真实和真诚去抚慰她的心灵,过新的生活。
但是也因为两个人有着各自的痛苦的经历,也使得北山在看到仓子时,常常陷入过去的痛苦回忆中。战场上的情景不断浮现眼前,北山惊觉自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痛苦和已经深入骨髓的记忆。甚至他开始怀疑母亲的爱,“在那个战场上,如果说有人会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别人的话,那除了母亲之外就没有别人了。可是,即使是母亲,也是很可疑的”。此时的北山,已经深深地陷入到对人的不信任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了。戰争创伤最终导致了北山放弃仓子,结束了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
三、小说中的人性观
所谓“人性”不是仅指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事实上存在的特性,而应具有“理性的人”的意味。来自西方古希腊传统的人性观认为,人的特性是有知识的、理性的,故当将人区别于野蛮人时使用“智慧的人(homo sapiens)”概念。与此不同,继承了希伯来主义传统的人性观认为,作为被神所造的人首先应是“宗教人”。中国古代孟子提倡人性本善,荀子提出“性恶论”,而世硕、王充等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近代的人性观受人本主义(humanism)的影响,对人性的看法更趋于包容。
《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北山年夫对战友见死不救,能否证明“人性恶”呢?当然不是。实际上那是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的本能反应,这就是人的肉体的个体性。木村幸雄对此评论道:
这绝不是由于所谓的“利己主义”。他心里对中川二等兵非常同情,但这种同情无法逾越“人的肉体的个体性”的坚硬墙壁。在严酷的战场上,人的肉体性的界限不是以抽象的形式表现,而是以“人只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命,自己治愈自己的痛苦,用自己的手挽救自己的死”如实地逼近着我们。[2]
木村进一步指出从野间宏作品思想的整体来看对于“这种在战场所被迫形成的人的个体性的自觉,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而将其作为‘战斗的人的自觉意识给予肯定[3]”。这一点被大多国内研究者所忽略。其实从小说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旁证。例如,在描写主人公形象时:
北山年夫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身上带有长年在军队生活所形成的放荡不羁、疲惫沧桑的特征。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熬过了军队生活以及战争苦难的人,他的内心很坚强。[4]
另外,北山与仓子交谈中也说道:
“当然,我并不认为6年的军队生活把我的人生彻底搞垮了,永无出头之日!……我一定会很快找到我要做的事情!……我会从内心发出力量来!我什么都能干,幸亏军队把我身体改造成现在这样。”[5]
更值得思考的是,野间宏所在部队于1942年1至4月期间对美国、菲律宾联军发动的巴丹会战大获全胜,俘虏了大约6万菲军和1万5000美军官兵。随后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虐囚事件——巴丹死亡行军。结合小说的描写不难想象,那些被压在底层的士兵遇到真正的敌人将会如何表现。
综上所述,《脸上的红月亮》与其说是对战争的控诉,毋宁说是对战场上人的个体性的深刻阐述。正如木村指出的“可以认为野间宏对于人的个体性问题,是从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将其视为巨大的矛盾来处理的。因此,《脸上的红月亮》中只不过是聚焦在其否定的侧面而已。[6]”
总之,《脸上的红月亮》是一个通过爱情与战争体验两条主线交错编织的故事,其主旨不是阐释爱情,而是深刻解剖战争中的人性。人的个体性不同于利己主义,只有在战争中才会被无限放大。在残酷的战场上,人的境遇如此悲惨只有亲身经历之人才能体会。特别是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野间宏在小说中对战争的反思并没有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追问战争的非人性,其影响更为深远。可以说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北山年夫所经历的人的个体性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人类还没有找到杜绝战争的手段,野间宏的这篇小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转引自木村幸雄:「『顔の中の赤い月』について」35页
[2] 同上33页
[3] 同上38页
[4] 日文版『顔の中の赤い月』,笔者译
[5] 同上
[6] 木村幸雄:「『顔の中の赤い月』について」38页
参考文献:
[1]莫琼莎著:《野间宏文学研究——以“全体小说”创作为中心》,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崔新京:“文本解读: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日本学刊》,2001年第6期。
[3]唐承红:“自我保存的利己主义—评野间宏的,《阴暗的画》和《脸上的红月亮》”,《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6月第12期。
[4]木村幸雄:「『顔の中の赤い月』について」,『福島大学学部論集』第 21号,1969年11月。
[5]野間宏:『顔の中の赤い月』,筑摩書房,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