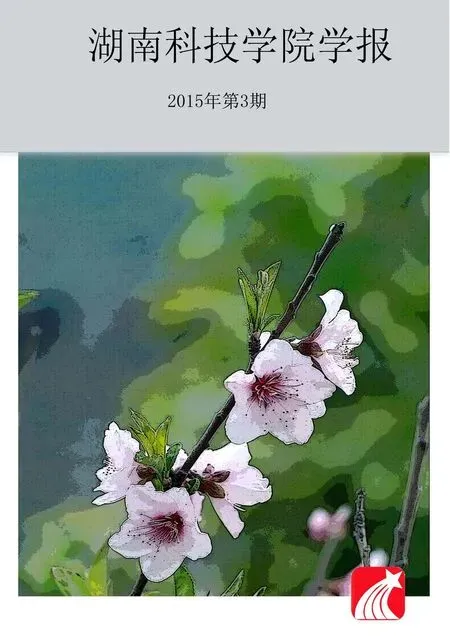我们的干爹石山保
陈泳超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永州朝阳岩是一处铭刻丛萃的著名区宇,坐落在今湖南零陵城西潇水边。我之所以想念它,是因为喜爱柳宗元的《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此诗六句,在唐诗中并非主流,却很有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意思;更让我倾心的是,该诗描画的是山水云天的萧散意境,却以拗促顿挫的仄声韵出之,其情韵之间的妙味,吟哦再四,犹有余香,而诗中的“西岩”,据说正是朝阳岩。某年初冬季节,我赴永州地区做较长时间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寄居湖南科技学院。该院踞于柳子祠和朝阳岩之间,我工余之暇,亦时时徜徉其间,发抒些今古幻织的菲菲之想,颇有澄意歇虑、调节身心之功,然而一直没有亲临朝阳岩,总觉得就在身边,随时可去。
真正激发我去朝阳岩一探究竟的,是该院教授、北大学长张京华先生。某次席上,京华兄说他正带着学生将朝阳岩所有石刻墨拓下来,要做一个完整的资料汇编及相关研究,他兴奋地向我们诉说了墨拓工作的进展和种种动人故事,中间也夹杂着一些抱怨,主要是针对当地人总爱在石头上刻“石山保”字样,从而打破了古代文人题刻的完整性,对此他是很有些嗔怪之意的。我听说之后,反而,莫名地兴奋起来。所谓“石山保”,是当地广泛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即将自己的孩子寄名给大石头作干儿女,据说这样就可以保佑小儿顺利成长。我在永州地区看到过很多类似的表达,有的是写个纸条贴在大石头上,比如我在蓝山县舜岩的大溶洞口就看到这样一张有点发灰残破的贴纸(为排版方便,将原来竖行改为横行,下同):
长命富贵
石公石母台前更换乳名成石姣大吉
易养成人
而有的就直接在石头上刻字,格式差不多。显然,京华兄所说的“石山保”,应该就是“石公石母”的同义词吧。
怀着这个心思,我终于来到了朝阳岩,果然漫山遍野的裸石上随处可见此类“石山保”字样,通行的格式是:
长命
某某某寄名石山保富贵
非常简单,变化也很小,但铺天盖地,与丰富多彩的历代文人题刻交错混杂,颇为壮观。
朝阳岩作为天然山石,固然存在了不知几千万年,但作为文化景观,是从唐代元结开始的。元结在广德、永泰、大历年间曾两次出任道州刺史,在今永州地区留下了很多石刻题铭,朝阳岩更是他独具慧眼的“杰作”,是他第一个从“自古荒之”的自然状态下发现了其山水形胜,从而喜爱上了它,名之曰“朝阳岩”,为之写下了《朝阳岩铭(并序)》和《朝阳岩下歌》等作品,并第一个在此题刻,其目的是“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此后,朝阳岩果然“世人有知”了,历代文人题刻济济累累。经京华兄指导的学生汤军先生在其大作《零陵朝阳岩小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中统计,现存题刻唐代4通、宋代31通,元代2通,明代51通,清代33通,民国10通,现代1通,不详时代者17通。其中不乏周敦颐、何绍基、谭延闿等大人物的身影,其价值之高无须申说。我非常理解京华兄等实际墨拓者的心态:好不容易历经风霜雪雨留存下来的各种书体的石刻墨宝,被那些歪歪斜斜、拙劣难看的“石山保”打破灭裂,几无幸免,墨拓作品自然很难完美,非但影响了对古典文史艺术的研究,也使朝阳岩的实存面目大为减色,这或许是从古至今知识阶层的一致心态。但我心下却很愿意替“石山保”们发一声不平之鸣——谁的石头?谁有权利?
照理,一切山林水石是自然界的固有存在,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任何人物或阶层,对之享有法律、习惯或道德意义上的专属权,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是也。朝阳岩的山石,文人开辟出来题写诗文,并不表示这块区宇就变成文人阶层的专有物,民众照样有权在上面题写自己的心愿,他们甚至还有更充分的理由:文人们只是发挥茶余饭后的高雅情怀罢了,但对于民众来说,这些题刻却是为了维系代际生命的绵绵延续,具有某种神圣的使命感。文人雅士们或许嫌其鄙陋迷信,可是,像“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之类被传统儒生视为经典的说法,实在也不过是些玄妙的昏话罢了。平头百姓自然不敢指望去认天地为干亲,甚至像佛教回向偈中所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对他们来说也有些遥不可及。他们只是看着山石很坚硬,不易损坏,便为儿女认个干爹,这种简明可爱的万物有灵思想,寄托着民众深沉博大的生命关怀。朝阳岩上重重叠叠的“石山保”字样,乃至在非常危险的石壁上也偶有显影,充分可证。至今在朝阳岩下,仍然有很多香烛供养的痕迹,其理正同。
我这么说,并不是支持现代社会中在文物、景点乃至其他任何公共场所随意刻画的行为,事实上,对于时下这种屡禁不止的恶习,我也痛心疾首,与世人无异。其间的差异在于:当文物没有成为全社会共同认知的保护对象之时,它的存在仅仅代表了部分人群的趣味和价值,而部分人群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群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因为每个人都是绝对意志的自由存在。但当文物保护观念逐渐被社会全体或大多数人所认可,并由政府将之作为社会集体意志的体现而以政令、法律予以规定之后,文物便被视为整个民族国家的共同财富了,任何个人的破坏性使用,都将被视为非正当行为,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从历史上说,文物保护观念尽管古代也时有提及,但真正确立并形成社会的实施规则,还是在中国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后的事情。我们不能用现代规则去要求前现代社会的民众。
其实,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知识阶层来说,他们对民众在人格上或许并无太多歧视之意,甚至对于民众这些有点迷信色彩的习俗,也未必多么痛恨,关键是雅俗趣味的不搭调。如果这些“石山保”出现在普通石头上,他们可能视若无睹或一笑了之,但像朝阳岩这样被文人视为风雅集萃的所在,就难以容忍“石山保”们入侵淆乱了。问题是:文人就一定风雅吗?风雅之人就一定值得尊重吗?
我们来举两个朝阳岩的题刻实例。
例一:《零陵朝阳岩小史》中录有一幅奇怪的图表,上面两层是诗题和一首短诗,第三层画了一个稚拙的大兔子,然后是十二月卦象,再下面是两棵树形简图。此题刻在今天朝阳岩中已经找不到了,是张京华兄从明人黄焯的《朝阳岩集》中发现的。黄焯在集子中附记说:“右题镌于朝阳岩峭壁间,雨淋苔蚀已就馍餬。附刻于后,博雅君子幸鉴焉”。(李花蕾、张京华著《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研究》,第3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经京华兄考订,此乃宋代熙宁年间曾任永州通判的武陵人柳应辰所作,其考订的主要理由是柳氏一贯的“玄怪风格”。此言不虚,该题刻文字不难理解,那些图像到底是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明白,这跟“石山保”不是一般的神鬼莫测吗?那些拙劣的图像刻画,实在也看不出比“石山保”高雅几许。
例二:在今天朝阳岩非常醒目的位置有一硕大题刻曰:“何须大树”,后有跋:“丙辰伏日,天久不雨。流金烁石,忧心如焚。避暑朝阳岩,凉风飒然,不减箕踞长松下矣,题此志慨。彝陵望云亭。”其体量在朝阳岩所有题刻中可居前三之列。浅陋如我者,当时还以为“望云亭”是一处亭子的名字,或者是某个文人的自号,后来查找资料才知道是晚清民国时一位武将的大名。据《零陵朝阳岩小史》中介绍,望云亭“民国二年(1913)九月,随湖南督军汤芗铭至湘,出任湖南省第六区司令官兼道县知事。在任上为结好士绅,对起事农民,大肆捕杀。民国四年(1915),授零陵镇守使,陆军中将衔。民国六年(1917)病逝于北京”(第229页)。而网络上还有这样未经查证的补充文字:“他在道县不到一年,竟杀害起义农民近千人……当地仕绅感其‘功’,在武官衙门前建一石亭,题名‘望云亭’,后被群众捣毁。”原来还真的有过一个亭子叫“望云亭”!这样一位滥杀农民的赳赳武夫,只为耐不住暑热跑到朝阳岩来躲避几日,就自命风雅地弄了这么一通硕大无朋的题刻,普通民众为自家儿女保命起见,刻几个小小的“石山保”又有什么不妥呢?“望云亭”是被群众捣毁了的,望云亭的题刻大约因其刻崖太深且广难以刬灭,终于高悬至今,然而,这是朝阳岩的光荣抑或耻辱呢?
也许有好心人要调和:民众实在要在此地刻“石山保”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最好刻在空隙处,不要打破原有的文人题刻,这当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多数“石山保”确实是刻在空隙处的,民众也不愿意去刻在已经有字的地方,那样自己的宝贝文字同样会不清楚。问题是朝阳岩比较方便刻字的地方,早被密密麻麻的文人作品占据了,没给民众留下多少余地;而民众又无力去开发、磨平新的位置,只好挑已有题刻文字的空隙(文人题刻有其格式,留白甚多)去镌刻自己的心愿,按照他们的观念或许正是物尽其用也未可知,至于顺着“石山保”的文理笔式而侵犯了已有文字,确是势所必然。再说,文人题刻本身也从来就有后人刬去前人作品而自题其上的风气,甚至因此还出现专门以此为生的底层职业。据《零陵朝阳岩小史》中说:“据传:在当时,每有人游朝阳岩时,便会有石匠袖手以待。游人题字写诗后,便磨石刻上。甚至早先就把崖壁磨好,待价而沽。对于那些在朝阳岩吟诗唱和者,在他们眼中都是‘达官贵人’,再不济也至少是个读书人,纵然吟囊羞涩,在经营这关系‘千古’的事情时,也能慷慨一番。但对于朝阳岩的很多碑刻被磨掉,再转刻他人诗文,这些刻石者应难辞其咎。”(第283页)作者的这个态度我有点不认同,在国家政策和地方规约都不健全的时代,保护文物只是文化道义上的提倡,并非民众应该履行的职责,民以食为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朝阳岩就吃朝阳岩,并无罪咎。如果非要说“难辞其咎”,恐怕那些一心经营“千古”事业的文人,更要首当其冲吧。比如望云亭的“何须大树”,我就仔细看了,该题刻的周边还有不少未被磨尽的字划痕迹,显系刬除了前辈文人书法而非“石山保”之类民众刻画。如果不是望云亭这等汹汹气势,谁敢(愿)去做这么大规模的剗挖磨平工程呢?如其有罪,罪在望云亭还是石匠呢?更不用说那些瑟瑟然自刻“石山保”的普通百姓了。或许正是早就有此意念在心,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时去考察朝阳岩题刻并将所有能够找到的“石山保”一一拍照的时候,心里偶或也有些对文物破坏的遗憾,更多时候却充满着一种报复式的狞厉快意。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早已颁布,朝阳岩石刻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任何人再随意题刻,都将被视为违法,包括“石山保”,也包括任何文人墨客或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乡民们要继续发扬“石山保”的民俗,就只能另辟蹊径去寻求“他山之石”了。但我还要强调一点:作为文物保护对象的朝阳岩,绝不应该只是指那些文人题刻,包括“石山保”在内的民众刻画,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它们在立法之前已经存在,有的甚至还很古老,我拍摄的“石山保”照片中,最早一通是明代天启三年,它在文物意义上并不比朝阳岩半数以上的文人题刻逊色。所以,如果刬挖磨灭这些已有的“石山保”,亦须一律视为违法行为予以处置。
总之,民众与文人都生来自由、人格平等,当我们回溯历史、珍爱文物之时,亦须对相关的民众生活史予以了解之同情,否则得于物而失于人,就有失民胞物与的人间正道了。《零陵朝阳岩小史》中有一段话我颇觉骨鲠:
万历三十六年(1608),元结来游后第八百四十二年。游人题:“万古一囗”四大字,刻于青阳洞口。字大径尺,端庄圆润。惜郡人凿梯时毁其后部,不可得其姓名。郡间鄙人,为图一时之便,而置先贤遗迹于不顾,可哀可痛!宁其无父无祖也。(第166页)
汤军先生的业绩我非常赞赏,也很为京华兄有此高足而庆贺,只是在这个观念上,我难免要多讨教几句。我不知道上述凿梯行为是在有政府管理文物之前还是之后:如是之后,我同其呼吁(未必同其咒骂);如是之前,尤其是在前现代社会的话,鄙人则深不以为然。试想:一个不明来历的游人在此留下一通不疼不痒的题刻,本地“鄙人”便须爱护,以致生计事宜比如凿梯之类亦须规避,这岂非地道的阶级压迫逻辑么?“无父无祖”之呵,对于“郡间鄙人”实在太过寡情。我倒很想代替“郡间鄙人”们如是上禀:“无父无祖乎?那些游人也好,先贤也罢,我们从来不想高攀他们为父为祖;我们都有各自的父祖,并且,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干爹——石山保!”
(责任编校:张京华)

朝阳岩题榜、诗刻与石山保的交错状态 (拓本制作: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