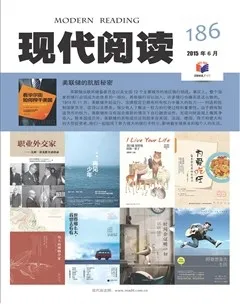沈崇走了!
那个曾使50万人为之上街,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倒台的女子走了!
当年本是偶然出现的不幸,随之是两种力量的角力,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后来事件更以她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沈崇事件”。
根据当时警方的记录,1946年12月24日晚,是年19岁的北京大学先修班学生沈崇在去往影院途中,被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皮尔逊强行带至东单广场奸污。次日,北平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发了一条新闻,迅速被各大报刊转载,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的极大愤慨,终于触发了震撼全国的抗暴运动。
事件的触发和背后力量的争持,时任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余涤清在其《中国革命史册上的光辉一页——回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抗暴运动》中有详述。不过,笔者个人研究和搜藏并不限于此,我更关心的是,大型群众运动后的个人,那随“偶然”之后而来的“必然”,她如何去面对?
她曾再一次受到伤害。事发第三日,北大训导长陈雪屏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一张墙报,更说事件是延安的“苦肉计”,是“八路女同志引诱美兵成奸”。
幸而,北大同学会主席刘俊英约了七八个女同学,以慰问名义前往杨正清(沈崇的表姐夫)家进行访问,终于弄清了沈的身世。
原来,沈崇192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祖籍福建闽侯,系出八闽望族。她的曾祖父是曾任清朝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外祖父是翻译家林琴南,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副部长沈劭,哥哥是驻法公使,陈雪屏更是其远亲。于是那“八路女同志”之说便得以澄清。大家闺秀的出身让她得到更多同情,社会愤怒的火烧得更炽烈了。“沈崇事件”最终招致全国各地50万人的示威,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塌。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为平息声势,不许她再去北大上课。她就回到上海,并在解放后改名沈峻。她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俄语,并于1956年在学校入党。毕业后去北京,进入中联部。但中联部发觉沈峻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太复杂,不合要求,因而调去对外文委(下辖外文出版社),在宣传司管书刊。后来外文出版社分出去,外文委独立成为外文局,沈峻便进入外文局,直至退休。
漫画家丁聪的妹妹丁一薇是沈峻在复旦时的同学,1956年于复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回京。丁一薇时常拉着沈峻去看丁聪,两人因此熟悉起来,1957年结为终身伴侣。“反右”运动时,丁聪被划为“右派”,其时沈峻已怀孕,大着肚子搬家。生孩子那天,正是丁聪发配北大荒之时,丁聪匆匆到医院,隔着玻璃窗,看看新生的儿子,随即赴北大荒劳改。沈峻说,“我们一家人,分住四个地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一家团聚。
按理,世事的不公,该令她性格变得阴郁吧?事实却又不然。
沈峻性格果敢刚毅,一派“大姐大”形象,很能干,也很会照顾人。三个妹妹都由她供读大学。丁聪夸沈峻“除了不会画画,什么都会”。她被尊为“家长”,一干好友也都以此称之。
沈峻乐于助人。丁聪的老友、原中调部驻港负责人潘静安先生1982年退休居京,晚岁卧病医院八年,期间沈峻常加以照顾。沈峻每星期都要从西城寓所骑单车去东单的北京医院看望他。潘喜欢吃牛尾,沈峻就常炖给他吃。几天不去,医院的人就会问,怎么“家长”不来了?
2012年初夏,笔者托沈峻闺蜜董秀玉(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相邀餐聚。席间笔者出示秘藏之“沈崇事件”文献,包括沈崇亲笔记录案发经过之自白书,及北京大学致该案代理律师赵凤喈之函件,另有当时报纸报道等彩色复印件,赠予沈峻。对着这些文件,沈峻默认她为沈崇真身,并对笔者有问必答,详述其出身、经历、事件发生后之情况、解放后的经历、“文革”间的遭遇,等等。笔者得以撰述《沈崇自白》一文,并通过董总呈请“家长”审定,后于当年8月发表。
沈峻说她自小已无法无天,到85岁高龄,还胆敢滑雪。丁聪2009年去世,享年93岁。隔了五年,2014年,沈峻去世,享年87岁。
(摘自《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