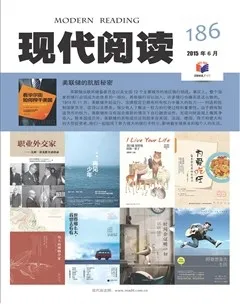坦赞铁路乘车记
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全线完成。坦赞铁路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
夕阳下,一列火车在大裂谷里缓缓穿行,铁路早已年久失修,列车行进时发出很大的“吱吱嘎嘎”声响。前方依稀看到一个东非村落。火车的到来,扰破了村子的宁静。
村落里,茅草覆盖下泥巴糊成的房子错落有致。远处,是大裂谷的重山与深谷,热带丛林在夕阳下映衬出玫瑰的颜色。这就是著名的坦赞铁路,是中国人给非洲留下的礼物。
坦赞铁路的诞生是因为赞比亚南下出口通路被敌对国家堵死。南罗得西亚雇佣军还曾深入坦赞铁路,破坏了铁路桥梁。因此铁路沿线民众被教育要“保卫铁路、防范间谍”,因此对造访的陌生人特别是外国人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坦赞铁路设有独立的警察部队,不受其他管理当局节制,有权盘查路人。因此,作为一个外国人,虽然可以毫无障碍地乘车旅行,但要想下车以笔者身份采访,则有诸多困难,存有危险。
经过多方联系反复交涉,坦赞铁路局终于向笔者颁发了采访许可证,并向全线下发了公函。这封公函起到了“路条”的作用,给笔者的采访一路开了绿灯,并在笔者后来遭遇人身困难时充当了护身符。
拿到采访许可证后便是买票。笔者的票比较特别,是一张允许中途下车的“自由全程票”。票价8万先令(约合人民币320元)是一等票(相当于软卧,但实际条件与国内的软卧完全是天壤之别)。
买到票后,笔者想要一张列车时刻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却很难满足。原因是,车站根本就不对外提供时刻表,就连车站自己也没有现成的。反复折冲了一个半小时,笔者才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获得了一份时刻表。
坦赞铁路每周开行两趟客运列车,每周二、五分别从起点达累斯萨拉姆和终点卡皮里姆波希对开。
由于车辆和线路保养较差,列车运行速度缓慢。按照时刻表,“快客”周二发车,全程45小时,平均时速约41千米;“普客”(即慢车)周五发车,全程48小时,平均时速约38千米。车开得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36年来缺乏对铁路的保养,安全事故频发,因此很多路段设置了限速,有的甚至限速到10千米/时。如此限速,当然就快不起来。
但实际上,连这样慢的时刻表,也很少遵守,晚点非常普遍且严重。坦赞铁路局官方统计的客车正点率为11%,而笔者个人感觉就连这个数字恐怕也达不到。如果说国内火车晚点以分钟计,那坦赞铁路的晚点则以小时甚至以天计。笔者认识的一个人曾乘坐过一次“正点”列车——晚点整整24小时。
一切就绪后,笔者准备踏上坦赞线西行之路。第一站是坦桑尼亚南部城镇伊法卡拉,距达累斯萨拉姆约357千米。
笔者出发就遭遇了晚点。原本应下午4点发车,拖到晚上8点还没动静。
此时,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人。车站有售卖水和干粮的小卖部,生意很是红火。当地人早已习惯了晚点等候,有备而来,因此并不十分着急。他们身上浓烈的汗味和香水味开始在这座中式建筑里四处弥漫。很容易判断旅客们的目的地:坦桑尼亚境内下车的,行李一般不多;去赞比亚的,则是大包小包,携带各种生活用品乃至粮食。这是因为坦桑尼亚物价低于赞比亚。不少沿线民众利用坦赞铁路做买卖,大多是小本生意。坦赞铁路就这样养活了许多当地人。
笔者都做好返回达市住处的准备了。不过,此时人群骚动,开始检票了。首先上车的是一等车旅客。笔者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到了检票口。笔者的坦赞铁路之旅,正是在这骚动、混乱和当地人的汗味中开始。
运输乏力、速度慢是坦赞铁路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实际运量远远没有达到设计能力,而且运输速度很慢。票价低,又因制度原因无法提高票价,因此客车是亏损的。收入主要靠货车。货车固定是每周两对,但是因为缺乏车头,所以货运时间难以保障,经常出现迟送乃至送不到的情况,让客户蒙受损失。久而久之,客户也就少了。没有客户,收入也就谈不上了。
过了检票口,走上站台,迎面就看到笔者将要乘坐的列车。虽然天黑,但笔者还是大致辨认出机车的型号——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的系列。车厢是老式的中国“绿皮车”,整个车厢看起来还可以,很难想象这居然是运行三十多年、从未经过像样维修的“老爷车厢”。
然而,毕竟是在非洲,完全没有电。车厢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幸亏笔者对这种绿皮车太熟悉了,才摸黑找到自己的铺位。褥子被子乱糟糟地放在铺上。直到灯光打开后,笔者才看到脏兮兮的铺上居然还有残留的血迹。
突然,“咣当”一声,火车剧烈晃动,把笔者晃倒了。原来,这是火车启动的动静。行进中,列车前后、上下、左右剧烈摇晃,坐在列车上好像坐在风大浪急的海船上一样,还时不时就来个急停,然后又是“野蛮启动”。晃动是如此剧烈,以至于笔者感觉列车随时可能脱轨。列车碾过铁轨接缝处时,时常“咕咚”一声,整个车厢都颠了起来。车厢交接处噪音非常大,发出非常刺耳的“吱吱嘎嘎”声。在车厢内行走,笔者时刻担心被摇晃急停的列车磕到或摔倒,甚至被直接扔出车窗或车门——这并非夸张,因为车窗很多都是大开的,经常是没有玻璃,有的车门也合不上,就这么开着。
虽然行前早就对此做了准备,服用了防晕药,笔者还是不争气地晕车了。在吐了个七荤八素后,笔者软绵绵地躺倒在铺上。
“你好!我要查票!”一声乡音打断了笔者的梦乡。不过,进来的却是一位黑人列车员。原来,他曾接受过中国专家的培训,会说点简单的汉语。见到有中国旅客坐他的车,他很兴奋。他说,他们太需要这种培训了,因为中国人不仅给他们带来技术,更带来一种勤奋工作的“中国速度”。“不知道中国人能不能回来做人员培训?”
随列车员而来的还有一位铁路职工大叔。他此行是前往伊法卡拉料理丧事。他的一位同事一周前不幸感染疟疾身亡。而伊法卡拉也正是笔者的目的地。
大叔名叫诺亚,55岁,已近退休年龄,在坦赞铁路工作大概30年了,还曾接受过最后一批“中国师傅”的现场指导。他说,中国人做事非常有秩序,对他们要求很严格,设定了目标就一定要完成,对员工的管理非常到位。他说,“中国人走后”,管理变得散漫了,经营情况也逐渐恶化。
面对笔者对车况的调侃,诺亚大叔不无痛心,说现在的车厢得不到维护,车厢的维修包给了外边的公司,但其实他根本没怎么见过像样的维修。给列车加水的车站原来有9个,现在只剩下了4个。乘务和卫生也极为懒散。
凌晨4点多,列车到达了伊法卡拉,此时已经晚点了八九个小时。车内外都是一片漆黑。令人吃惊的是,所谓的“站台”,就是一片凌乱杂草,没有半点灯火,看起来像荒郊野外。笔者顿时凌乱了,再三向诺亚大叔确认,这是伊法卡拉?若不是大叔再三坚定地说这就是车站,笔者断然不敢在漆黑的夜里下车,一个人被撂在这非洲“荒野”。
乘务员不见了,下车完全得靠自助。得自己扳开车门和挡板。也不见有梯子,需要自己跳车或爬下。幸亏大叔接过了笔者的行李,并把笔者生拽下车,算是平安到站了。
下车后,周围满是杂草,脚下是硌人的石头。周围都是黑黢黢的,似乎充满了危险。笔者提着行李,也提着心,跟着大叔在“荒野”里摸黑走了大概一两里,感觉过了好久,才看到前方一点点灯光。这才是真正的站台。
此后,笔者才意识到,这是火车司机故意把车停得离站台很远,以怠工方式消极抗议。笔者在伊法卡拉站的狼狈经历,折射出坦赞铁路紧张的劳资关系。
坦赞铁路刚通车时,铁路职工曾经是令人羨慕的工作。然而,今天风光已不再。铁路员工收入不高,而且经常被欠薪。劳资矛盾频发,铁路工人经常怠工和停工,甚至在笔者到访前曾组织了一起罢工。
劳资关系紧张的另一个侧面是劳动效率低下。在坦赞铁路的辉煌时期,曾有员工6000多人。现在员工总数大约2800人,但运量只有区区数十万吨。劳动力大量严重闲置,很多人没什么活干,工资照拿,管理层却囿于当地法律不能“无理由”开除过剩员工。管理层抱怨工人怠工且偷盗,工人则抱怨钱少且欠薪。笔者在采访中经常能感受到劳资之间的紧张感。
在非洲不少地方,工会势力非常强大。坦赞铁路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坦赞铁路的工会还分为坦、赞两方,以及总部机关工会、站段工人工会两大系统。在坦赞铁路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互不信任。这种紧张感是沉重负担,窒息着坦赞铁路向前发展的脚步。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寻路非洲:铁轨上的中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