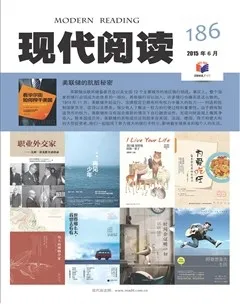《诗刊》:在噩梦初醒的年代
1976年, 那是噩梦初醒、曙光微露,但远非风和日丽而是风云激荡的年头,三中全会还没开,平反冤假错案正突破阻力进行,真理标准讨论波及全国;一个似乎偶然的机缘促成了丙辰(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人们满怀希望,期待着“每天出现的太阳都是新的”。
《诗刊》刚组织了一次关于“天安门诗歌”的座谈,这时正筹备开一个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为了要有足够分量的诗作,首先找了当年跟严辰一道从重庆前往延安的艾青。艾青虽寄居京城,“身份”却尚未分明,但先已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封杀二十一年后的亮相之作《我们的红旗》。艾青在诗刊社会见了才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不久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他是因参与天安门悼念活动中的表现,跟一些“同案者”一起被舆论称为“天安门英雄”的。这次访谈后,老诗人以高涨的激情,出手了长诗《在浪尖上——给韩志雄和与他同一代的青年朋友》。
诗刊社主办的这次朗诵会,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人们像前年“四五”前在天安门广场上,跟着每一句诗行心动神飞,却于悲愤难抑的同时羼上了几分胜利者的欣幸。掌声不断,泪水不断。这个场地,十年前万人大会上残酷批斗过彭德怀等高级干部,以及文艺界的“黑帮”,人们记忆犹新。这天来听朗诵的,有群众也有领导。散场时夜凉如水,听人喊“王子野”,我看到这位出版界的老干部眼眶还是红的。
由平反天安门事件触发,进而控诉十年浩劫,“义愤出诗人”也持续地反映到《诗刊》版面上。
柯岩从陶铸夫人曾志那里拿来了陶铸遗作诗词,立即交给作品组组长杨金亭去编选。她又出示陶斯亮怀念父亲的长文,《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大家读了,无不泪下。严辰、邹荻帆立即拍板:发!当时没有人像后来那样质疑,以为一个专业的诗刊,不同于时政性或综合性的杂志,为什么要刊出这一篇纯政治性的散文——是不是还囿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且不说大道理,单是编辑部三位领导个人的“文革”经历就能回答——严辰曾遭屈辱的殴打,邹荻帆右耳一下子被打聋,柯岩为贺敬之被当做“黑帮”揪斗,亲自上文联贴大字报辩诬……几乎所有经过十年动乱的人,后来对陶铸一家的悲剧无不感同身受。谁也离不开政治,反抗那害人政治的政治,就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感情的!过去以害人的政治压艺术不对,可也不能以艺术为名鄙弃公众的愿望和社会共同的利害啊!
我们先后找了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还有跟彭老总关系密切的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盼她们写写对彭老总的回忆。但她们对《诗刊》来人心存疑虑,推托婉拒。他们受骗受害太深,很难轻信陌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假如在《诗刊》刊登陶斯亮文章后,拿给她们看,也许会打消顾忌。但那文章首发于12月号,我们则是11月间去组稿的。
于是我写信给住在邯郸的“小八路”刘真,请她帮忙。刘真立马奔晋东南,重访八路军总部旧址,12月5日赶写出一篇情见乎辞的《哭你,彭德怀副司令员》。1979年1月号刊出此文时,前面冠以毛泽东1935年发给彭老总电报中的四句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诗末加注了多年前军报编者对此诗出处的说明。我原以为这表明了毛泽东主席与“彭大将军”间一向情深义重,完全没想到这一来会形同反讽。我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过当时读者都从大处着眼,对这一点忽略不计。
《诗刊》总算配合了三中全会为陶铸、彭德怀平反的示范性举措。全社同仁可以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否定“文革”出了力。
这时我们兵分两路,严辰和邹、柯两位一起,为在1979年1月份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做准备,我则接手为1979年组版的编务。不久,“文革”前老《诗刊》编辑吴家瑾也从山西调回诗刊社,跟我一起负责编辑部这一级“二审”;1981年初夏我成了副主编,主编们有轮值,她则成了“常务”。我们想在几位领导的既定方针下,尽量使开年一期继续有所出新。
严辰“文革”中被勒令提前退休回乡,1977年,李季向中宣部呈报拟请严辰出任《诗刊》主编,中宣部同意,并转中组部办理了恢复严辰在职干部身份的手续。严辰到任后,带动大家使《诗刊》适应政治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1978这一年的刊物,开始打破曾经一统天下的“帮腔帮调”,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力图改变既成之局,初见成效。如白桦《我歌唱如期到来的秋天》,写出粉碎“四人帮”时的真情实感;公刘《红花与白花》坚持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怀念;李瑛、未央以及新出现的曲有源、高伐林的诗作也饶有新意,当时“旅居”新疆的易中天(后来成为学者)和杨牧(后任《星星》诗刊主编)还合写过富有生活气息的组诗《十月的阿吾勒》。
被长期的软硬暴力压下去的全民诗情,有如地火运行。这时诗刊社每天的来信来稿从一麻袋增加到两麻袋,自发来稿中不乏血泪凝成的篇章。贵州作者李发模写因出身而受迫害的叙事长诗《呼声》,可以看做形象的《出身论》。
进入1979年后,有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人参加的全国诗歌座谈会成功召开。这是诗人们暌隔十年甚至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大规模重逢,也是重新集结诗歌队伍的一次集体亮相。艾青、公木、蔡其矫、吕剑等老一辈诗人,五十年代涌现的公刘、孙静轩、周良沛、胡昭等中年诗人,都曾经以作品活跃一时,却以种种罪名沉沦多年,这回聚首一堂,共话人的团结与诗的繁荣。这个座谈会由严辰、邹荻帆、柯岩共同主持,还请来胡耀邦跟大家亲切座谈。
事后检点,这次会的遗憾是还有许多该来的诗人没能来。一是像受胡风一案牵连的诗人们还没有进入平反程序;二是有不少诗人如流沙河、梁南等长久沉于底层,失去联系;三是有些老诗人从1949年后搁笔多年,像后来称为“九叶”的辛笛、杜运燮、郑敏、袁可嘉、曹辛之(杭约赫)以至穆旦等,已几乎为此时的诗坛所遗忘;四是老将多,中青少,诗歌新人乃大缺口。
大约1978年年末,一天,吴家瑾进门就兴奋地传告,《今天》(一本民间的油印文学刊物)张贴到诗刊社大门外墙的《诗刊》(街头版)旁边了,里面有的诗真不错!很快我也从别的渠道得到了油印本《今天》创刊号。我们选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给严辰看,他也十分赞赏。于是我把舒婷《致橡树》排进了四月号由铁依甫江开头的九首“爱情诗”中间,把北岛《回答》排进了三月号以《清明,献上我的祭诗》(姚振函诗,高莽插图)为首的一组中间。二诗引起很大的轰动,甚至引起争议不绝。大量读者能从并不显著的位置发现这两首短小的大作,足证由“样板戏”、“锣鼓词”和“东风吹,战鼓擂”主导诗风的时代即将过去了。
姚振函、北岛们这一辑清明献诗及连续几期刊发的关于天安门事件题材的作品,抒情的,叙事的,政论式的,都把发自肺腑的真情跟深刻的思想熔于一炉。彻底告别假大空的颂歌战歌之所谓政治抒情诗,书写说真话的、独立思考的、有所反思的诗,“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前后诸多新人新作,如张学梦《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骆耕野《不满》,以至部队文艺工作者叶文福规劝首长不要滥用公权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满城争说,都属于这一类型,是作者披肝沥胆的倾诉,即使有咄咄逼人的严酷批评,也蕴含着与人为善的热忱和冷静的思辨。接着出现的,关于烈士张志新的多首悼诗和关于刘少奇平反的诗,既适于在广场朗诵,也适于个人默读,因为无论是控诉,是辩护,都基于对历史的沉思,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选择,而不仅是一种亢奋情绪的宣泄了。
从辽宁爆出有关张志新的新闻,实际是一件旧案:四年前在那里,坚守良知的女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张志新被极其野蛮地杀戮了!新闻传出后,青年女诗人孙桂贞(伊蕾)在1979年4月7日晚至8日凌晨,用女性的笔喊出了诗的抗议:《一个死刑的判决》。北大七八届新生,从江西来的熊光炯诗题就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从学习李瑛情景交融的部队生活抒情诗起步的军旅诗人雷抒雁,也按捺不住,一改温雅的节调,从一个党员内疚的角度,写出了如泣如诉的抒情长诗《小草在歌唱》,唤起读者普遍的共鸣。他很快接到大量来信,其中一封寄自四川成都,对这首诗作了精准的分析和极高的评价。许久以后,才知道是胡风易名写的。他当时还没平反,却已情不自禁就诗发言了。
为了纪念张志新,《诗刊》还刊发伍必端教授石版画《临刑前的照片》,同时配发了当时腾传众口的两句箴言式的诗句: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到了天平上,使一切苟活者失去了重量!
因不知作者是谁,代署了“无名诗人”,后来才知道这位无名诗人乃是有胆识有文采的记者、诗人韩瀚。
在这之前,早春二月,诗歌座谈会后不久,组成艾青、邹荻帆领衔的诗人团队,沿广州、海南、上海、青岛一线海港采风,一路新作集成《大海行》专辑,陆续刊出。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