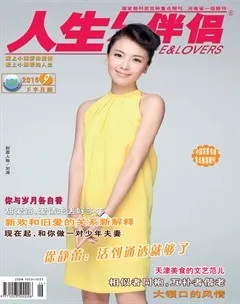天津美食的文艺范儿
据说在以前,北京的达官贵人,都爱坐上马车到天津玩,“吃尽穿绝天津卫”一点也不浪得虚名。
天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它跟深圳这样新兴的移民城市又不一样,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津人,都自称自己是个“老天津”。所以,天津的美食文化就总带着一些杂交的味道,比如在杭州吃过龙井虾仁,在天津菜馆里也能碰巧遇上清炒虾仁,做法同出一脉,即便有些调料不一样,但宗旨是相似的。
也许去过天津的人都觉得,天津的吃食文化透着一股浓浓的市井味,大多数好吃的都在街头巷尾处,比如吃煎饼馃子,就得找哪个街道小区门口,当地妇女掌勺一堆老太太排长队等候的摊子,味道总是没错的。
天津小吃的名字也总是离不开接地气,像狗不理包子、嘎巴菜、面茶等,这些现在都成了天津人爱吃的早点,听名字就能让人想起清晨临时搭建起来的早餐档里,烟气笼罩的幸福画面。
说到市井味的天津美食是如何跟文艺范儿挂上钩的,这不得不从我最近一直当作枕边书的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说起。里面关于天津包子的精彩描述,说刚出笼的包子汤汁咬破之后溢出,流到手掌上,沿着胳膊一直流到脊背去,还有咬下去溅了对面人满脸花,那人也不动声色,只有堂倌赶紧递上热毛巾……后来发现很多地方的小吃都开始沿用这个典故,我听得最多的便是广东中山的小吃金吒,也是说好吃到汁水倒流的地步。可见“好吃到忘乎所以”这个深刻形象,已经完全固定在食客们流着口水手捏着包子抬头往嘴巴里送的画面上了。
天津人虽然爱吃,但也爱耍嘴皮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天津美食的文艺范儿大概也源于这里。在中国那么多门派的饮食当中,与曲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当数天津了。甚至很多天津菜的起名都来源于传统曲艺,而在曲艺相声段子里也常会扯上吃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时候在厨房里随便拉出一个正掌勺的师傅来,让他表演一段技艺也能头头是道不输台上的艺术家,而曲艺界的名角儿进到厨房烧得一手好菜的例子也是很普遍的。难怪在美食界,“火候”一词的说法都源于戏曲,说的正是天津这种美食与艺术相得益彰的精彩,是真正的“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说起文艺范儿不得不提洋文化。打着文艺小资标签的上海是洋文化的主要代表,但是天津作为开埠大都市,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与世界接轨。说到天津的老西餐馆,当年张爱玲家隔壁的天津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便常常在黎明制作面包之后,把香味飘到她的家中,让人对这家咖啡馆无限向往。如今它安静地坐落在五大道一座不起眼的小洋楼里,依然保持着陈旧的模样,默默地供给着如今那些怀旧小资的文艺青中老年们营养,追忆着过往的似水年华。
最近看书,才发现曹雪芹是在天津的水戏庄写了《红楼梦》,单是这一部著作便能研究出几部关于饮食的著作来,但是凭借那讲究技艺又荟萃了古今文艺精华的各种小姐们的私房菜谱,就足以判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莫不是这天津味儿养人,才让曹雪芹文思泉涌?
近日坐动车去上海,8个小时的车程,饥肠辘辘,又不愿意吃车上的便当,看到杂志画面上的一笼天津包子,突然就想起自己竟然有那么多年未去过天津了。闭上眼睛面茶的芝麻香又从四面飘过来,那沿着碗边儿转着喝面茶的得意劲儿,还有把煎饼馃子的馃子抽出来就着面茶吃,吃完还得拿馃子扫一下碗底的幸福,便总是把那股好不容易攒起来的文艺气息忘掉,满脸溢出来的都是真实生活的俗不可耐的表情,倒也觉得,这才对得起那让人流连忘返的小吃档里,满嘴流油的快乐。编辑 / 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