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拍殖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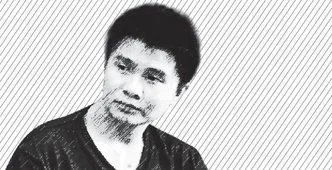
自拍已经变得和刷牙一样普及。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2015年毕业典礼演讲中分析了自拍。她认为自拍是一种“无休止的自我关注”以及“不停的自我放大”,这可能导致两个后果:削弱对于他人的责任感,或是形成对于他人的依赖。
也许喜欢自拍的人不会同意她的话。他们会说,自拍只是一霎那的自我欣赏,是日常生活中一瞬间的自我呈现。自我关注也没什么不好,英国作家王尔德早说过,自恋是一个人一生浪漫的开端。
我不认为自拍令人厌恶,但它令人惋惜。
当你在迷人的风景之中,不肯尽情用眼睛亲吻大自然,而是拿起手机,努力把自己和海浪、树木、鲜花框在一起。看上去你用手机得到了它们,实际上你却永远失去了。当你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时,你不肯沉浸在他欢乐的笑声中,与他嬉戏,而是拿起手机,拍下与他的大头合影。亲情在这刻不是升华了,而是被疏忽了。
自拍是对日常生活的轻度谋杀。我们不断拍下场景,用微信或微博发送,收获一个又一个点赞,而人生经验就在这过程中变得轻飘与零碎。借用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话,在自拍中,与我们不可分割的某种东西被夺走了——交流经验的能力。自拍不是高质的经验交流,它单向而肤浅。
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在《变石》中写道:“那过去的年代,大地腹中的宝石和天空高悬的星星还关系到人的命运,不像今天……星星不再关系凶吉,大量新的宝石被开采出来……但它们不再向我们昭示任何东西,它们与人对话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与别人对话的时代也过去了。很少有人愿意坐下来面对面、眼睛看着眼睛地交流。我们会谈论一切突发新闻,洪流般淹没我们的各种信息,但我们很少再与人谈论自己的生活。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未经谈论的生活则被一笔带过。
我怀念过去。那时候,人们坐在一起,听远方的人讲他的奇妙旅程,听本地的人讲古老传说。在这些奇妙旅程与古老传说中,人遇见了自己。
自拍,尽管可以为生活留存证据,但这些证据缺乏生命力。当我们老了,坐在庭院里,向子孙讲述过往时,我们应该依靠故事,这些故事一旦被讲出来,就插翅而飞。可如果只向子孙翻出那些自拍,你觉得他会如何理解你的命运?自拍将你的生活分割成彼此漠不相关的片断,抽走内在的喜怒哀乐,贬低为一堆干巴巴的数据化合物。
自拍是为了记住生活,但往往却通向遗忘。自拍是为显示自己的存在,得到他人的关注,但往往只得到廉价的赞赏,并在日复一日中依赖上别人的眼光。不自拍就会死,自拍了没人看也会死。我们的生活被自拍殖民了。我们的心灵,被自拍用镰刀割走玫瑰,却给荒草施肥。
是时候重新培养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能力了。放下手机,尝试着不依赖数码,而是用语言讲述关于生活的一切。当我们讲述时,就连废弃火堆中的灰烬也会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