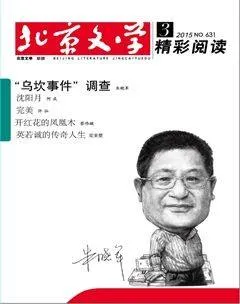吃尽漂泊之苦,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里有一种特别的骚动在折磨人,唯有文学创作能使它得到平静。为此,这些年我没完没了地拼,很艰难,很孤独,吃尽漂泊之苦。
我出生在云南小凉山,那里,可说是原始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交杂着持续到解放前,偏远程度可想而知。1986年夏天,我高考全县第一名,冲关而出,游学长春。1990年夏天,我走出大学校门,在滇中一个地质队熬了四年。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距小县城5公里。县图书馆很小,约有3万册藏书,却是我最关注的地方。两年后,我已经在那里找不到想要看的书了,跑到昆明,在省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和昆明市图书馆各办了一个借书证,每月跑到三家图书馆借一次书,单边行程大约5个小时。
1995年,我自动离职成为广大“边缘人”中的一员,处在体制的边缘,城市的边缘,生存的边缘,潮流的边缘。我的经历正是很多“边缘人”的经历,身不由己被夹入梦想和现实两扇石磨之间轧碾着,苦不堪言。
当时刚在昆明创刊的《大家》是我心中的圣地,我成为编外编辑。
不到两年我就离开了,先后进过云南的几家报刊当编外编辑,存了点钱。又辞职,写完一部长篇小说,钱花光了,又去找工作。写作时没有收入,只出不进。打工时,工资只有编制内人员的一半,仅够付房租和吃饭。有时某些单位欠着几个月工资迟迟不发。多年里,总有一种生存恐慌感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每到一处我都很出色,是一个答应了就要坚持干好的“责任狂”,但收入有时不到“在编”者的一半,要自己交房租,也没有福利保险之类。我看够了“多劳少得”的社会现象,也使自己想干的事一直干不了,生命浪费太大了。2001年,我上演了“英雄末路,春城卖刀,流落羊城”的一幕。
当时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了简单却未曾好好使用过的写作环境:二手电脑、打印机、价值约三万元的书、为了当杰出记者而忍痛购置的摄影器材和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这是我最喜欢最需要最离不开的东西,但英雄已到末路,只有变卖它们作为活下去的周转盘缠。这情景与秦琼卖马和杨志卖刀毫无区别,英雄身上只剩一把刀都拔出来卖掉了。我曾纳闷,这些人身怀高超手段,为何竟至于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却不去偷抢骗讨。轮到我了,也确实没有办法,只有三文不值两文出卖的“马”和“刀”,拿到了三千多块钱路费,望羊城方向流落而去。
这里有《花城》,在水荫路,有它我就不孤单。我跑到水荫路,看了一眼《花城》所在的大楼,正是国庆假期,它铁门紧锁。我满足了心愿:看到了《花城》所在的地方。我要在这大楼前的报刊零售亭买一本《花城》,摊主说,广州根本就没有这本杂志。我气得转身指着那大楼说:“喏,就是这里面出的杂志,连《花城》都不知道你还卖什么杂志呢!”他说:“凡是能卖掉的,我这里都有,我都知道。凡是卖不掉的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我到广州五个月了,常逛报刊书摊,竟然未找到一本《花城》。
我在白云区岗贝村租了个小单间,每月200元。它不通风,里面终日不见一丝阳光,外面丽日高悬,但屋里就像在晚上。深夜两三点钟,住在楼里的人仍像赶集般喧哗。为节省开支,像很多在广州打工的人一样,床也没买,在地板上铺一层报纸、放一张凉席就是床了。不过,我一个人住,他们一群人住,还是我优越。当时我已36岁,睡眠状态不好,突然就这样躺在了广州的一块如此环境中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更是难以入眠,把骨头突出的关节处都磨破皮了。广州冬天阴冷潮湿,别的季节闷热潮湿。这种情况下还幻想搞文学创作,那是天方夜谭。本想去京城,某行业报来了录用通知电话,但想到“长安居,大不易”,去那里只能变成可怜的房奴。
一年后,不得不吃回头草。昆明居,亦不易,但比起北上广,生存压力要少些,打工之余尚能兼顾创作。喘息间写出多部长篇小说,花在稿件复印、打印上的钱和投稿的邮票钱至少有1万元了,但稿子像飞蛾扑火。漂泊吃苦,时时被生存的巨大压力弄得喘不过气,几近绝望。
幸好内心里那只有着火红色毛发的野兽,在边缘地带深林中飘逸奔跑,在时光中发出咆哮。依然艰辛的2010年过去,我渐渐缓过气,《穿越佤邦》《戒毒大农场》《深深横断山》《凉山热雪》等书陆续出版,产生影响,获“金盾文学奖”,上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上榜2014年度中国有影响力图书推展……我本人也被媒体和读者称为“真正的实力作家”“草根大师”“未来诺奖得主”等。相信,有一天我会平静地去世。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