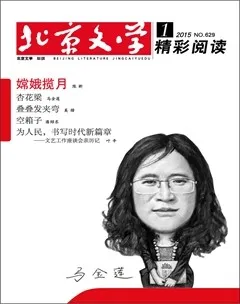真水无香
妈妈的话越来越少了。
往家里打电话,一般都是爸爸接的。如果我不是刻意让妈妈接电话,妈妈是断不会抢着接电话的。爸爸说,只要妈妈听说是儿子来的电话,爸爸在这头讲电话,妈妈在那头兀自偷着乐,一脸的知足。
有时候爸爸出去锻炼,或是到邮局取报刊,妈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的电话打过去,妈妈接过电话第一句话就会问:“你找你爸有事啊?”我说:“有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妈妈就说:“哦,那就等你爸回来再打给你!没有什么事就挂了吧,省点儿电话费,哈!”我正打算跟妈妈聊上几句,只听电话那边已传来无情的“嘟—嘟—”的蜂音。那时那刻,我就“恨恨地”想:难道妈妈就不想儿子?难道妈妈就这么“狠心”?
妈妈的“狠心”,我是多有领教的。
前几日路过家乡小镇,顺便回父母家探望。小坐了个把小时,临行,我们的车驶离家属楼,妈妈竟然跟着车走出好远。我打开车窗向妈妈挥手:“回吧!回去吧!”妈妈也不说话,只是远远地站住,直到我们的车驶离她的视线。
一向“狠心”的妈妈,幼时经常打我骂我的妈妈,无言无语中现出老态,我的心一阵发紧……
1
在我10岁以前,爸爸远在鞍钢工作,妈妈一个人拉扯着我和妹妹生活在乡下。一家之主不在家,我们娘儿仨基本可以被视为孤儿寡母。妈妈既当爹,又当娘,家里家外一个人。
小孩子在外面惹是生非是免不了的,通常是跟小伙伴打了架,回了家又要挨妈妈的巴掌。年幼不懂事,看妈妈既要种田,又要忙活家务,每天累得半死,我却成天跟小伙伴到处胡作,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一玩就是一天,天黑了妈妈不满屯子喊遍了绝不回家。这时妈妈就会气不打一处来,烧火棍、鸡毛掸子就飞将起来,在我的脊背和屁股上留下一道道绺子。
然而,一觉醒来,经不住小朋友的口哨、暗号,趁妈妈一不留神就溜之乎也。用妈妈的话说:顺着粑粑尿儿就跑了。妈妈气得不行,索性骂了起来:你这个披麻袋的荒料,什么时候能懂点儿人味啊?
玩累了,我索性决定独自一人去姥姥家过年。想不到,“狠心”的妈妈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那是1978年1月,也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此前七八年的童年,我几乎年年都是在姥姥家过年。不为别的,只因为姥姥家人多,热闹,有意思,当然姥姥的厨艺对我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鞍钢工作的爸爸为了省路费,常常不回来过年。
妈妈把猪肘子、猪心装进一个筐里,上面用一块花布蒙上,就含着眼泪打发我上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步,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接下来的生命体验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自是欢天喜地,完全不顾及妈妈的感受,着筐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
姥姥家在临近的另外一个公社(现在叫乡镇),与我家隔着三四十里的山路。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只有徒步行走。道路我是熟悉的,从一个村屯到另一个村屯,我都熟记在心。只是在两个公社交界处的山梁,灌木丛生,行人稀少,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但为了到姥姥家过年,我的凛然,我的义无反顾,早已将这些置之度外。走在无人的山间,我大声唱着无名的歌曲,给自己壮胆、打气,我有一种战争电影里孤胆英雄的感觉。我的脑门儿上有一种麻沙沙的凉意,但我的额头冒着男子汉的热气。偶尔有牧羊人走过,我不动声色地紧紧跟在那些绒山羊和绵羊的屁股后面,我闻到一股好闻的干草的味道,还有羊身上特有的膻味儿……
筐越越沉,我不断地更换胳膊。当两只胳膊都无法承受猪肘子、猪心之重,我就停在路边歇息一会儿。这时不断会有路人打趣地问我:“小孩儿,上哪儿去啊?”我就瓮声瓮气地回答:“上俺姥家!”当人家表示要帮我筐的时候,我便坚辞拒绝。虽然那时节没有人贩子这个行当,但我有着与生俱来的警觉。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妈妈嘱咐我,遇到陌生人,视年龄称呼大爷大娘大叔大姑,嘴一定要甜。那一刻,我全忘了……
我怯生生地走进姥姥家的院子,大黄狗率先认出了我,朝我直摇尾巴;然后是灶台前忙碌的姥姥喜出望外地喊道:“哎哟妈呀,这不是外孙狗么!”之后就开始数落:“你妈也真放心,这么小一个孩子,走丢了可怎么办啊!”不苟言笑的姥爷则露出难得的笑容:“这个小熊儿有点闯劲儿,将来是块料儿。”
我人生第一次徒步走向陌生的天地,妈妈下了怎样的决心,我是不得而知的。
那时没有电话,没有人告诉她8岁的儿子是否真的到达了她的娘家;那时只有写信,但邮局的效率之低,足以让一个孩子丢失一万次。
她唯一的期望,就是孩子再次真切地出现在她的面前,那要等到二三十天以后,与一封信的旅途相差无几。
妈妈的心,真够狠的。
2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简直就是个“病秧子”。腰酸腿痛大概是劳累所致,整日价的头痛,我基本可以断定是姥姥的遗传,因为妈妈像姥姥一样大把大把地吞吃着去痛片、安乃近这些白得瘆人的药片儿。
妈妈一有病,就卧床不起,哼哼呀呀疼得在炕上捶胸顿足。这时我已经稍微懂事,我开始学着做饭炒菜、喂鸡喂鸭喂猪,尽量让妈妈省心。
我首先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淘米。
淘米是一门手艺。
当年妈妈为了吃上大米饭,毅然远嫁他乡。她不仅教会了我淘米的手艺,还在那些寒冷的冬夜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我和妹妹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秋翁遇仙记”“卖花姑娘”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成为我一生念念不忘的“神话”。
时至今日,我时常有一种冲动,面对着即将入锅的大米,总想展示一下自己淘米的功夫,但是瓢呢,我已找不见。我知道,我有一种说不清的病。
这种病是妈妈给予我的,她“狠心”地让我过早地学会了淘米、切菜,让我过早地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即使我的左手在切菜时切出一个大口子,妈妈也没有惯着我,照样让我在学习之余做家务。只是如今,妈妈常常对着我左手长长的刀疤发呆,却没有半句后悔的话。
妈妈的心真硬!
3
在辽南的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负能量”的俗语: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
究其缘由,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线有战事,邻村在部队上服役的人有参战的,有牺牲的,也有负伤的。所以不少人家对孩子当兵多有顾忌,不少人干脆想方设法逃脱服兵役,把当兵看作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就亲眼看到,大姥爷家的二舅去当兵临行那天,大姥娘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儿子要去赴刑场似的。这件事,让我改变了对大姥娘一度的好印象。
我妈却不是这样,她对军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她极其羡慕她的大姑找了一位军官,整天“吃香喝辣”的。这朴素的追求,成就了我妈妈和爸爸的姻缘。22岁,妈妈与正在海军某部服役的爸爸经人介绍,处上了对象。一年后,爸爸转业到鞍钢,他们就成了婚。
只有高小文化的妈妈眼光是独到的,也有人说她命好,但不管怎样,尽管爸爸没当上军官,但这个受过部队锻炼的男人,在饥馑年代过后,基本上做到了让妈妈衣食无忧。
所以妈妈对当兵这条路是比较看好的,尤其是当军官,在妈妈看来,基本上是吃穿不愁的。
小的时候,妈妈就教给我一首儿歌: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爸爸兄弟两个,爸爸在海军服过役,叔叔在陆军服过役。于是妈妈就让我长大了当空军,当飞行员。我也在她的心理暗示下,整天骑着小马扎当飞机开。那时爷爷家门上钉着一个“光荣军属”的牌子,金属做的,漆着红漆,黄字,毛主席的字体。我常常跟小朋友炫耀这块牌子,上学时写“我的理想”为题的作文时,我都是写长大了要当空军飞行员,从来没有变过。
1989年3月,空军某部到家乡征兵。当时我正在读高中,偷偷报名参加了体检。镇里体检通过了,到县上体检却是需要跟家长沟通的,瞒是瞒不住了。
村里负责征兵的治保主任到家里说了,我也主动跟妈妈坦白交代了。当天夜里,下班回来的爸爸火气冲天,一场家庭论战的硝烟弥漫在逼仄的小屋里。
爸爸坚决不同意我走从军之路,一定要我考上大学,给他争口气。在他看来,我当时读高二,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文学社社长,前一年还在全国中学生诗歌大赛中获奖,前途一片光明,怎么能轻易放弃学业?然而我去意已决,与爸爸争吵得面红耳赤,只是爸爸碍于我业已成人,才没有向我抡起拳头。
这时,还是妈妈发了话:“随他去吧,没准儿在部队上还能考上军校,当个军官也不好说……”
爸爸还是不依不饶,直至声嘶力竭,那一刻,他简直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名革命军人。这时候,妈妈的眼泪流下来了,妈妈的眼泪成全了我。爸爸在万般无奈之下,一阵长吁短叹,答应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家里帮不了我。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穿上了军装。临走那天,妈妈没到镇上送我,也没说多少话。后来妹妹写信给我,告诉我上车之后,妈妈在家里号啕大哭。
两年后,我考上了军校。
然而,只上了一年军校,我的人生就出现一场重大的变故:因为一个无法言说的事故,我的军官梦迅速破灭了。确切地说,是妈妈的军官梦破灭了。
尽管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一心希望儿子出人头地的妈妈始终转不过弯儿。我退伍回到家乡,但我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走进自己的家门,“狠心”的妈妈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只好寄住在同学家里,直到找到工作以后,妈妈才慢慢地接受了我。
我不知道妈妈的心有多高,我只知道从小妈妈就自认为我比别人家的孩子优秀。妈妈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每次考试要求双百,年年要当三好学生,要第一批戴上红领巾,不一而足。不然,打骂是常有的事情。
我常常想,这个女人是不是我的亲妈?如果是,她的心怎么那么狠、那么硬?
我走上军旅的道路,除了践诺梦想,很重要的一条,是我要尽早地离开这个家。
4
自从工作、结婚之后,我回家的次数极其有限。除了工作忙、路途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妈妈在我的心目中难称完美,与许多人笔下慈祥的妈妈相去甚远。同时,由于我所受教育的局限,很少能跟妈妈面对面促膝交谈。有时即使面对面,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反倒是对妈妈的唠叨总是有些厌烦。
人到中年,我也常常反思:作为儿子,有什么理由要求母亲十全十美?什么理由要求一个农家妇女必须知书达理?母亲对儿女的爱,唯其朴素,才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唯其无言,才更值得生命的推敲。
在妈妈眼里,我是个不善于表达的孩子。
我想,我的讷于言是否有母亲的基因?我的敏于行是否成于母亲的狠心?母亲常常念叨着的“惯子如杀子”,是否是她的信念?只是她诠释得如此教条,甚至冒着让儿子误解的危险。
我该怎样形容我的母亲呢?
我想到了一个成语:真水无香。
明人张源的《茶录·品泉 》:“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真源无味,真水无香。”本意是表水,真水不在于显示自身价值,而能助茶发挥到极致,比绿叶红花之喻具有更高的境界。
倘若我是茶,妈妈就是这样的真水。一旦妈妈狠下心来,我的人生就有了些许的芬芳,淡淡的,一漾一漾,被不老的岁月渐渐化开。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