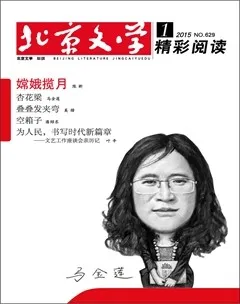为人民,书写时代新篇章
金秋的风把笼罩城里几天的雾霾吹跑了,北京又迎来了秋天里一个明媚晴朗的好日子。10月15日,我们在京西宾馆大楼前集合坐面包车,集体前往人民大会堂。通知说是7点45分准时发车。
我是7点40分走出大堂的,早饭之前,京西宾馆的大院里还有几分清冷。这会儿,太阳一出来,已经感觉暖洋洋的了。
我上了一号车,迎面见到了大个子冯骥才,和他握手招呼时,我发现整辆车已经全坐满了。我扫了一眼,贾平凹、王安忆、阿来、麦家、迟子建都在座,莫言坐在后排,作家协会系统通知的与会作家,大多坐在车上。和众人打了招呼,我在面包车第一排的里侧坐下。只一会儿,张抗抗也上了车,整辆车只有我身旁还有一个空位了,她坐下来,就打听这会可能怎么开。
于是有人说,我们只要到了会上,认真听总书记的报告就行了。
也有人说,还有人发言的,我们作协口就有两位。
张抗抗问:哪两位发言?都是女作家吗?
把座位都腾出来给了作家,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只得坐在司机旁边的车盖上,脸对着张抗抗说:“我们作协发言的有两位,一位是铁凝,一位是叶辛。”
抗抗于是问我:“你讲些什么?”
我说:“一会儿你就听见了,很简短的。”
13日下午3点20分,我走出从贵州飞回上海的机舱门,就接到了中国作协办公厅的电话,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请你参加。请不要请假。因为联系不上你,我们已经通知了上海作协,请他们给你订明天到北京的票。你拿到票之后,只要通知我们就行了,我们会安排车接你。”
她讲得清晰明白,我只说了一声:“谢谢。”
果然,到了出口处,上海作协接我的小罗就说:“你给办公室小周打个电话,他让我转告你,有重要事情通知。”
我给小周打去电话,他告诉我,已给我订了东航机票,明天下午3点钟飞北京。同时也会通知中国作协。
当晚7点,我正在吃晚饭,又接到一个电话,是李小东,熟人,他是老领导金炳华书记的秘书,现在也在中国作协办公厅任秘书处长。他说接到通知,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时间不长,7分钟左右,但必须在今晚写出发言稿来,字数在1500字左右,多晚他也会在电脑前等着。我有点犯难,问他,领导部门有没有说写哪方面的内容?他说没规定内容,建议你根据自己的创作实际,结合对当前文艺的看法,谈点自己的体会。
时间紧迫,我请孩子留下,一会儿等我写出稿子,让他们帮我把稿子打出来,及时发出去。
走进书房,想了半个小时,我决定结合自己创作近40年的一些体会,写一个稿子。
晚9点,我写出稿子,请孩子打出并发给了李小东。那时已经9点半了。
约摸十几分钟之后,小东来了电话,说稿子写得不错,但建议我改一个名字,因为谈生活学习容易和其他发言者的重复。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题目改成了现在发表出来的《捕捉时代的新意》。
虽经一阵忙碌,但是稿子定下来了,心中还是安定坦然多了。要不,仅仅带一点想法,或是准备个发言提纲,像平时开会一样,到了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始终会悬着颗心,惴惴不安的。
14日傍晚我抵达北京时,接我的女同志交给我一个稿子,说改了一处,你看看。上车之后我趁堵车,借着车外透进来的光,看了一遍稿子,发现整篇稿子,只改了第一句话,我写的是“我刚走出机舱……”改成了“最近”两个字。后来中国作协李冰书记当面给我解释,说铁凝主席从奥地利坐飞机赶回来,你又写刚走出机舱,有点重复。我表示完全理解这一细节上的改动。
14日晚,中宣部影视处长王强同志到我入住的客房里来,和我交流了发言注意事项并告知我是第六位发言者。
果然,当我们的面包车顺着长安街上时堵时畅的车流,于上午8点半抵达大会堂北门,上了台阶走进东大厅时,我又收到了一份稿子,我对比了一下,三份稿子字体不一样,一个字都没改动。但最后这份稿子十分清晰,字体也更大,年纪再大的人,不需要戴眼镜就能一目了然。
进大会堂之前,我们每位与会者都收到一条短信通知和一份书面通知,那是参加会议的注意事项:
1.带上身份证。
2.请着便装。
3.不要带照相摄影器材。
我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两会,每次要求代表、委员着正装、佩戴代表证,现在这样通知,我心里想,会议的氛围肯定更和谐融洽。
8点40分前后,参加会议的72位代表纷纷在东大厅自己的座卡前入座。我们7位发言的人士面对着主席台。我看了一下,坐在第一排右侧的是几位老同志:王蒙、冯其庸、陈爱莲、玛拉沁夫。他们后面坐着中国整个宣传口的部长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也坐在这一排。
坐在左侧第一排的也是四位老同志:欧阳中石,冯骥才、靳尚谊、李维康。
9点整,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为首,刘云山、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栗战书走进会场。全体与会人员起立鼓掌,掌声热烈持久,总书记双手两次示意大家才坐下。
在我的感觉中,会议是按三个部分进行的。从9点到10点20分,是7位同志发言。每位同志发言之后,总书记都作了点评、呼应,不时插话询问有关的情况。10点20分到12点整,100分钟里总书记就五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12点到12点半,总书记走到每位同志面前,亲切接见并和大家交流。整个会场里洋溢着喜悦热烈的气氛,欢声笑语不绝。
会议正式开始,总书记说:“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
开场白之后,七位同志轮流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她发言的题目是《牢记良知和责任》。她在发言中,又一次回忆到总书记和作家贾大山之间的感情,并提到总书记当年写的那篇《忆大山》。在她发言之后,总书记讲起了他当年和贾大山之间的交往和感情,肯定了贾大山对人民的感情和他对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疾恶如仇。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同志。他以《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体会》为题目,谈到了《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的创作体会和感受。
总书记对此回应说:你的戏我看过,很有现实针对性,真正起到了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作用。
在尚长荣后面发言的是人民解放军文艺战线上的老兵,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他的发言题目是《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发言开头就说道:“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在他发言后,总书记赞道:我赞同阎肃同志讲的风花雪月。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四位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以《关注视觉中国,弘扬核心价值》为题发言之后,总书记关心地问及中国美术学院的近况,许江一一作了回答。总书记笑了。
在第五位发言的中国舞协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赵汝蘅以《文化的力量》发言之后,我以《捕捉时代的新意》发言。安忆后来夸我,说你的发言最精彩、最实在,为我们作协,也为我们上海长了脸。总书记对你的发言回应得最多。
会后,不少同志都对我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而我个人,可能是太紧张了,觉得时间不长,一瞬间就过去了。事后看了中央电视台15日当晚、16日晚上的详细报道,和网络上的详尽叙述,细细回想,似乎确是像大家感觉的。
为说明问题,我将自己的发言详录如下:
捕捉时代的新意
最近,我又去了一趟贵州。上海的作家朋友们问我,你怎么对贵州乡下有那么大的兴趣,几乎一年要回去一次?我用一首小诗回答:明丽艳阳耀山川,洁白云朵绕山峦,冬春夏秋到山乡,四季景观不一般。这虽然有一点和朋友开玩笑的意思,但也是我由衷的体会。每一次回到我熟悉的贵州山乡,我总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带着泥土味的实感的东西,心中也就会萌动起一股创作的愿望。比如我这次去的贵州安顺西秀区的浪塘村,本来是去看美丽乡村风光的,没想到却歪打正着地看到了这个古朴而又传统的村寨上,用栽种农作物的生态办法,解决乡村里的污水净化问题。我绕着净化田走了一圈,一点儿也没有臭味,这不仅令我欣喜,还令我吃惊。因为我记得在参加上海市人民代表对市郊先进的农村污水处理站考察的时候,还做不到这样。
乡下的河道、小溪流、沟渠的污染,是一个谈论了很久、让人烦恼不已的问题。我不由得在污水净化田旁边站了很久,联想到今年夏季参加全国书博会后,我去贵安新区的布依族村寨,看到家家户户整洁的院落,寨子里弯曲的小路上铺设的既生态又平整的道路,院墙上充满布依族风情的农民画,和我40多年前插队落户时生活了多年的寨子相比,可以说是真正地换了人间。我从心底深处感受到,今天的贵州山乡农村,虽然仍是那么遥远而又安静,但是也在起着令人喜悦的变化。
差不多20年前,我写过一篇《两种生命环》的短文。在文中,我写到了作家应该不断地向生活学习,用两副目光来观察生活的体会。我初到农村插队的时候,经常是用上海小青年自以为是的目光来看待贵州山乡里的一切,觉得山乡偏远、闭塞,甚至还荒蛮和落后。但是,在村寨上待得久了,和贵州的各族老乡共同劳动,慢慢地我的目光起了变化,我经常也会用一双乡下人的眼睛,疑讶而愕然地瞅着县城、中型城市、省城,瞅着北京,瞅着上海一年和一年不同的新景观,并且把这些新的人和事带给我心灵的震颤用笔记下来。就是这样,当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往往会有新的灵感冒出来,新的创作冲动涌现出来。
35年前,当我创作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的时候,有出版社的编辑劝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怎么写小说啊?上面还在提倡要到农村去,客观上一批知识青年都在回城,你写出来,出版社怎么出,出版社的编辑也无法把握。我也为此困惑了很久,但是我后来想,我要写的都是我生活当中体验过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捕捉时代的新意,是会有读者的。所以,我还是把《蹉跎岁月》写了出来。事实证明,《蹉跎岁月》发表、出版,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以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20年前,我创作长篇小说《孽债》的时候,也有人劝我说,你这种故事,是知识青年命运中的少数。一个知识青年有两个女人,一个女知青嫁了两个男人,这种故事没什么典型意义。我也犹豫了很久不敢下笔,但是我回想起一个个有这种感情经历的知识青年跟我叙述到他们命运时的苦恼眼神,我想这是生活恩赐给我的,我应该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故事带着时代的烙印,它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感情经历,会给读者有耐人寻味的思考。后来《孽债》出版了,也改成电视连续剧播出了,同样受到了欢迎。
今年,我又写作了长篇小说《问世间情》。这本书写的是我们两亿多进城打工一族中时有所见的临时夫妻现象。又有人劝我说,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支流,不要去表现它。但是我看到生活中有过这种烦恼感情经历的男男女女,像生活中旋涡般打转转似的情景,而且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在呼吁关注这种现象。这是一种新的矛盾,处理好这样的矛盾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书出版短短几个月,就印了好几次。
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在生活中捕捉新意,可以说这是我40年创作的一个信念。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每一个有追求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应该为我们的祖国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书写新的篇章。
在我讲到这一次去的贵州乡村时,总书记插话问我:那是在什么地方?
我愣怔了一下,又把那地方放慢速度重述了一遍:那是黄果树附近的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浪塘村。
他点了点头。
在我整个发言完毕时,他又说:我和叶辛都是上山下乡的一辈(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又对着我说),你说的我很能理解,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艺术一定要脚踩土地,并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
接着,总书记满怀感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插队落户生活,讲到了他初次下乡的亲历,遭遇比现在PM2.5还要大的风沙时的真切感受,并讲到在农村插队落户时的情景,和农民交朋友,日子久了,他的住处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由他主讲,坐在炕上,和农民们交流感情。还讲起了有一次回城,他兜里揣着5元钱,豪气地对姐姐说:今天我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随便点。结果,姐姐想了半天,说想吃个榨菜肉丝。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听着总书记深有感触的回忆,我不由得想起了总书记在1999年给知青们的题词:广阔天地,永难忘怀。
可见他对插队落户生活,对上山下乡的岁月,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后来电视、网络上关于这一段,作了不少报道。听着总书记的回忆,我始终在点头、微笑,没有把他的每一句话记下来,十分可惜。但是他讲到插队期间,听说离开自己村子30里地的一个知青那儿,有歌德的《浮士德》,他专门抽了个空,约了个知青伙伴,走了30里地去向那个知青借阅这本书的情景,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广为传开,我也牢记在心。当他讲到那个知青起先不肯借,后来给他磨,他才勉强答应借三个星期时,大家又都乐开了。
因为回忆往事,人们不由自主感到,这段对话别有意味。如果说会后文艺界反响格外热烈的话,在我周围,在我手机上,曾经的一代老知青群体,反响也十分热烈。他们从天南海北给我发来一条条短信,表达他们喜悦和兴奋的心情。这是以往我参加任何文艺会议之后没遇到过的情景。“我太感动了!”“你太幸福了!”“真该好好祝贺!”一条条率直的表达真挚情感的短信把一代知青的心情都道了出来。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文联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同志。
他的发言题目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流》,题目似乎很平,但他声情并茂的演讲,配上歌谣,和他特有的音调及生动的事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不少的文艺界人士。包括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书法、摄影、曲艺、杂技、民间文艺在内的各界人士,都被他的发言吸引了。
事后,王安忆对我说:李雪健的发言时间肯定超过7分钟了。
总书记回应李雪健的发言说:你讲得充满深情。正如你所说,从焦裕禄、杨善洲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职业病——自讨苦吃。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把荧幕形象刻画好、塑造好。
10点20分,7位同志发言结束,总书记说:下面我讲,会很长。说着他望了望坐在右侧第一排的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对大家说,今天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年事已高,大家如果累了,就到休息室休息或者走动走动。请工作人员照顾一下。
我留神了,工作人员很快走到几位高龄老同志身旁征询,几位老人都摇头,没有动。
于是总书记作了100分钟的重要讲话。
这几天里,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全国的媒体作了充分的报道。要说体会,我也通过媒体从几个方面畅谈了自己粗浅的体会。其实这只是我聆听总书记讲话以后刚进入学习阶段的感触,对于整篇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还要进一步深入地学习、思考,真正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为读者、为祖国和人民,书写时代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 王""" 童